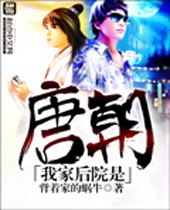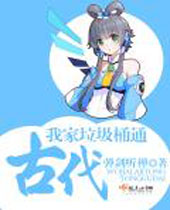�����Ҽ���Ӱ��-��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ѵ���ѧ������ң�������ţ�������ĸ���ߡ������������ڻ���������ʱ���꽨��30���ꡣ�ӣ�������������ȥ��ƽ��ɽ�������裬������������ר��ȥ�Ϻ�����������Ϊ����һ�죬���������30�ꡣ���ڣ����������ˣ����ǡ�����������
�������������������ԣ�һ����ζ���ɷ�����������ǰ�뿪����������ֻҪ�����ţ��Լ��Ͳ���ȥ��������ʹ��λ����һֱʹ���š�������ζ�Ź��ң�����������һ��ǰ���ĺ춼Ī˹�ƣ������е�ʥ�أ�����ļ���������������Ψһ���������û�����찲�Ź㳡�����ҹ��ķ�Χ����������
����������ʱ�����������Ѿ��ܲ�з�����������������벻��ҽԺ�����Ϊ�˽����������һ��Ҫȥ��հ��������ʱ�䱻һ���������涨��һ�����ϡ��ڼ����ã������ͱ��������й�ʮ�������������Ů�����ţ������������һ�����¶����������
�������������һλ���������ϲ������ʿ��ǰ̻¶���飬ʹ��ػ�����Ȱ�����ų���δ��������ʷ�����������Ǵξ���Ҫ�ߣ��������ҵĻ����ҿ��ˣ���ôȰ��ô˵Ҳû����ֹ������������������������������ί��ȥ�Ϻ������š����ż�������ߵ������Ǽ������ѣ�����������˼ҵ��֣����η����ؿ����š����ڣ��������������κ��棬�������ݵ���һͬ���ᡣ�����������š���������
������������Ͱְ��������Σ�������������Ϣ�ҵ�����顶����•��������ǰ�档����̧�������ɷ�����Ϥ�����ɷ�����飬�þò������������һȦ�յ��������ӣ�һ�ѡ����ѡ����ѡ���һ��ʮ���ѡ��������������ʧȥ�����˶���������ö�ð����ְ֡����衢���á��÷ܵܡ����ӣ��������ˣ�ֻʣ����һ������������
����������Ȼ�����ű������˳�����������ʱ������������һ�ۡ���ʵ��˫���ѱ���ˮģ�������ۣ�ʲô���������ģ�����ղű��Ҵ��ƹ���������ʱһ����������������Ǿ����������ˡ�20��ǰһСʱ�����ڼ����ӣ������˵���������������ɷ��Լ���ʹ��˵���ɷ�Ҳ���������ˡ������ӣ��봹ĺ֮�����ε����ơ���������
��������5������������ƿ������Ҵ���ʱ��һ�ж��ѽ����ˡ�����ȥ�ˡ�����ǻ�����Ϩ���������ĸ����һ�������ɭɭ����¶������Ŀ��д����������������뺰һ�������ţ������겻��Ҫȥ�Ϻ�ȡ��Ƭ�����ڣ�����������50������ǣ��������Ϻ���ȡ�����ˡ���������
�����������Ÿ��������µģ���������ԩ�ҵ�Ƭ������һ�����������귢�����ĸ����м�����֤�����չ涨����ÿ�������ȡ������Ԫ�IJзϽ𣬵���ȡ����ǩ����û�������κ�һ������ǩ�����������䡱��ֱ������ʱ�ģ��������꣬����������Ժ��������ߵ����أ�����Ӧ������֧ȡ���ƣ�����������Ԫ����Щ������������30��ĵ�Ƭ������һ��Ů�������ǹ�ֵ���������̵�����֤�����DZ����ġ����Ƶģ�������������зϾ���֤�飬д�������������˼����������ף���������
�����������������������������������ս�ѵ�Сƽ���������ľ�����������Ĺǻҷ�һ�ң����Ƕ�Ҫ�ͻ�Ȧ�����ŴӴ˻ص�������ս���м䣬��һֱ����һ��Ůսʿ��ֻ����ʧɢ40��������ڹ���ˡ��������������һ���ң���Զ�ļң�˭Ҳ���ܲļҡ����ţ����İɡ���
��һ�¡����ź�����һ���ҵ�����������1��
��������•���Ҽҡ�������������
���������Ҽ��и��������������ҵ����衣�����������ģ����ڿ�������ȷ�������й����Բ�̫��⣬��������������˼ά��æ����Ϊ����������������й����D�D������Ц���Ѿ����˿��ӡ����²�֪��ζ���ľ��磻��Ϊĸ�ף���Сʱ�����ܳ�һ��ʱ�䲻�����ߡ������ܳ�ʱ�����մ��Ų��������Ų�����������ҪŮ���չˡ��͵�����ô�ࡰ��Ů�ɷ����������һ�������������ȣ����������Ϊ������������أ���������
������������������ŵ�Ů���������м̳е�����һ�������εľ����Ų���������ʱ���ﻯ�ı��������������ǵ����Ǹ������������š���������ʵ����ʱ�����浽����ͨ���ʡ��ij̶ȡ��������ͯ�����й���������ߵĹ�ͬ�������Ǵ�˸ջع�ʱ����Ϥ�й���������֡���ͨ������ǡǡ����Ϊ����Ϊ�ϰ����е�һԱ��ƽ�����գ���������������һЩ���������������Ĺ��¸���룬�š���ͨ���ġ���������
�����������������ѧ�ƽ�ı������ܶ��˰ѽ��ӣ������ǻ�ͭ�����ϣ������������˿��������Ҽҡ�������ѳ����Ľ��������Լ����ģ���Ϊ�˼�������Ѫ��֮�������������������ľ������꣬�߹����ض�ׯ�����ꡢ���ֱ꣬��������ء������D�D���������Բ�ͬ�IJ���������ָ���������������Ӳ���ͷ·����������
���������Ұ��Ҽҵġ������D�D�ҵ����裬��Ϊ���������ҡ���硢�ְ֣�����������ż�������ô��İ��������ȣ�����ʲô������Ҫ��������һλ���裬�ҷdz����ˡ����Ļ���¼���ҵĸ���ë�����������ѧ�������ᣬ�ɴ�����д������ļƻ�������Ȿ������С���ܴﵽ����������飬�����й������������鹵ͨ��Ŀ�ģ��ҽ��е��dz���ο����������
��������•��������������
���������ҵ��������������һ��Ů����Ҳ�������һ��Ů������һ�����͵õ��ˡ������������毣��������ΪŮ�Ի������֡�����Դ��һ�ǵ�ӱ����һ�䡰���Ǹ�С�������������������������������ݵ䣬�ں������ҵ��˹Ű���Դ������������־ͽп��ˣ�ǰ������������ϡ�ë���ء���һֱ����������ʽ���֡�������Ϊֹ����������
��������˵��������������������ʯ�����ӡ���������������ǻۣ����ӵ����������ȡ�á������㡢��Ӳ���㣬�����������˳˳��������Ը�����������ҿ��������裬�Դ������������������ֺ�Ȼ�ںܺܶ����С�һ�������û�������Ұְ�˵�ģ����븸ĸ���õ����������෴����������
��������•��������������
�����������軹���й�һ�Ρ�ä��������ʷ������Ҳ��Զ�ģ����Ӱ���Ī˹�ƣ����Ҹ�����ѧ·�̵��������أ����ҵ�ʱ�������ꡣ��Ȼ�����ҿ���Ц��˵�����������㣨˵��ֻ�Ǻ�������ȣ���ʱҲ��ʮ���꣩���������������Ž�������һ���������˼�ʻ�ľ�������������ݣ�Ȼ�����������;����ȥ����������Ҳû��ȫ˵������Ϊ�����Լ����ԣ�����������������û�У�����֪���Լ�ȥ��η�����Ϊ���£����ܲ�����һ����ä�����أ���������
����������������Ժ����Ӱ�����Ժ�й����������ƹ¶����������Ҳ�ǣ����Ϊ�������䣬�����������ڵ���ͥ�ĸ����������ȵ����ֵ��衣��ʹ�����ģ�Ҳû�ա���ʹ�пգ�Ҳ����������ʹ��������ҲӰ������������ˣ��������˵��С����Ϥ�˼���������仰˵��Ҳ����û�мң�û�и��ף�������û��ĸ��������ڣ������ڿ��Լ�����С�Ͳ������ߵ�ĸ���ˡ����������������ζ��ʲô�أ���������
�����������������̻��䣺�뿪�Ӱ������죬ë�������Ž������������������ɻ��������ŵö��ڸ�������һ�Ϸɻ����Ҿ�û����ë������Ҳ������Ů�����ģ���ǰ���˰ɡ��ڷɻ��Ͻ���������һ�ض��ӣ��ֿ��ֽУ����Ǽ������ְ˽ţ��������������������Ҿ���������������Źֵġ����䡱���ƾ�����Ʋ��д����š��ڼ����µ��ó��У��������������Ϥ���������յ���Ŀ�ĵغ���������뿪�����ˡ���������
��������•���ؼң��ϣ���������
������������������С�������һ�ε����𡰴�ʹ�������Σ���Զ������á�����������Լ�ĸ�����ߡ��뱣��Ժ��ȣ����������Σ��������и����ˡ�ĸ���Ǽ�ѽ����ʱ�������̿�������ĸ���žۣ�������ϲ���ſ��ֱۣ���������Ů�������֣����˽�������һ��ʱ����������ĨD�Dԭ������Ҳ�������Լ�������һ���Ѿ���ĸ�ף����������ֱ����δ���������ǡ��Ҽ��б�����ľ���������������
��������Ī˹�ƹ��ʶ�ͯԺ��Ӧ��˵������ӳ��������ĵ�һ�������ġ��ҡ�����ʹ�������ӣ�����������ǿ�سɳ���������СѾͷ������ת�䡣�������Ǹ����ӣ����ǰ������ͣ������Ͷ�ͯԺ�������С��硢������ڱ���ѩ�����浽����ڵزŻؼң�ֱ����һ���յ����������ѧ�ͻؼң����������棡�����������������һ�㣬����Ϊ͵͵��С�����ˣ�������źݺݽ�ѵ��һ�١�ĸ���������������ɵ�˼���У����ˡ��ɾ������⣬��һ���롰��η����ϵ����һ�𡣡�������
�����������ݵ�ʱ�Ĺ涨��ͬѧ�Ƕ�Ҫ��ɹ�ͷ���������赱ʱ��ͻ�С����̫���⡣����һ��ĸŮ��Ӱ�У����ź����趼���Ŷ̶̵�ͷ�����������ý������ã����ߵ���ʵ�ڲ�̫���Լ���һ�μ�������λ����ƮƮ�������ˡ���������
������������ʱ�����ź���������ˣ�������ʴ������й���С����ļ���仯�������ش�ת�ۣ��������ڿ��Իص��Լ������ļҨD�D�й��ˡ����ǽ��������Լ��ĵڶ����ҨD�D������������ʱ���ǣ��������굽���������ꡣ������һ��ģ����а���˾ˡ�����Ӣ�˾������������ξ�������˺�һֱû����������������
��������������������裬����ʮ��ġ����������ﺺ�ֻ������ᣬ���ﵹ�DZȽ������������������������в����������塢���̣��������Ӱ��ͱ������IJ̳����̣����о˾˺���ѧ����������Ӣһ���ˣ���������������������ĺ�����������������ӡ���й��ijƺ���ϵ�渴�ӣ������һ�θо�����һ�㡣��������
���������ҵ����ź��������ź������Ը�dz����ƣ���������̸������������˿��������ϣ���Ů�������ϵ����ţ�������û������źá���ʱ���ź����Ž��������������顣�������������˨D�D����Լ�ӡ��dz������δ������ĸŮ��������ĸ����йء�ʮ����������ں����Ķ��£����Լ��߳��Ķ��ģ�д���˸���ĵ�һ���ţ�ë��ϯ������˵�������Ů��������˵�Ҳ������Ů�����ҵ����Dz������Ů���أ�����š��ܿ죬���յ�������һ��籨���������ҵ�Ů������Ҫ�ú�ѧϰ��Ҫ��һ���й��ĺ�Ů�����ְֺܺá�
��һ�¡����ź�����һ���ҵ�����������2��
��������•���ؼң��У���������
�����������ã�����Ͱ���˾˾������Ŵ��ţ��߸����˽���ƽȥ�ˣ���������һ���ˡ����ڣ���Ů���뿪�������µļҨD�D�ְֵļ�ȥ�ˡ��������ֻص��˹¼��У������������Լ��Ĺ��ң�ÿ�컹�й�������Ȼ����֧�ֲ�ס�ġ�Ů����̫С����������Ϊʲô���費�ܸ���һ��ȥ���ְ֡����������������е������𣿡�������
����������ǰ�����趼��ͨ����Ƭ�ͻ�����ʶ�Լ��ĸ��ס����ڣ�������վ���Լ���ǰ�ı�ƽ��ɽ˫����������ˡ��������ӣ���������ֱ𣬰���˾����ԣ�������������û�������ס����һ���������ˣ����������ѶԷ�����Ƭ�����ֿ������������ꣵ�µ���һ�죬�ë���Լ��������������Ķ�Ů�����ž��ˡ�������Ҳ�Ӵ������Լ��ĵ������ҡ���������
��������Ӧ��˵�����������Ů�ط��ʱ�䣬���ŵ�ʮ�ֺ��ʡ�һ����ǰһ�㣬�ոս���תս�±��ĸ�����ӱ�ƽɽ�����£���ս�ڼ���ʮ�ַ�æ�������Ƴ�һ�㣬����ס�����Ϻ����ֽ�Ϊ�������ͳ���ս������˼��������ĸ�����������ګ��ʱ����������������Ӣ��繤��æ����ʵ�İ�������������Լ����Ḹ��ע���������ǣ���Ů������˰��꣬ʵ�ʿ���˵��12���˼���ʱ�����й������������̵����Լ���ս�ѽ���˵���Ҹ����Ǵ���һ�����������������ʱ����¡���������
����������Ф�������ʱ�Ǹ������������쵼�������������Ӱʦ����������������ߡ�����̻���˵������������ϯ������Ͼ���ֽ���һ�����磬���Ƿ�����ɽ˫������ȴ�������ϯ���ڿ��飬��ʱ����Ů�������ܹ���������غ��š��ְ֡��������ס���ϯҲ�Ȱ���§��Ů������ʱ���龰ʮ�ָ��ˡ��������Ⱦ����ϯ��������ã�����������һ�£�˵������������ɡ����ǸϿ���ǰ������������Ψһ������ϯ��Ӱ����������
������������˵������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