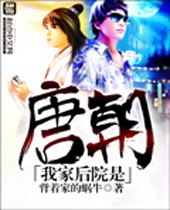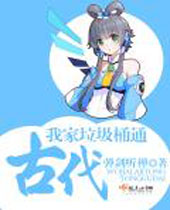�����Ҽ���Ӱ��-��3����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ɵģ����������۵�ʱ�������ں�������ǹ���ܽ��������ۿ�����Ҫ�����ˣ��øϽ��Ҹ��ط�ѽ��˵����Ҳ�湻������·����ͷ��û�з��ӣ�Ω���м���һ��������С���ݡ����ǸϽ��Ѻ�����̧�����ݣ�����û���ˣ����ŵ�ͭ������ð����������������
����������ʱϣ��������һ�������֣���˵��������ӱ���������ң�˵������������һ��Ů����ͬʱ����һλŮ���������Ҳ��һ��Ů�����˴���ȡ��һ�����֣��С�˫������������º��ӣ�ֻ���˺���һ�ۣ��㱻����̧����·�ˡ���������
�����������������䣺һ�����磬�������Ķ����������ݰ������һ����ׯ��������һ���а�ɽ��ɽ�壬��������·�ĺ��������������ʹ����Ԥ�е���Ҫ�����ˡ��������������䣺����ϴ�ɾ��������ðײ������Ӱ��á���ͬ��������������д�������ӣ����Ƿ�����ʮ�����������ѻƬ�����������ж����ƽʱ�Է��Ĵ��룬����һ�ۣ��������롣����������һ����ں��Ӱ������д�����Ӵ����ǽ�����������Ҫ������������ȥ��Ϊ���˱����о����ܴ����ӣ�������������ĺ��Ӽ�����������������Ů�ɣ��������˻��ܰ���ɵ���������
����������ź����Ĵ�ʡ�����صİ�ɳ��һ�����������Ŷ��������������СŮ���Ĺ��¡��������ͣ�������������ص�ʷ����������ص�������һ��˵���϶�ȷ�д��¡��ݵ��鿼֤���Ŷ��ż�ס��ɳ�ӱ߳����ϣ�����������µ�ŮӤȡ�������䡣�����º�������ҽ�β������������⣬���������ź�������ĸ����ӵĹ��¡���������
��������•���������ߡ�������
��������������һλû���������֣�ֻ�ж������ֵľ˾ˣ���Ҳ�����ŵ����һ�����ӡ����Dz��ҵģ����������������Զ�븸������֮���Ī˹�ƣ�ʮ����ʱ��Ⱦ�Ϸ���ȥ�����������ʧȥ������ӣ��������������ߵ��ҵ����裩��������˵������֮������ô����Ҳ�����ֵġ���������
�����������ǣ���ȴ�ö̶����������������16���15���ͬ����ĸ�������˼����ϲ�á��ҵİ�Ӣ������˾˴���������������Ϻ���ز�İ����˾ˡ����ǿ����������֮�����Ƹ���ë��С�������Dz����Ѿ��˷ܵ��뵽�˲��û�����µġ�ë�����ֵܡ�����������
�����������Ҹ���ʱ������̫�̣������ű�ʹ�����ظ��߸����������Ϣʱ������Ҳ����ס����Ȫӿ��ͬʱ��������Ȱ���������裬�����ѹ��ˣ���Ҫ�������壡С�ܵܲ����ˣ����������ţ�����Ҳ�����Ķ���ѽ�������裬�����衭����������
����������ʱ����������ʹ��ʧ��������ͻȻһ��§ס��Ӣ�����ࣺ�����衢���衱������ѽ����ѽ�������˿���һ�š�����������������˾˵�һ�������ź��������衱������ʴ�����ʧȥ�������ź��Ѿ������û˵�����ˣ��������˼�����֣���������
������������ʧȥ���������ӣ�ȴͬʱ�õ����������ӡ�������ʮ�����Բ����ػ��Կ�������ĸ�ӵĻر�����ĸ��Ӯ���˶��ӵİ������⣬���ҵ����߾˾����Լ�СС�����������ġ�
��һ�¡����ź�����һ�����ź�����ĺ�������ϣ���������ϲ
�����������������꣬�������ڻص�����ʮ�����������Ժܴ�����Ͷ�빤���У���û�й�������ɷ�ë������һ�������⣬�⼸��ɳ�Ϊ��������Ļƽ�ʱ�ڡ���ʱ��38�꣬�����긻��ǿ֮ʱ����Ȼ�����ܵ�����ĥ�����������������������壬��������Ŭ���˷��Ų�ʹ�����ٴ�������Ƭ�Ͽ�ȥ�����е���Ů����ķ�ɡ���������
���������������й��˿������൱������Ī˹������������ţ��Ѳ����Ӱ�ʱ�����Խ�������֮�Ա��ˡ�ǡǡ�෴����������������˳��������С�����Ī˹�ơ�֮�ƵĹ���������ϣ�Ӯ��һƬ�Ȳʡ�һ�Ȳ�����Ҳ���˺��Σ�����������ϸ����֫���ϼ��ú���ķ�װ������ȥԶ��ʵ���������ᡣ����һλ����Ůʿ�����ܲ�������ͬ־ע�⣬ʵ���ϣ��Ѿ�����ί��ض�����ʾ�˺øС�Ҳ�������Ž��Ӵ������µ�����֮·����������
���������������ڿ�ʼ���˶����������㽵����ţ���ʱ�����뵽�ľ���Ů����������������������Ϊ�����Լ����������κ��ش�������������Ů���кô��������෴�D�D�������ĸ����ѽ�����ǣ�ĸŮ���й�һ�η���ʽ��̸�������ŵ�������˶��ı䡣��������
��������ֻ�������ı�������ǰ����ǿ�����ߣ����������11���Ů�����ǴΣ����Ź������赭д�������裺��������������Ҹ��ְ֣��ò���ѽ�����赱ʱ����˼���غ�������Ҫ����һ��������������ʵ���Ϻܴ������Ρ��������������ϣ������������������ãȻ��֪�����ˡ���������
��������������������ڻ���¼����Ī�����������Լ���ʱ����������������������û�и��ף��������һ��������ˣ�Զ�߸߷ɣ�һ����ʹ��ĥ���Թ˲�Ͼ��ĸ��������һ�У���Ȼ�����������ǰ��Լ��ġ�������ʧȥĸ�ף����������κ��˷���ĸ�ף��������Ŷ����������һ��δ��������Ҳ��Զ���������ġ���������
�����������ź���������������������ֱ������ĺͶ��ĸ��д��һ���š����ŵ������ݴ����˵����ϯ�����Ѿ��ص��й��ˡ������岻̫�ã��������������μ�һЩ�����������������࣬�ȳ�����Ҫ�ࡣ�������л����Լ����ú�ĸ���չˣ��������������ġ���������
��������ĸŮ���ŷ���������˵籨���Ǵ�����ġ��Ӵˣ�����������������ȥ���Լ��ĸ���ȥ�ˣ���������һ�����ڼ�����ȴ����˺���ɾ����ų�����������������תս�±���Ƭ������������֮�俸ǹ��սʿ��������ȥ����������һ�ΨD�D����ʱ�����������ǣ���������֮ǰ�����ܽ������������ɷ���ס�����Ϻ������һ���ط��ɡ�Ů��ʵ�������뻵�ˣ������ų����е����ţ����������������Ϻ��һ�����顢��ʵ������������ְ��ģ����Ǻ�����Ϊ��֪����ʿ�������š���������
��������DZ�����������еľ�ѹ���������ڻع�����������������������ǣ������������Ϻ�ʱ��żȻ����������������Ժ���������������ȫ���˴�һ��һ�λ��鿪Ļ�ʡ��㲥����һ����һ�飬��������һ����һ�顣ֱ���ڶ���ɩ������Ӣ�����������������ϣ����Dz��塣����������һҹ���Ѿ��ջ��ˡ���������
��������������β��ò��ᣬ��֪��Ϣ�����������ǰ��һ���������ᡣ����Ů����ȥһ���ţ�Ȱ����Ҫ��ҽ���ģ�������ҩ�����һ�������ŵ���Ҳ��ú���������������Ȱ����Ҫ����ô����̣������岻�á����������ֺ���ѧ�չ����š�����ž�����õ�ҩ������֪���ɷ����˼��һһ��ϣ�������������������
��������֮�����¼���ܶ����������˺����������Ϊ��������һֱ�洢�����ɷ�ʮ�������ȫ�����䡣���ѳ������������������ÿʱÿ�ֶ��ڵ�ȡ���Ƚϡ���ζ���������K�ޣ���ͻ�������Ĵ̼�����������������
�����������������ţ���������D�D�ӽ�30��ʱ���Ҳſ�ʼ�����ף���������һ�־��Ķ��ǵĴ�����飡��������
���������Ϻ�����·�������ţ�����������ס����30��ĵط�������һ�����ڣ�������������㷨ʽ������Ӫ���������ͬΪ�й���һ�������������ֵ������������ѵ��ܷ������������������Ϻ��г����㡣���ڸ�������֮������ս�Ѻ�������˽�������������
����������ǰ����һֱ��ס�ھ������ѧ���У�ֻ�н���������ССһ�����ҡ�����̽��ʱ�������ⲻ�������ŵ�������������ʼ�ղ������鷳��֯�����������ڱ����ȥ�ļ�����£��Ѿ��ܺ��ˡ���®ɽ�������ͬ־�������ŵ������֪���ڴ����ܸ�ʡ������ʱ������ص��ͷ˵�������ˡ���������
�����������������꣬����Լ��ļ��������ɽ������Ͻ���®ɽ�����������ŵļ��磬Ҳ�����ǹ�ͬ���ս������ĵط����������������������־̸�����ܵ��������������Ѿ��ֱ�22������Ӽ���һ�档��ʱ��������®ɽ���ᣬ��ʶ���ŵ��������࣬Ϊ������Ҫ���鷳�������Ǽ������ܵġ�������ڿ�����ÿ�������˵Ļ��䶼�������������
�����������ڿ�����®ɽ���������ջ������ŵ����������飬����ͬ�Լ���ˮ������һҹ��̸������¶����������ǰ��δ�ŵ����ࡣ���ֻ��ᣬҲ��ֱ��20��������·�����߲ɷ���ʱ�����֡�����ʱ�����Ѿ��ಡ������ҽԺΪ����������ϸ�����̸��ʱ�䣬Զδ�ﵽ��������������ֱ�����ܵij̶ȣ���Ժ����������õ��ź�����������
�����������Ǵ�̸���У�ˮ�����������������µ�����������ҫ�����ƹ⻪���·��ֻص����ǡ�����һ֦�����������Զž�족���ഺ��������Ż��������������ʱ������ż�������վ�����������ֹ�һ����������������ӣ�����С��ʲô��������˵�����˸���������������֪���������С�������Ź�Ϊ�ʮ���Ⱥ�����ʮ�����ӡ����º�п���������һλ��ôΰ������Ӻ�ĸ��ѽ���ǵģ����������ܳ��֤�����Ŷ������˽֮������������
��������������λ��棬���Ŷ�®ɽ�����������������ꡢ����������ͣ���������֮�ģ���������ɽ���������⣬����������н�����̺����ֳ���������ԭ������յ�һ������������̣��ʹ�һ��������һ�롣��ʱ����Ȼ�������Ű����̣��Ͱ�δ����ľŰ����ѳ���İ��һ����ã����������š�����һ�������ű�����ʰ�����̣����������ڳ����һ���е������̾���Ϊ��®ɽ���ơ���������
����������������������ʫ�����ҵ��ġ����룬�Ƿ����������ӳ��λ���˻���˼��ĸ��������أ��ϲ������������ס����⡷���Ի�ɬ�������봩�丽���������ɣ���û��Ҫ��ֻ�о�ĩ�䡰��������Ϊ̽����ʵ�ڴ������ڡ���̽�����ġ�����˵�IJ������Ǵ�С���ڸ�ĸ֮�䵱����ʹ���������
��һ�¡����ź�����һ�����ź�����ĺ�������£�����������
�����������ź������ת�۵㣬����Ϊ���Ǹ�������ij������㿴�����ĵ�Ц�ݣ���������Ƭ��ʵ��̫�����ˡ��ҵĸ��������ڣ��������꣬��ë�ҵ�������Ψһ�����������D�D��ʱ�����Ǹ�Ӥ������������
�������������Ҫ�����һ����ͷ���йصĹ��¡����辡�ľ�������������չ����ŵ����Σ���Ƭ�����ŵķ��;���������Ƶġ�ֱ������������ڣ����Ŷ��ǰ�������ͷ���������С���Ӳ������Ժ�������������ϴ������Ͱ����ŵı��Ӵ���ͷ�����ϣ����м�Է֣����Եþ�����ˡ�ֱ��ȥ�������Ŷ�����������͡���������
�����������������꣬�ҳ����ˣ�����Ҳ���������������������ҵ���Ƭ��ȥ��������ʱ������Լ��������һ���������������Լ�ϲ���ġ�÷���������ҡ���ô�������İɣ���������
���������������Ϻ������ģ����굽����֮�䶼���������߶ȹ�������˵���������辡Т�ɨD�D��ĸ��ʱ���Ǿ��ˣ���Щ���˶����ϣ����Ǹ���æµ�����ڵ�ʱ���С�����Ÿ��ҵ�ӡ��û�к����˵��Ҳ�֣����������¼����������涼��������������ش������������������ȥ��ʱ��ȫ��������������ʱ����ȴ���ֳ����˵�ƽ������������
�����������ڻ�������������һ�β�����ǰ���ε�Σ����ֻ��������ѹ�ֽ����ʱû�б��������ּ������ͷų�����ֻҪ����һ������¥�����Ͼ������˾�ס�㰲�������Ƕ���ѳ�������˼����������µ�ʹϧ��һ˿һ�Ƶ�������ʴ���ս�˥�ϵ����ġ��������Ǹ�����Զ�������ǵģ������������֮ҹ�������˯���ҷ����С���鷿�����ƴ��������ϣ�����ֻ����һ��С�졣�������Ϯ�£��ڶ����ҷ��������Ѳ��������з��ˡ���������
��������Ȼ�������Ų����治��ʱ��ʱ���ҵ������������ҷ�������������������ѡΪȫ����ЭίԱ�������䡰��š��ˣ��������ձ���Ϊ���䷢�������Һ�������ҽԺ��������ž��������ĺ�Ӱ����һ�꣬����ʮ�꣬�����ꡣ��������
�����������������꣬�ѵ���ѧ������ң�������ţ�������ĸ���ߡ������������ڻ���������ʱ���꽨��30���ꡣ�ӣ�������������ȥ��ƽ��ɽ�������裬������������ר��ȥ�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