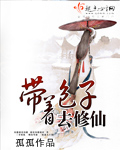����һ����ȥ���� by ��-��11����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һ����һҹ��ͬһ������ȥ�ͽ����������ڣ�ֻ�����ڡ�
������ʵֻ���������ڣ�������ÿ��ֱ����Ŀʱ�һ�õ�ǿ�Ҹ��ܡ�����Щ�绰����������Բ������ij��ʱ�̲Ż�չ�ֵ�������ò�����ܴ�ý�Ĺ����Կ��ܻ��ƻ��������ߵĴ���У�����ֱ̨������ʵ�ر�����ij����ʵ�ļ�¼�ԣ�������������İ������Ⱥ��
�˵�һ���У�һ����һЩ���飬������˽�˵ģ����ᱻ���ᣬҲ�����˷��������ԣ������ڱ�����������ʫ�ġ������˵ġ����ص����飬�¶��ַ�����
�ȵ����˽�Ŀ����ҹ����ɢ������ǰ����·��ƹ���ͬ���ߣ��������DZ����紵��Ļ�ԭ����Ŀ����ЩЦ���ᶼ�������Ӷ����ĵƣ�������û��ҹ�ı������Һ�Ȼ���ף�ij���˵�ɥʧ��ij��ʱ�̵���ȥֻ��һ���ǵ�ɲ��������������Ϊ֮ɥʧ�ģ����Ǹ��˶��ض����������˽�����ʣ����Ǹ�ʱ���������ظ�����ʵ�У�����Щ��һ˲�������ͣ�������ĸо�����һ����ʱ�ո�������Ҳ�������ľ��롣
ż��
С�к���l0�����ң��������ű�������ˮ��
������̨�췶���泤ɳ���ѻ���볡ȯ�����һ��Ҳû���ϡ������ߣ����ڰ칫�����⣬��������ϡ�����ȥ���������´α����������һ����������Ʊ���ò��ã����������������������������������ֲ����ҵ�ż��
�Һ�ͬ�¶���һ�ۣ�˭Ҳ������Ц�������ǵ��겻Ҳ��ˣ�˭û�Թ�������ɫ�˵ȣ�һ��ʸ־���塢��Ƚ�ᡣֱ�����գ����Ǽ�λŮ�ѣ�ÿ��ij���ӹ��������һ�����С�У��̶�˫�����������Ļ��ֻΪ��һ�������Ǻ���ĺ���Ц�ݡ�
���ܽ�Ŀ��и�16���Ů��˵��ż����˵����ǰ��ż���������ף�ǰ������������ɳ������Ҳȥ���ֳ������ǿ��������˼������ǩ��������Ȼ����Լ����˳��纣�е�С����һ˲��Ļ�����������ɥ�����ɡ����ؼҺ���������¼������Ŵ�����������Լ��ġ�ż��ʱ������
����������һλ����ȥ����״ӱ��������ij��š�����˵��ʮ������ʱ�����Գ°�ǿ�ĸ裬�Ժ���С��ҵ������룬��Ҳû��������ֱ��ǰ���գ�ѩҹ���ϣ���Ȼ�������ס�һ�������Ծ���������û���������ѣ�����ϲ��ʶ�𡭡��벻�����������£����మ��Ϊ�ηֱ�һ�������Ծ�������������ʱ��ں߳�����������ҹȴ����������ζ����������ɿ��Ƶ�˳��˫������������
�Ҳ�û�а�����½�����16���Ů��������ż����һ��������˵��ֻ�����Ƿ��ƿɳµ��������һ�㴫�桢һ��������һ������������ΰ��ˣ�������Ҫ��Ҳ�������ס����ģ������Ժ����꽥����ż������ʱ�����֡�Ʈҡ��ѩҹ�����ǹ������������顣
��������һ������Щ���ˣ�Ȼ��ȴ��ʮ��ʮ����ů�ġ��������Լ�������ӡ֤�ɡ�
���죬���ǻ��Ǵ�Ӧ���Ǹ�������С�к������ѻ�ʱ�����볡������������ΪЦ����ȥ��ͬ�º�Ȼ˵������֪���������������Լ���Ц����
������
���������������֣�����������˭֪������
����������
��һ����������ɫ���ĵ�Ӱ��������������ʼ��ͷ�ǵ绰���·ɿ��������ڸ��ٵ�����ɫӰ�д������ߺ��´�������ԽӢ������Ͽ��������·�ݺύ��������������˵�������������Ŀ�ĵء���ȴ��æ����
��������ľ�ͷ����Ϊ�����ߵ绰������ͼ�⡣���������������е�������ÿ������ͼ���ߵ������������У����������ܴ�ʱ�䲦������ʱ��æ�����˾�ɥ�����ߵ绰�빫����������������������ִ˲�ƣ�������˼�������ijһ���䣬�ֲ����������粢��Ϊ�������Ķ���
���ڱ�������ҹ������ǰ��̸����Ŀ��¼��������������Ϊһ�����ڶ�����������ʱ�������ܹ�����ϸ�������������Щ�绰�����ĺ�����һ˲��������Լ�ƽ�����ں��첻��ĸ������ʾ���������ࡣ���ߵ绰��������ͨ����ý�Ĺ����Խ���Ⱥ��£��һ�𣬰���С������֮�л�Ϊ���˵���ͨ���顣
Ȼ�������ߵ绰�ܹ������ǵģ����˶��ѡ��������ڡ�����ͼҹδ�ߡ�ʽ��������������Щ���Զ���ͨ�������ʰף�ֻ�dz����˴ӹ¶����б���ų����Ķ���ɲ�ǡ���������˼������һʧ��ɢ����ʱ����Ȼ�������������е��������ڳ��ţ�ֻ����Ϩ�����ŵ�ֱ���䣬��֪��˭���ڲ�ͨ�˵绰������ͽ�����������ţ�����������ҹ�����������һ����һ����
��ȫ��
�����ҵ�һ�����ڣ�24���������Լ�һ������Ժ��ż����绰����Ŀ������������Ц���̣�ʮ�������ˡ�
ȥ�����ڽ�Ŀ̸�ۡ�������������˷��߾������������̣�ĩ��Ϊ�����Ϊ��ǮΪ�˼�į�Ҵҵؽ��˻飬������ץסһ�㰲ȫ�С������˳���һ����˵�����һ���绰�����ģ��ɾ�ˬ���˵��������ʱ���й��õ�ǮҲ�����ֻ࣬���Ҳ���һ����ֵ�ð�����
�ף��������ϣ�ȴ���ֶ������Ǹ�������Ů�ӡ�
���ܵĽ�Ŀ�����ǡ��ȡ�������������绰�����������֣������˰��β�������˭����������˵���ȫ�������ķ��æ����һ�����ɺã�����Цһ��������̸�����ˡ���
�Է���һ���곤��20������ˣ�����Ů�ѵĸ��ס�
����������ʶ�����ˣ���û�뵽�ᰮ��������������������ϸ����˿��һ�ư��㡪��������ġ�⧲������ĸ�����ӵ����س�������������������������������������ֱ��£�Ϊ������һ�С�����������ֻ������������������϶��绰����������Ӧ��֮�����������������ˣ�������һ���˹����գ�����Ľֵ��ϣ���������һ����һ�顣
����ǫ���ذ�һ���ˣ����������Ҳû���ϵ�������ͨ����������������Ϊ�����ͷ����Ϊ����ͷ���ܲ������Ϊ��һ�����ȵĽ����ɣ�
���������ʣ���˵��������û̸���������������չ�ò�˳�����������۹�˾��ԭְ������������Ҫ����ȥ���������������ѵصȣ���Ϊ��ʲô�أ�����û�а�ȫ�еİ��飬ֻ��һĨ��Ӱ��ʧȥ�˶�����֤����������Ů�Ӿ�Ȼ����Թ�⣬�����Ծ����ᡣ
���������Һ�Ȼ���������ߣ������ģ������ⲻ��ȫ�У��ľ�����ɳһ���İ��������һ��û���س����ţ�һ�����ǵ����ѣ��ƹ�ʫ��˵����¯һ��ѩ�����ٲ��ܵ�������Ҳ�ٲ��ܵ����ޡ�
��ȫ�У�������ô���������֣�˭Ҫ��
�ɰ�
�Ǵν�Ŀ�����˸����ң�ǰ������ǡ��������ˡ����˶������£��������������ȵ�˵�����£���Ů������һЦ˵������û����˵���������㣬��Ҳ�������������������ҡ���
˵���º���̹�ס����ɰ�����������������ңԶ��ʱ�䡢���������±�á�һ����Ը�ļ��䡭�����Ǵ���Ҳ�����ˡ�
���ܽ�Ŀ����������š���һ����˵�������������ѵ�ǰ�����ѡ�4��δ������һ���ϳ����������к������µ绰���º������л��������������Է��ķ�Ӧȴ�������ϵؼ��ҡ���4�������Ϊ�����������������ᣬ�̶��������绰�����ˣ���̾���������ˡ�
������ɻ��ǵ�һ���ˣ������ʡ�
�������ǵá����������ӿڡ�
���������ܣ����Ȼ�ǵ��ң�һ���ǵ�������
�����������ǵá�����һ��ҧ������˾��飿��������4���ˣ������������ֶ������ᣬ��˵�ѹ�֡������ڻ����������ޡ���������������ͷ��Ӱ����ҹէ��ʱ�������շת�ţ����������ӻ����赲��
�ڶ������ֲ�ͬ����20�����꣬��һ���˰��������ĵġ���ʱ������Ϊ�⣬һƳ����ȥ�ˡ������������������£�����ƴ�������Ż�����������Ȼһ�������������Ϊ���汼����ij�վ�����ɽ·��ӭ�����˻��������֣����������Ǿ���ģ�������е������ɺã���Ҳ��ƽ���͵�˵���á���ȥ����
������˵�ˡ���Ҫ˵Ҳ��˵��Ȼ���dz�Ĭ�л�����һ��������˽�Ͱ�ο��
������·�����𣬶�û�����µ�ַ�绰�������ŵ�ĩβ˵����Ҳ�������Ի�żȻ������Ҳ���Ի�����Ц�Ų����������
�������ˣ����ŵ�����Խ�Ƶ��ϸ裬��ҹ�������ػصس�����лл���������ң�����ͬ���������ڻƻ�֮�У���֪���������ж���ʹ������
����
��Ҳ�����졣�����ϰ��·�ϣ�ϸϸ������������꣬�ȵ���ҹ���˽�Ŀ�����Ѿ����ˣ���æ����¥����һ�գ���Ȼ�и���ӭ���������ɵؽ��ҵ����֣�������һ�£�����һ�ߵƹ⿴�������ž�װ�Ű�������������ô��ĸ��ӣ���ȴ�����������ڰ�����˵���ǹ����ƴ��ѧ������Ҫ��ҵ�ˣ��������ң��Ǽ���������Ը����һʱҲ��֪��˵Щʲô��ֻ�������ɡ�ƹ�ȥ�������꣬�����Ϻ����˼����������������ã������ˡ���
�ҿ�������Ӱ��ʧ����ڵ���ҹ�ת�����ߣ��������������ܻ��������ǵ�ͨ�죬�ӿ㶵���ͳ�һֻ���н����ң���£˫�š�ˢ���ؾ���һ������ת�����ˡ�
��ֻ������װ����һֻС�ڹ꣬Ӳ���̱��İ���ˮ�꣬�������Ĵ�ơ�Ʊ����������ܾá����궬����䣬С��̰���˵���ů��ÿÿҪ���������IJſ�������֫����˯ȥ���������յ�����ɰ������
���ڻؼҹ���ʱ��ͬ��ת�ĸ���һ���ţ��Ǵ����ؼ����ġ�����¯��߲�ϸ��������д����������ҹ����û�����ұ�ҵ��ȥ�����Ҳû�и����㣬��ѡ�����ңԶ��ѩ���ԭ�������˼�������ʮ�ֺ��䡣��һҹ��ȥѲ�ڣ������¹������������ѩ�壬��Ȼ������Ϊʲô��Ľ�Ŀ��˵�����˵Ĵ���������ʯ�𡯡���
Զ����Ȼ�������ڵĴ��죬�Ҷ��˶٣���������ȥ����������������ϻ����кܶණ��ֵ��������ȥ����������ֻС��ɺã��������䣬�����������㣬��ȥ����������·���������г�ʱ�ģ�Ҳ��ͬһ�죬��������������������Ľ�Ŀ����һֱ��Ϊ���ⶼ���������ҵ������ϥ�ߵ�¯�������������Ϻ�����������һ��ů�⡣ˮ���Ѿ��������䣬�������㡣
���ӳ�˵
����4��30�֣������ʰ���ˣ�һֻСƤ�䣬����ǽ���ϡ����ص�����б������5¥�Ĵ�������ȥ��dz���Զɽ��������������Ѿ����ˡ�
3��ǰ��ʼ����ҹɫ���ᡷ�����Ҳ�����ʱ�����������飬��Ƭ���ţ�ֱ������ѩ���Ĵ�Ƶ�ͷ���ţ����������ܹ���Ҫ�dz����������ε�ϲ�ã�˵�������������е����¡����˽�Ŀ��������ҹ���ֽ��ϵ͵͵ع���һ�ִ��Բ�Ļ�����������ղŽ�ĿƬͷ��˵��ҹ����˽���������裬���̲�סҪЦ��
��֪�������������Ұ����㲥����Ϊ�������ֵ���������ϲ�õģ�����ģ�ƣ���ġ����������ݡ���ϲ������дʵ�Ŀ��������������ˣ���֮��������������Ũ�������иС�������Щ����������������ɣ�Ȼ�����ӻ����ż��Ҳ����������������һɲ�ǡ���һ�λ���˵���ĵ����£�һ���������������̾Ϣ��һ������ľ�Ĭ�����˺�Ȼ�����ơ��������Ĺ����ţ���ÿ��ͬ�飬���˸ж����ᡣ������������ӵ�������Ρ���Ƭβ������ҹ���纣��ʱ���˳�������Ƶ��������ų����Ĵ�غͺ�ҹ�ı�Ϣ�������ĺ����������֣����ҽ������Сȭͷ�����ĺ��Ӳ�Ҫ�ѹ���������������������һʱ�䣬˭�������Ǹ����ӣ������ã�����ϧ���ӱ������˵������л���˰�ο��
�����㲥���˲�������������һ˲��θ��ڵ�����ʵҲ�����dz��飬��һ������˯ǰ������ʫ������һ�����к��Լ���������ģ�Ҳ��һ����˵�����DZ���ϲ������ͷ�ǻ����ѡ�ǰ������ʰ���飬����ȥ����ǰ�������ѣ���һ��������Ÿ���һ�䡰�ƺ������ơ������������ص������м䣬�����ڴ���˻˻������ȥ�ˡ���3�������治���á�
�������һҹ�Ѿ����ˣ����˶�֪���������һ�ڽ�Ŀ�ˣ�����������ʵ��������Ϸ�绯�����գ�Ȼ������Ӳ��ͷƤ����ȥ����Ҷ�����ʶ����������������Ķ������������Եľ��𣬱��˵ĸ裬�������ڷ�Ȼ�ĸ�ס�ֻ����ʮ�ֻ�㱣�����Щϸ���ӵ�������ǰ�������ԣ����˽�Ŀ�ܾ�Ҳ���Ѳ���������㯡�
������ʰ�������Ѿ��ǻƻ��ˣ��ö����ˡ�ֻ�������ס�����ӵ�������Ρ�����һ���ϳ�Ƭ�������������СƤ���̫���Ѿ�����ȥ�ˣ����һ�������ڲ������ϴ�������һ�¡�����һ�����ʡ��Ҵ����˷��š�
�������������߳�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