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一个 文章合集_韩寒-第63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海,我的体会,是在这本书里,有很多我上海家里发生的事情,我小的时候,我的表哥、姐姐、哥哥,都可以在书里面看到一些线索。所以我看这本书的时候,会感觉一见如故。还有一点,这本书有一个特别牛的地方,用的是方言。也不是单单的上海话,金老师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上海话的改良。今天为什么马家辉会来主持,是因为他一点不懂上海话,但他看懂了这本书。还有一点,感觉现在的作家写一本书,都是今天这个题目是什么,字数应该是多少,书还没写好,就想下一本书是什么,有一个整体的想法计划。但金老师这本书,我看完之后马上盖起来,不能再看,看一次就够了。因为这本书看完之后,感觉经过了一生一世。《繁花》有这个感觉。
我看《繁花》是一口气看的,味道很鲜明。金老师讲过一句话,小说的精髓,就在那个味道,要写出一本书的味道。很多人说的故事,很多线,很复杂,但从来故事的完整,不是小说必须要具备的条件。金老师写的东西,超越一个故事。
我一看就感觉,金老师把一辈子的故事,要讲的话都放进去了,是很浓的一锅汤。我看了知道这有点亏,其实《繁花》可以写十本书或者二十本书,他说那时候没想过,还能再写一本书,就把所有东西都放在这本书里。所以我认为,这本书很对得起读者。
作为读者来说,我有个问题问金老师,很多人都讲《繁花》里很多的上海元素,但是开头你引了一句话,“上帝不响”,是什么意思?
金宇澄:是小说一段情节引起的,春香就要结婚了,她信教,拿不定主意,妈妈给她介绍了一个男人,她很痛苦,心里不愿意,希望上帝答复,同意还是不同意结婚,上帝不说话。
人生做任何的事情,可能都在上帝的视野里,但上帝不会给出任何答案,得自己决定。我把它放在前面,作为一个题记,也因为全书有一千多个“不响”,对于不了解上海话的人,可能觉得做作。刚才讲了,我是用上海话思维写的,如果是上海人,心里原原本本讲述一件事,“不响”两个字肯定是会出现。比如张三找李四,李四不说话,上海人心里就这样描述,李四“不响”。这两个字在上海话里相当常用,每个上海人一天都会讲几次,但为什么大家都没发现,都不这样写?刚才讲了,因为普通话的教育,我们一思考,一写作,就是普通话,普通话只有“无语”,“沉默”,字典里有“闷声不响”,没有“不响”的用法。有评论家说,如果是一篇两千字文章用了“不响”,这两个字别人还可以用,现在你一下子用一千多个,这两个字就属于你了,别人以后怎么用?我真不知道会是这样。
这两个字作为题记,是体现一种无奈和虚无。有一位评论家说,《繁花》整个的表现,是“花无百日红”,进入一种虚无或及时行乐的状态。开卷是《阿飞正传》,结尾提了“温柔同眠”,这两个意思,是因为惯常的人生观察,表现的方式,差不多都已经用完了,但阿飞这样的人,以另一种特殊角度看到的在城市生活的人,是什么样的?因此《繁花》只写上海市民阶层,包括一些不务正业者,人人都有自我的处世方法,如果祈求上帝,上帝一样是不回答的,一切只靠自己解决。
王家卫:“不响”这句上海话,很有意思,代表了我不讲话,不讲话不代表我赞成,但也不反对。不代表我反对,也是一个态度。金老师我为什么会特别有兴趣,他用这句话做书的开头,是非常有上海人的特点,很多事情都懂,或者,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态度,但是他们用一个“不响”来做个反应。
金宇澄:现在的读者是最聪明的,包括上海人,很多事情,可以慷慨激昂,大声疾呼,也可以一声不响,因为大家都明白了,有一些东西,都是非常明白的事,很多东西只可以沉默不语,书面的“无语”在网络上也很流行,这跟“不响”是差不多的意思。
王家卫:这个词是很重要,用上海方言写作,每个方言词,都有艺术在里面,广东话也有,北京话也有,每一种语词都很重要,值得保留和保护,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讲一下广东话。
马家辉:我刚才一直在讲广东话,你以为我讲普通话吗。刚才金老师说到上海人不表态,也有态度在。刚才导演说我不懂上海人,我必须承认,因为我故意不懂,因为我不喜欢懂,因为我必须承认,我不喜欢上海人。从香港的角度,我从小就记得,听长辈们说的,上海人特别是上海男人,逃不出三个特点:第一个大家都懂,怕老婆。这是我们香港人常说的,一讲到上海男人,就是给老婆洗内裤这样。所以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努力地想讨个上海老婆,后来失败了。第二个特点是狡猾,第三个是小气,抠门。长辈那一代人没办法,养成是这样,一想到上海男人就这样说。所以我故意不懂上海话。
可我也经常好奇,特别看到这本书里面谈到香港的部分,香港有亲戚,好几个故事人物都跑去香港,包括收到香港亲戚寄来的明信片。甚至出现上海过去的黑话,关进租界的西牢,叫“到香港”。金老师怎么来看香港,上海跟香港的对比?
金宇澄:上海、香港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对应的两个地方。上海开埠比香港晚,刚才说“到香港”,是旧时代上海话“切口”,大概二十年代的切口,现在上海人不大知道。
上海租界很多方式参照香港,巡捕房的建制都是从香港警方转移到上海的,会采取香港方面的样式,英租界一些高管,都是先从香港调来。1949年后,上海和香港的情况不一样。除了二战,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香港没有过,而上海经过几次的变化。简单作为人来讲,一个人老是变,一个人是不变,那么前者肯定非常注意后者。比如说我老是离婚,你一直没离婚,我就会觉得你怎么这样稳定,我怎么这么变化,大概这个意思。《繁花》有些人物,六十年代几个资产阶级小姐,喜欢跳舞,是躲在家里跳,很小心,怕有声音,窗帘拉起来,怕被人看见,居委会干部如果报告,就按流氓罪抓起来。一个叫淑婉的女人就说,这样跳有什么开心的,就算没被人抓。音乐非常欢乐,或者脚跺地板的跳法,都不行了,上海有什么好呢,就算我从香港弄来最时髦的唱片,又怎么样呢,上海早就不行了。
香港是一个参照物,我现在想想,上海市民最注意的就是香港,比如上海第一次开日本商品展览会,是1956年,非常轰动,一直被老百姓提起。《繁花》里没有写,塑料制品第一次让上海人看到,有这样好看轻巧的东西。但这种热情,还是和看待香港不一样。等于说,上海一直与香港是差不多心理位置,它就一点没变。小说里写寄来的明信片,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降落的照片,理发师很骄傲,说是他的亲戚寄的,实际是寄给楼上小毛的,理发师插在镜子前面好几天。包括八十年代初,阿宝的香港哥哥来上海,阿宝爸爸在香港搞革命,留下的孩子,阿宝爸爸很警惕,不承认这个儿子。香港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上海也一样是革命的摇篮。曾经搞地下工作的阿宝爸爸问儿子,凭什么给我送港币,是收买我?得到什么情报?知道我腰腿有病?他害怕和香港有什么联系,是被整怕了。这两个城市既互相这样对立,却又有紧密的纽带。
马家辉:你经常来香港吗?
金宇澄:来的次数不多。
马家辉:这一次要好好走走,香港的变化终于来了。每天我都打开报纸看电视,我就觉得这是不一样的香港。港片你看得蛮多的,比如《阿飞正传》。
金宇澄:一部非常好的电影。王导《阿飞正传》那个结尾,就是《繁花》的开头。
马家辉:结尾用的《东邪西毒》。
金宇澄:是梁朝伟这一段,前面部分他这个人物从没出来过,为什么会放在后面,等于无意中的《繁花》开头,把这个人放在《繁花》的开头,我很佩服这个处理的方式。电影和小说作为艺术品是一样的,虽然有些同行认为《繁花》并不怎么样,我只觉得不能都是四平八稳的,应该有一个属于作者本人的标识、标签一样的特征。《阿飞正传》结尾,突然冒出这么一个人来,这就是王导的风格。我们要琢磨好半天,这个人干吗要跑出来一次。
马家辉:我好奇,《繁花》很多不同的故事,将来拍成电影也好,或什么处理方法,王导有兴趣拍成电影的话,有没有想过怎样处理这个作品?
王家卫:这个我第一非常感谢金老师,因为我们不是最有钱的,也不是最有势力的。这样的书做影视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我也有一个很大的焦虑,因为中午金老师做了一个比喻,说他自己跟书的关系。我没有他讲得那么好,请金老师自己讲一下。
金宇澄:已经讲过几次,就等于是,一直不生小孩的老太太,到五六十岁突然怀孕,生了这个孩子。可以试想这个老太太的心理,对于得来不易的小孩,肯定变着办法去给她打扮,翻花样,不停给她梳小辫,买裙子买皮鞋,这也就是《繁花》改了二十遍的原因,有点不正常的心态。一个年轻的二十几岁的女人,生小孩就很方便,一年可以生一个,可以连着生,很骄傲。五六十岁的女人如果怀孕,走路就很难为情,包括他人的看法,很复杂的心态。
王家卫:这也代表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要考虑到的一种焦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责任,我希望可以把它做好。还有一点,我看这本书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其实一段时间以来,每次讲上海的文学,其实都非常明显,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张爱玲的影响,永远都是非常女性的。但是金老师的小说,对我来说是非常男性的,也是非常性感的,这种性感不是粗犷的也不是颓废,是一个上海男人的性格。在这方面来说,我希望大家可以看《繁花》,有机会也可以找金老师以前一本随笔集《洗牌年代》、他的小说集《迷夜》来看看。
马家辉: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金老师的书不是单讲上海,看他的影评,还有他的中篇、短篇小说,会体会到他写的是什么。王导演拍一部片五年、七年,金老师这一点超越了他。你写小说好像停笔了二十年,蛮长的时间。
金宇澄:九十年代以后写得很少,做小说编辑后,慢慢就不写了。
马家辉:回到作品的语言,王导演说方言除了表达以外,还有本身的音乐性,我们知道金宇澄先生用上海话呈现小说内容的时候,不是把每一句变成上海话写下来,注意到沟通问题。我们想听金老师讲一下怎样处理上海方言的心得,先请金老师用上海话读其中一段,这是很难得的机会。
金宇澄:今天两位一定要我念一段,我从来不念,你们希望我必须念。如果纯粹上海话,《繁花》肯定是不够格。首先第一,上海人早晨起来要讲的字就是“侬”,侬就是你,你侬我侬这个字,说起来很简单,大家没有一个不认识。想想看,如果拿到一本书,翻开里面每一页都是“侬”,肯定不习惯,很古怪的。比如说“我们”,上海话就是“阿拉”,这种字多了的话,一本书翻开都是这种上海话常用字,有种心理暗示,一般普通话读者在心理上就不喜欢它。所以《繁花》做的大量这样的事,是里面没有“侬”,也没有“阿拉”,都转换掉了。等于这个小说里基本上没有这些,实际蛮难做的,等于这本书里,“你”字变成称呼名字,或者换个位置来写,只有写到北方人讲话,才有“你”、“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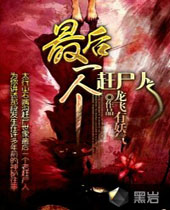
![[快穿]给我一个吻封面](http://www.nstxt.com/cover/0/72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