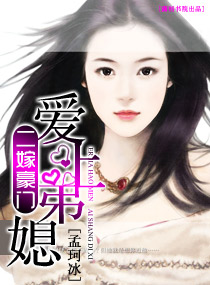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术成果作了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之后,才能予以客观公正的回答。而以钱氏学术之博大,目前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以下选取几个侧面来说明钱钟书的“知识修养”不限于“博闻强记”。最显著的例子是,钱钟书对宋代诗歌、宋代诗论有相当深入的体察或研究,从其选本名著《宋诗选注》及诗话巨制《谈艺录》等著作来看,一方面,他在对宋诗的“具体鉴赏”(78)中屡有精审卓识之见,如对王禹偁《村行》一诗中“数峰无语立斜阳”一句的解说就相当精妙:“山峰本来是不能语而‘无语’的”,诗人“说它们‘无语’”“并不违反事实”,“但是同时也仿佛表示它们原先能语、有语、欲语而此刻忽然‘无语’”,因此,如“改用正面的说法,例如‘数峰毕静’,就消减了意味”。(79)另一方面,钱钟书在对宋代诗论的评价上也颇有创获,如对严羽的“以禅喻诗”说,一些近代学人囿于清冯班以来对此说的诟病而视之“蔑如”(80),钱钟书则在参以西方神秘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Plotinus)等人有关神秘经验之说的基础上,另眼观照严羽此说,进而以“别开生面”许之(81)。据钱钟书自称:他对严羽的肯定性评价随《谈艺录》的出版面世后,“物论稍移,《沧浪诗话》颇遭拂拭”。(82)如,曾对《沧浪诗话》的观点持否定态度的郭绍虞先生就认为钱钟书的评价“最为圆通”。(83)这个例子表明,钱钟书既有“兼览之博”,亦有“专门之精”,足堪比拟于章学诚所谓“通人”。而从“知识修养”的个人性角度着眼,钱钟书之关注宋诗,自与其早年与“同光体”诗人陈衍的诗文交谊有关。
前文的注释中曾提到钱钟书的清华同学饶余威称赞其“精于哲学、心理学”,而当时的清华教授冯友兰也称许其在哲学方面颇有“见识”,可见他在文学之外的其他人文领域方面的“知识修养”亦非泛泛。当然,冯、饶的观点只能作为旁证,我们不妨从钱著中选取一些内证,以为佐证。
钱钟书生前曾对人说,他“一生为学,得益于黑格尔、老子的辩证法者甚多”。(84)这句话对理解钱钟书的学术思想实在是一个极重要的提示。以此反观钱钟书的学术研究,可以看到,钱钟书对黑格尔思想、老子哲学都相当关注。如对《老子王弼注》,《管锥编》中有专门阐述,而黑格尔的美学、哲学思想,也屡见于钱著。老子有“反者道之动”之论,冥契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钱钟书对此曾作过比较,他说:“反者道之动”之“反”字兼“反”意与“返”意亦即“反之反”意,一语中包赅“反正之动”为“反”与夫“反反之动而合于正”为“返”,与黑格尔所谓“否定之否定(das Negative des Negation)”,“理无二致”,因此,老子“此五言”可谓“约辩证之理”。(85)这段论述显示出钱钟书对黑格尔、老子辩证法思想的较为准确的把握。而综观钱氏之学,可以看到,辩证思维乃是钱钟书的重要运思模式。如在评析王禹偁之《村行》“数峰无语立斜阳”一语时,钱钟书之所以能一眼看出“无语”乃“有语”之反,从而体会出欲语而不语(正而反)、不语而欲语(反而正)的妙处,显然与其长于辩证思维有关。
又如,按照美国文论家阿布拉姆斯(M。H。Abrams)的看法,“阐释循环”命题所描述的局部与整体彼此互动的认知模式,首先由现代解释学的奠基者施莱尔马赫所揭示,后经狄尔泰(Dilthey)命名并明确阐发后才成为解释学领域的核心范畴。(86)这种说法似与历史事实有出入。因为,就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最先揭示认知过程的循环性的,应该是德国19世纪哲学家和语言学家阿斯特(Friedrich Ast)。钱钟书就曾指出关于“阐释之循环”的现象,系由阿士德(即阿斯特)在《语法学、阐释学、订勘学本纲》中首申此义,并援引伽达默尔的观点指出,“此盖修词学相传旧教,阐释学者承而移用焉”。(87) 此外,钱钟书还曾指出:“其事未必然,其理未必不然,这就是解释学” (88)这一对西方解释学的定位,可以说是折衷了伽达默尔的原义如幻影之论与赫施的文本“含义”确定说。因为,所谓 “其事未必然,其理未必不然”,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即是说,读者对文本的解释未必符合文本的原义,却未必不符合情理。换言之,文本的原义存在也好(赫施)、不存在也好(伽达默尔),并不妨碍读者进行有效的解释。由此可见,钱钟书对西方解释学的定位确乎是切入问题实质之后的折衷之论。这无疑表明钱钟书不但对西方解释学的源流有所了解,还对西方解释学的本质有相当深刻的把握。这一点后文还会论及,兹不赘。
综上所述,钱钟书对宋代诗歌与诗学,黑格尔、老子的辩证法思想,以及西方解释学等东西方学术知识的了解,绝不仅仅停留在“记诵”的水准,而是颇为深入并别有会心的。这就意味着,这些知识已由“书卷见闻”化作钱钟书的“性灵”,并融入他的学术思考中。而唯有能将书卷见闻化作自身性灵者,方能由博学者跃升为大学者。同理,“多闻之学”若未转化为学者本人的见解,也算不得真学问。这也许正是钱钟书给予后人的一个重要启示。其意义并不亚于当年清华外文系兼重中西的教育模式及老清华尚“会通”的学风给予当今学术界的启示。
第二章 “新旧中西子竞通”:钱钟书的知识修养第12节 视通中西的知识修养及其反思(2)
注 释:
(1)吴宓在《外国语文学系概况》(见《清华周刊》1935年6月14日向导专号)一文中有云:“……,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厚”,本论文所用“知识修养”一词,即源于此。
(2)傅璇琮《学养深厚与纵逸自如》,见《濡沫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
(3)王水照《〈对话〉的余思》,广州:《随笔》,1990年第3期。
(4)钱穆曾就“国学”一词发论曰:“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名词。”(《国学概论•;弁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笔者认同此说,因此,本章凡借用该词以涵盖中国传统学术或古典文化时,均加引号,以示对该词的借用仅出于“权巧方便”。
(5)许国璋教授谈及他在西南联大的老师钱钟书时,曾云:“钱师,中国之大儒,今世之通人也。”,见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北京:三联书店,1996,P53。
(6)参见本章第二节第二小节的讨论。
(7)钱钟书《槐聚诗存》序,北京:三联书店,1995。
(8)钱穆在《国学概论•;弁言》中称:“其时中学校率有‘国学概论’一课,此稿特为讲堂授课之用”。
(9)1998年9月,叶至善先生主持创办了“圣陶学校”,以教授中国传统文史或经史书籍为主(《北京教育报•;校园周刊》,2000年3月4日);而和钱钟书甚有渊源的近代诗人陈衍则明确强调:“为学总须根柢经史”(见钱钟书《石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0)笔者在介绍钱钟书的生平与学术时,尽量直接引用钱钟书本人及与其渊源甚深者(如其亲属、师友)的记述。
(11)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P346。
(12)见李洪岩《钱钟书与近代学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P12。
(13)钱基博日记,1935年2月21日,见《钱钟书与近代学人》,P24。
(14)钱穆《师友杂忆》,长沙:岳麓书社,1986,P111。
(15)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号辛楣,在清代汉学吴派学者中,学识最博,成绩最大。著有《潜研堂文集》、《廿二史考异》、《元史艺文志》等。其于史学上的成就,世所公认。江藩称誉其“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汉儒拟之,在高密之下,即贾逵、服虔,亦瞠乎后矣。”(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上海书店,1983。)
(16)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见钱钟书著《围城》附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17)“古文”与“骈俪”对举时,有特定所指,即与骈文相对的文章体裁,而不能等同于以文言文为语体的文章。前文提到钱钟书古文写作能力的古文,则指后者。
(18)《管锥编(全五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陈文卷七》。
(19)(21)见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无锡国专丛书。
(20)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著有《石遗室诗集》、《石遗室诗话》及《续编》、《宋诗精华录》等。
(22)见钱钟书《石语》。
(23)张尔田《海日楼诗集钱注序》(转引自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诗派》,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P7-8)
(24)《续怀旧》,郑朝宗著《海夫文存》,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25)见吴忠匡《记钱钟书》,《随笔》,1988年第4期。
(26)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
(27)夏敬观《忍古楼诗序》卷二。
(28)(29)(30)(31)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修订本)》。
(32)(33)爱默《钱钟书传稿》,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3月初版,P25。
(34)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
(35)闵卓《一个开拓者的生活道路》,《人物》1980年第5期。
(36)如夏志清《追念钱钟书——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新趋向》,见《不一样的记忆》,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
(37)《清华周刊》1935年6月14日向导专号,刊发了吴宓所作《外国语文学系概况》。吴在文中提到“按查本校外国语文系课程,系在开办大学部时,审慎编定。今仍遵用,无大更改。” 而清华“大学部”创建于1925年(见《研究院章程》,《清华周刊》1925年10月20日第360期),比钱钟书考入清华(1929年)早了四年,因此,吴文虽刊于1935年,其时,钱钟书已毕业两年,但仍可以借以说明钱钟书在清华四年所受教育。
(38)(39)吴宓《外国语文学系概况》。
(40)资深翻译家许渊冲先生认为,钱钟书在牛津毕业后得到的是“文学士”学位,亦可译“副博士”。见许渊冲著《追忆逝水年华》,北京:三联书店,1997。
(41)夏志清《重会钱钟书纪实》。
(42)据李慎之回忆:钱钟书“十分关心世界上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潮,不但包括文学,而及于哲学。伦敦《泰晤士报》的每周文学增刊,他是每期必看,而且看得很细,所以什么时新玩意儿,他都十分熟悉。”“80年代初,中国流行的是向南斯拉夫取经,实践学派正在走红。我去请教钱钟书,他不但回答了我的问题,而且送我了一本Praxis。前几年,中国兴起了解释学。奇怪,我那八卷本的哲学大百科全书,竟然没有Hermaneutics这个辞条。他又告诉我:‘其事未必不然,其理未必然。这就是解释学。’”“关于后现代主义,我看他知道的也不会比别人少,……现在的时髦青年老爱挂在嘴边的‘解构’(deconstruct)原来还是钱钟书应别人之请翻译的。”(李慎之《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送别钱钟书》,广州:《东方文化》,1999年第2期)
(43)李慎之《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
(44)钱钟书在致张文江的信中说:“近人的学术著作(包括我的在内)不必多看……”,见牟晓朋等编《记钱钟书》,大连:大连出版社,1995。
(45)夏志清《重会钱钟书纪实》。
(46)《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注(3),见《七缀集(修订本)》。
(47)见《管锥编(全五册)》P167,P525,P837。
(48)(49)吴宓《外国语文学系概况》。
(50)吴宓《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清华大学一览》1937年。
(51)(53)(54)(55)(56)(57)何兆武《也谈“清华学派”——〈释古与清华学派〉序》,见徐葆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