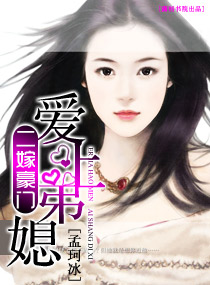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3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能打破旧传统,建立新传统。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谈到一种隐含在科学研究之中的‘必要的张力’。”(10)
显然,库恩所谓“必要的张力”,主要是指“常规研究”(受一致意见制约的收敛式研究)与学术创新(依赖于以“思想活跃”和“思想开放”为特征的发散式思维)或“科学传统” 与“科学革命”之间的均衡关系。他所谓“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必然同时显示维持传统和反对偶像崇拜这两方面的性格”(11),正表明维持“必要的张力”的能力,乃是科学研究者所应具备的重要素质。
虽然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理论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而发的(12),但它对于我们思考人文学术传统或文学研究传统的变革也颇有助益。例如,库恩所谓“科学家必须经常调整他们以前所信赖的智力装置和操作装置,抛弃他以前的信念和实践的某些因素,找出许多其它信念和实践中的新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新关系,接受新的就必须重新估价、重新组织旧的”,如果对“智力装置”、“操作装置”等语词进行适当转换,就基本适用于人文学术传统或文学研究传统的变革(或称“创造性转化”)。具体言之,人文学术或文学研究领域之所以会出现变革的趋势,恰恰是因为人文学者或文学研究者以前所信赖的观念和方法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而促使人文学者或文学研究者调整其观念与方法的动因,或者是因为人文学术或文学研究自身演变的需要,或者是因为外来思潮的冲击,以中国人文学术传统或文学研究传统的现代变革而言,应当说是两者兼而有之。此外,就变革的方式而言,人文学者或文学研究者在调整其观念与方法时,也应当抛弃他以前的观念和方法的某些因素,而在接受新的观念和方法时,也同样必须“重新估价”、“重新组织旧的观念和方法”。由此观之,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论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视为钱钟书“辨证革新论”的注解。区别在于,库恩的科学革命论主要着眼于科学传统自身的纵向演变,而钱钟书的“辨证革新论”还兼顾本土传统与外来文化的横向关联。再从学者的素质而言,人文学者与文学研究者又何尝不应兼具“维持传统”和“反对偶像崇拜”这两方面的性格。
经验证明,中国人文学术或文学研究在进行现代变革之时,一味趋新或一味效仿西方都缺乏可行性。合理的作法,应是把握好变与不变的尺度,并对“过去的现在性”始终保持清醒的意识。显然,注重“过去的现在性”,不同于以“怀旧”(nostalgia)的心态面对“过去”。“怀旧”的特点在于,“只留意于过去的积极意义”(looks only at the positive in the past)。这无疑会使人“丧失分析变迁动机的能力”(disables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changes)(13)相反,对“过去的现在性”的强调,其着眼点恰恰在于“现在”,其深层的关怀,则是旧中开新或传统转化的可能性。
第七章 变迁的张力:钱学启示录(1)第38节 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及其限度
前文提到,中国人文学术传统或文学研究传统的变革,不是简单地以新换旧、以西化中或以科学性排斥审美性。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科学性”与“审美性”的紧张关系(14),主要是针对文学领域的现代变革(尤其是“科学化”趋势)而言的。
笔者以为,中国文学研究传统的现代变革的基本趋势之一即是“科学化”。并且,这一趋势是与“西学东渐”的过程密切相关的。为了说明“科学化”的具体特征,不妨先来看看钱钟书对上世纪初西方文学研究领域尤其是文学批评领域所出现的“科学化”趋势所作的描述:
“老式的文学批评家并不是不讲科学方法的,譬如硕果仅存的古董先生Saintsbury教授各言谢书,第一辑中便曾说过非对于几何与逻辑有研究的人,不能做文学批评家——虽然老头子,所谓几何,不过指欧几利得(通译欧基里德), 所谓逻辑,不过指Aldrich。但是老式的批评家只注重形式的或演绎的科学,而忽视实验的或归纳的科学、只注意科学的训练而并不能利用科学的发现。他们对于实验科学的发达,多少总有点“歧视”(不要说是“仇视”),还没有摆脱安诺德(即Matthew Arnold;英国19世纪著名文学批评家——笔者按)《文学与科学》演讲中的态度。这样看来,瑞恰慈先生的《文学批评原理》确是在英美批评界中一本破天荒的书。它至少教我们知道,假使文学批评要有准确性的话,那么,决不是吟啸书斋可以了事的。我们在钻研故纸之余,对于日新又新的科学——尤其是心理学和生物学,应当有所借重。换句话讲,文学批评家以后宜少在图书馆里埋头,而多在实验室中动手。麦克斯•;伊斯脱曼先生(Max Eastman)称瑞恰慈为‘旷古一遇的人——教文学的心理学家’(Literary Mind第五十七页),诚非过当,便是伊斯脱曼自己,也同样地表示着科学化的趋势;他在《文心》(Scribner.1931)一书中,利用Jean Piaget儿童心理的研究来解释近代诗之所以难懂,利用Jennings下等生物的研究来说明诗人的心理,诸如此类,都十分地创辟。”(15)
显然,钱钟书所描述的西方现代文学批评领域所出现的 “科学化”趋势,主要是指借助实验科学(如生理学、心理学等)的理论或方法进行文学研究的学术取向,如英国现代文学批评家瑞恰慈(I。A。Richards)的《文学批评原理》一书,便是以“心理学”和“生理学”进行文学理论研究的开风气之作,该书因而被钱钟书视为当时英美批评界中一本“破天荒的书”。(16)美国现代诗人、“对科学高唱赞歌”(radical celebration of science)的麦克斯•;伊斯脱曼(Max Eastman)(17)则通过利用“儿童心理”和“下等生物”研究领域的成果解说诗艺和诗人心理,而在文学研究中有所“创辟”。
从中国文学研究传统的现代变革来看,其“科学化”趋势,除了借助自然科学范围内的实验科学(如属于西方心理学重要流派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等)的理论或方法进行文学研究的取向之外(18),还包含着对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方法”的强调,如逻辑推理、系统分析等。关于系统分析的利弊,本文第五章已有所探讨,兹不赘。此外,以笔者之见,中国文学研究在现代转型之初所推重的逻辑方法,主要以形式逻辑范围内诸如因果律、排中律、矛盾律等规则为依据,并未超出著有《逻辑方法纲要》(1691年版)一书的阿尔德里西(也就是钱钟书所说的Aldrich)的视野。总的说来,关于中国文学研究传统现代变革中的 “科学化”趋势及其特征、以及“科学化”在文学研究中的局限性等问题,尚有待全面深入的探讨,限于篇幅和学力,本文拟在提出上述问题的前提下,以钱钟书本人的思考与学术实践为着眼点,切入对 “科学化”在文学研究中的局限性这一问题的考察。
钱钟书曾借古人“明体达用”之说阐发曰:“用之学问(所谓technology),日进千里,体之学问(humanities),仍守故步,例如亚理士多德之《物理学》无人问津,而亚理士多德之《伦理学》,仍可开卷有益。”(19) 钱钟书所谓“体之学问(humanities)”即是指“人文学科”(含文学研究),“用之学问”(technology)则是指“自然科学”或“自然科学”范围内的技术科学。在他看来,人文学科如“伦理学”中的有关思想的有效性,并不会因时间的变化而丧失,如亚理斯多德关于伦理学问题的思考,至今仍对现代人有所助益,但自然科学的观念和方法却处在不断进步(progress)的过程中,因此,亚理斯多德的“物理学”研究在今人看来,便不再值得关注。钱钟书的论述首先表明他对“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界限有明确意识(20);其次,它可以深化我们对不同类型的传统的不同特性的认识,在钱钟书看来,至少在自然科学领域,某种传统的存在往往只是阶段性的存在,亚理斯多德时代的自然科学传统就与库恩所谓“当代科学传统”(自然科学层面)处在不同的阶段,因此,现代科学革命(自然科学层面)所必须依赖的传统,便不是亚理斯多德时代的自然科学传统,与此形成对照,一般所谓文化传统固然也受时间性因素的影响,但不象自然科学传统那样有着明确的阶段性,因此,文化传统可以视为变动中的“一”,自然科学传统则只是某个阶段的“一”。由于人文研究就其所思考的基本命题(如美、正义、价值、人性等)而言,往往具有永恒性,因此,人文研究传统的阶段性也不如自然科学传统那样明显。
为了说明自然科学学科与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学科的差别,钱钟书还指出:“不同的学科对于语言文字定下不同的条件,作不同的要求。这许多条件都为学科本身着想,并没有顾到文学,应用它们的范围只能限于该学科本身”,他随后举例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时,有一条规则,略谓本会会员作文,不得修饰辞藻,须同算学公式般的简质(of a mathematical plainness)云云。”(21)可见,在钱钟书看来,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字规范。例如,适用于自然科学学科如数学(mathematics)学科的“不得修饰辞藻”这一规则,就未必适用于文学学科,更未必适用于文学创作。究其实质,“修饰辞藻”追求的是表达的美感效果, “不得修饰辞藻”则以表达的“准确性” 与明晰性为唯一目标。因此,“不得修饰辞藻”这一学术律令便是科学研究对“审美性”予以排斥的明确信号。从钱钟书的表述来看,他并不赞同将“不得修饰辞藻”作为文学学科的学术律令;就其文学著作的表达方式来看,他在兼顾辞达的前提下,格外讲究文字的润饰、辞章的经营。前文提到,钱钟书曾提出过“骈体文不必是,而骈偶语未可非”这一文体论意义上的重要命题;并且,于“古文”写作中时嵌骈骊的作法,恰恰是钱钟书主要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编》的基本语体风格。(参见本文第一章第一节)笔者以为,钱钟书对词章及“词章之学”的重视,一方面固然与他对古人“义理”、“考据”、“词章”并重之说的认同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作为“作家型学者”的特点有关。与同时代的鲁迅、朱自清、闻一多等人类似,钱钟书也在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两方面均有建树。由于对创作艺术的个中三昧颇有体认,钱钟书在学术文章的写作上便体现出较高的文学修养,其《谈艺录》、《管锥编》中的某些片段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某些片段一样,都堪称美文。此外,基于对创作艺术的浓厚兴趣,钱钟书在进行文学研究时,往往习惯于从操作的角度对文学现象进行分析。他曾指出,他之所以择取总集、别集中“有名家笺释者”予以研读,乃是为了借此“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以资其“操觚自运之助”。(参见本文第一章第一节)
由上可见,钱钟书在文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这两个层面上,对“不得修饰辞藻”这一“科学化”诉求均有所否定。此外,钱钟书对逻辑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也提出了质疑。由于对逻辑方法、逻辑思维的强调也是“科学化”趋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钱钟书的上述质疑自然也可以视为对“科学化”在文学研究中的局限性的反思。
钱钟书指出: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擅长,一到哲学思辨里,就变为缺点——不谨严、不足依据的比类推理(analogy)。讲究名辩的《墨子•;经》下说“异类不吡,说在量”,“毗”即笋比”,《经说》下举例为证:“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逻辑认为“异类不比”,通常口语以及文学词令相反地认为“凡喻必以非类”,流行成语不是说什么“斗筲之人”、“才高八斗”么。宴几道《清商怨》“要问相思,天涯犹自短”;又《碧牡丹》“静忆天涯此情犹短”, 不就把时间上绵绵无尽期的长“相思”和空间上绵绵远道的“天涯”较量一下长短么?明人诗“鄂君绣被寒元香,江水不如残夜长”(刘基《江上曲》),清人词“人言路远是天涯, 天涯更比残更短”(《全清词钞》卷三徐尔铉《踏莎行》不就更直捷爽快地用同一尺度来侧“量”“异类”的空间和时间么?外国成语不也说一个瘦高个子“象饿饭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