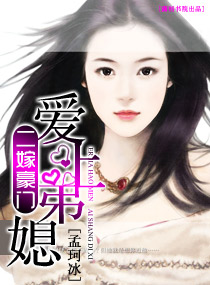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其研究对象时,往往容易滋生比常人更多的同情,但这并不妨碍研究者保持相对客观的立场。
(82)需要说明的是,对传统文艺思想的现代诠释,并不等同于援西释中,但由于物质文明领域的现代化乃至人文领域的现代变革,均导源于西方社会,因此,此处所谓“现代诠释”,一般难以超离中西会通的语境。说得更明确些,所谓“传统文艺思想的现代诠释”,在很多情况下,即就是以西方“通用术语”诠释中国的传统文艺思想。
第六章 挑战西学范式:钱钟书的反“体系”论第29节 文学研究的“体系化”(1)
自葡萄牙人于明正德年间重起中西交通以还,西方“有形”之“物质文明”与“无形”之“思想文明”便开始“逐渐敷布东土”(1 )。在这一“西学东渐”的历史过程中,传统文化的特性和传统学术的格局发生了微妙转变,体现在人文学术的研究模式上,便是越来越注重“理论系统”、“历史系统”的建构,而越来越轻视传统诗文评、札记和注疏的“不成体系”(2),自“五四”以后,此种价值取向已蔚然而成风习(3) 。
究其因,不难看到,随着西方学者的社会/人文思想陆续传入中国,其重逻辑关联性和总体相关性的人文研究模式及其相应的重“系统性”的学术著述体例,也同时对中国学人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在西式的大学教育和学位论文评审制度正式移植到中国之后,那种重“系统性”的学术著述体例和重逻辑关联性和总体相关性的人文研究模式(含文学研究形态)便具有了“典范性”的意义。这就不难理解对于钱钟书以传统札记体、诗话体形式写成的《管锥编》和《谈艺录》,何以前有“五四”一代的学者不以为然地评之为“不成体系、失之琐碎”,后有新进学人视之为“不合学术规范”。(4)依此类推,钱钟书师长辈的著述,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陈衍的《石遗室诗话》等,也难逃“不成体系”或“不合学术规范”之异议。
那么,重“系统性”的学术论著是否就一定比所谓“不成体系”的学术著述如《管锥编》、《谈艺录》高明?所谓“理论系统”、“历史系统”的学术价值是否就一定高于散见于传统诗文评、札记和注疏 中的“片段思想”?此外,在西学“范式”(5)和不断被强化的“学术规范”的制约下,以“片段性”而非“系统性”为特征的传统文学研究形态——诗话体, 是否还有复兴的可能?
通观钱著,可以看到,对构成二元紧张的“片段思想”与“理论系统”的学术价值,钱钟书有着明确认识。他一方面批评了西学东渐以来偏重体系建构的学术取向,并从多个角度揭示了“理论系统”的通病,另一方面则对“片段思想”的学术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而他在现代学术语境下完成的诗话体著作《谈艺录》,又为诗话体的复兴,提供了必要的基石 。
第一节 西学东渐与文学研究的“体系化”
按照西方哲学史的经典表述,古希腊哲学在经历了“宇宙论时期”、“人类学时期”之后,进入了“体系化”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为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他们同时也是整个西方“古代思想”的代表。他们与前辈学者的显著差异在于其学说的“体系性”。而他们的学说所以具有这种特性,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所关注问题的“全面性”,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处理这些问题时的“自觉统一性”。换句话说,这三位大师都分别利用了从各自的“基本思想原则”得来的“目的和方法的统一”,以从事全部知识资料的“统一加工”。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步骤:1)“将经验和观察所获得的东西集中起来”;2)“检验、比较”由此获得的“概念”;3)“使迄今为止仍然散见而且孤立的东西成为富有成果的结合和联系”。(6)
通过上述加工过程,“三种不同世界观的典型轮廓”在不到两代的短时间内就被制定出来。它们分别是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体系”,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体系”和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体系。这三种思想体系或“理论系统”(7)就其思想内涵本身而言,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构造这三种思想体系的以“系统化”处理及注重有机联系为基本特征的研究模式,则对西方学术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自“西学东渐”以来,这种研究模式也借助其所构造的思想体系对中国学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以此研究模式为衡量尺度,传统诗文评、札记和注疏的“不成体系”,便似乎成了必须加以反思的学术痼疾,而传统人文学术的“方法论”改造或转向,则似乎成了势在必行的要务。
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钱钟书凝聚才情、学识与心血从事“诗话体”论著《谈艺录》的写作(8),便在客观上具有了某种“方法论”反拨的意味。而他在西方人文研究范式(包括“苏联模式”)(9)业已笼罩了整个中国人文学界的二十世纪后半叶,仍然坚持以传统的“札记体”形式完成了他的学术巨著《管锥编》,则表明他对所谓“不成体系”的传统人文学术范式有着高度认同,也表明了他对以“系统化”加工为基本特征的西学范式,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
事实上,钱钟书除了在学术实践中延续了诗文评、札记和注疏等“片段化”传统人文研究范式(10)之外,对带有明显西化烙印的“系统化”研究模式的弊病及与之相对应的“片段思想”的价值,也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
例如,他在完成于60年代初的《读〈拉奥孔〉》一文中的一段方法论性质的陈辞(11),便颇具代表性,现节引如下:
“在考究中国古代美学的过程里,我们的注意力常给名牌的理论著作垄断去了。不用说,《乐记》、《诗品》、《文心雕龙》、诗文话、画说以及无数挂出牌子来讨论文艺的书信、序跋等是研究的对象。同时,一个老实人得坦白承认,大量这类文献的探讨并无相应的大量收获。好多是陈言加空话,只能算作者礼节性地表了个态。……倒是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也许有人说,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不成气候,值不得搜采和表彰,充其量是孤立的、自发的偶见,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不过,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再说,我们孜孜阅读的诗话、文论之类,未必都说得上有什么理论系统。更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都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
这段话的理论内涵相当丰富,概括而言,它至少涉及了人文研究(主要是文艺研究)方法论中的两个问题:
1)研究对象的范域(“挂牌讨论文艺”的文本/不“挂牌讨论文艺”的文本);
2)研究的模式(“片段思想”/“理论系统”)。
钱钟书指出,在对“中国古代美学”的“考究”中,研究者们的视野往往局限于“名牌的理论著作”如《乐记》、《诗品》、《文心雕龙》或“无数挂出牌子来讨论文艺的书信、序跋等等”(如司空图的《与李生论诗书》,何景明的《与李空同论诗书》,萧统的《文选序》,钟惺的《诗归序》,苏轼的《书黄子思诗集后》,龚自珍的《书汤海秋诗集后》),而忽视了那些没有挂出牌子来讨论文艺的文本如“诗、词、随笔”、“小说、戏曲”乃至“谣谚和训诂”等等于“无意”中道出的“三言两语”。钱钟书举例说,中国古代的民间谚语“先学无情后学戏”,虽只短短七字,却涵盖了戏剧表演艺术的真谛,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12)他又举例说,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批驳一则唐传说时下的评语“凡画奏乐,止能画一声”,徐凝《观钓台花图》一诗中的结句“画人心到啼猿破,欲作三声出树难”,均揭破了“时间艺术只限于一刹那”的奥妙,理应受到“中国美学史家”的关注。(13)
质言之,钱钟书对不“挂牌讨论文艺”的文本(包括文学文本如“诗”、“词”和非文学文本如“谣谚和训诂”)的理论价值的揭示,用意之一在于提示研究者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域。钱钟书自身的论著,便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在《谈艺录》、《管锥编》以至经院色彩甚浓的《七缀集》中,均超越了“名牌理论著作”或一般挂牌文论著作的束缚,而广泛涉猎了中西文艺作品、历朝笔记、民间谚语(包括钱钟书故乡的谚语(14))及各类注疏,可谓最大限度地扩展了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的范围,并显示出文艺研究领域在挂牌文论著作或文学文本而外至为丰富的学术资源。
这类“学术资源”作为理论文本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无意”为之,也就是说,它们只是偶然涉及了文艺理论问题,而不属于专门的研究。正因为是“无意”为之,其表现形态往往是“三言两语”的“片段思想”。钱钟书要求文艺研究者(同样适用于其他人文学者)充分重视这些“片段思想”,而不应象某些学者那样“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钱钟书认为,如果那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便是“浅薄庸俗的看法”。
事实上,“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这一与“西学东渐”及现代学术体制密切相关的学术症候,诚可谓其来有自,于今为烈。纵观当前学界,论文越写越长,专著越写越厚,追求“数量”已成一时风气,真不知如陈寅恪的《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等区区一、两千字的精妙短论,若从当前的视角观之,是否还算得正规的学术论文?更不用提钱钟书以札记体写成的少则数百字的《管锥编》了。
第六章 挑战西学范式:钱钟书的反“体系”论第30节 文学研究的“体系化”(2)
笔者以为,此种追求“数量”、偏重“长篇大论”(最极端的表现,就是钱钟书所谓“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的学术风气,一则应归因于日趋量化的学术评议机制,一则应归因于“西学东渐”以来渐重“理论系统”的人文研究取向。
当前的人文社科学界,无论是学位的授予,还是职称的评定,都以一定数量的论文或专著为“硬指标”。(15)且对学位论文的字数,也有“明码标价”的规定,如硕士论文若干万字,博士论文若干万字。这类硬性规定,无形中助长了追求“数量”的学术风气(或曰学术浮夸风),对那些不愿轻易“立言”的学者,构成了体制化的强大压力,迫使他们要么退出学位与职称的评审机制,要么被迫依循既有学术程式炮制出聊以充数的“长篇大论”,以在学术界站稳脚跟。此风所及,长篇论文和大部头专著一时间“蜂拥”而出,而有足够“份量”的精品,却寥寥无几。为此,不妨重温海德格尔的警句:
“多思,少说,保护语言。” (16)
在钱钟书看来,偏重“长篇大论”、轻视“片言只语”的学术风气与重“理论系统”而轻“片段思想”的人文研究取向是相对应的。那些致力营造“理论系统”的学术论著,其表现形态往往便是“长篇大论”:大到象维柯的《新科学》、黑格尔的《美学》、鲍桑葵的《美学史》等鸿篇巨制,小到象布封的《论风格》、海德格尔的《诗人何为?》、《艺术作品的本源》以至钱钟书本人的《读〈拉奥孔〉》、《中国诗与中国画》等单篇“专论”(17)。
前文提到,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学说所以具有“体系性”,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所关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