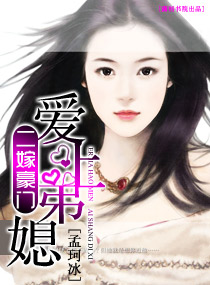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辞-意(王安石),文-词-志(孟子),语-意(庄子)这三组概念的辨析。
首先,何谓“文”?《孟子》赵岐注,释“文”为“文章之文”,而《孟子正义》撰者焦循,则从朱熹之说,纠正“赵注”而释“文”为“文字之文”(39)。钱钟书显然认同于“焦疏”。因为,他将王安石的“文同而不害意异”,苏东坡的“字同义异”,薛蕙的“不以一说蔽一字”并提,且在正面描述“阐释循环”一节,将“某字之诂”对应于“文”,同时,依次将“某句之意”对应于“词”,“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对应于“志”。
那么,“词”和“句”到底有什么区别?“词”和“辞”又有什么关联?
“词”可解为“语言组织中的基本单位”(据《汉语大词典》),如“词语”的“词”,有时又不妨释为“语句”,如“唱词”的“词”。“词”又通“辞”:《管锥编》正文中的“辞之终始”,在目次中写作“词之终始”。而王安石系以对“智”、“仁”、“不明”等的解释,来说明“考辞之终始”的必要性,因此,这里的“辞”,即“词语”的“词”。
以上表明,在钱钟书的论说语境中,王安石的文-辞-意,实即文字-词语-词意,而孟子的文-词-志,则意为文字-语句-“全篇之义”。需要说明的是,“词语”或者“语句”,均处于文字和篇章的中间层。无论由解释文字到理解全篇,还是从理解全篇到解释文字,“词”(“词语”或“语句”)都是无法绕过的中介、
接下来,我们问,庄子的“语-意”何指?且看其原文: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40)
显见,此处的“语”同于“言”,“语”之所贵在于“意”,并形之于“书”(文字)。而“意之所出”,“从道而来”,“道”既“无色无声”,故“不可言传”(41) 。这表明,在人类的“表述”活动中,存在着“能够说”和“不能说”的“界线”(42) 。庄子的“道”,即为“不能说的事情”。但是,“道”(“道理”)虽不可“道”(“道白”),或者,可“道”(“道白”)非常“道”(“道理”),人们并不甘于“沉默”,仍然“横说竖说”,“强为之名”(43)。对于这种“道”与“言”/“名”的复杂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言意矛盾,钱钟书在《管锥编》“老子卷论第一章”作了详尽分析,下文将论及。同时,我们看到,若返回原文,庄子的语-意链实可扩充为书-语-意-道“四重根”,比孟子、王安石深入了一层。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它们都归属于传统美学和(语言)哲学范域内的“言意”理论。
钱钟书又指出:
两文俪属,即每不可以单文孑立之义释之。寻常笔舌所道,字义同而不害词意异,字义异而复不害词意同,比比皆是,皆不容“以一说蔽一字”。匹似“屈”即“曲”也,而“委屈”与“委曲”藐若河汉。“词”即“言”也,而“微词”与“微言”判同燕越。“军”即“兵”也,而“兵法”与“军法”大相径庭…… (44)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文同而不害意异”(“字同义异”)与“字义同而不害词意异”的微妙差别。
仔细体味钱钟书的论述,可以看到,“文同而不害意异”,意为字形同而不害意异,例如,“老吾老”中的第一个“老”字,与“毋老老”中的第一个“老”字,虽字形相同,但在前后两种“上下文”中,却有不同含义,一为“尊之爱之”,一为“轻之贱之”。而“字义同不害词意异”,意为字形不同而字义同的两字分别与同一字(按,其同在字形)搭配构成两词,而词意不同,如“屈”与“曲”,字形不同而字义同,但与同一字“委”(字形同)相搭配构成“委屈”与“委曲”两词,却有不同词意。
综观上文,钱钟书由纠正《左传》“杜注”的一个误释,说到“不义不昵”型句法可于不同“上下文”中区分为“因果句”、“两端句 ”两类,进而引证王安石的“辞之终始”说等传统言意观,并借用西方语言(哲)学术语予以阐发,又一再强调“文同不害意异”,不“以一说蔽一字”,反反复复,主要为了提示人们于“解会赏析”之时,务必重视语义与“上下文”的关联。
第五章 在巴别塔的废墟上:钱钟书的文学解释观第25节 狄尔泰与戴震的对话
不难看出,钱钟书在语义与“上下文”关联问题上的反复申说,实际上为下文批判“乾嘉朴学”的单向语义阐释模式,正面描述“阐释循环”,作足了铺垫。反过来,钱钟书对“循环阐释”模式的论析,又全面揭示了语义与“上下文”的关联:即,局部语词的意义固然由“上下文”决定,而“上下文”的整体意义,也受限于局部的语义。
且看原文:
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只初桄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句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者是也。《鬼谷子•;反应》篇不云乎:“以反求覆”?;鸟之两翼、剪之两刃,缺一孤行,未见其可。戴震《东原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又卷一《〈古经解钩沉〉序》:“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躐等。”(略)钱大昕、凌廷堪、阮元辈诵说之(略)。然《东原集》卷一O《〈毛诗补传〉序》:“余私谓《诗》之词不可知矣,得其志则可以通乎其词。作《诗》者之志愈不可知矣,断以‘思无邪’之一言,则可以通乎其志。”是《诗》破“古经”之例,不得由“文字语言”求“通”其“志”,如所谓“循阶”以升堂入室;须别据《论语》一言,以“蔽”全书之“志”,反而求“文字语言”之可“通”,毋乃类梁上君子之一跃而下乎!一卷之中,前篇谓解“文”通“志”,后篇谓得“志”通“文”,各堕边际,方凿园枘。顾戴氏能分见两边,特以未通观一体,遂致自语相违。(45)
显见,钱钟书是以反思乾嘉“朴学”(着重于戴震)为逻辑起点而引入“阐释之循环”这一命题,以正面说明其解释观和言意观的。
所谓“朴学”,按钱穆的看法,系指清乾、嘉以来的“训诂考证之业”(46) 。粱启超则把“朴学”视为“清学”之“正统派”——“考证学”学者——所“矜尚”的“学风”。他又指出,清代考证学的根本治学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其代表人物则是乾嘉时期的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而段与二王,其学均源于戴氏,世称“戴、段、二王”,“故正统派之盟主必推戴”。(47)这表明,钱钟书在批判乾嘉“朴学”时,着重于戴震,是有所考虑的。另外,钱钟书所提到的“钱大昕、凌廷堪、阮元”,均“宗尚”“考证学”,其中,钱大昕受惠栋影响,凌廷堪为戴震弟子,阮元则主持校刻了《十三经注疏》并主持编撰了《皇清经解》这一汇集清代“汉学”成果之巨著。
事实上,“朴学”在清代学术界一直受到质疑。钱钟书对乾嘉朴学的反思,则着重于作为乾嘉朴学代表人物的戴震的解释观。
钱钟书首先对“以词通道”的单向语义阐释模式提出了批评。
其特征是:“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钱钟书对“朴学”语义阐释模式的这段描述,显然对应于戴震所说的“经之至者,道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钱钟书指出,“以词通道”的阐释模式,只注意到了解释活动的“一边”,而忽视了另“一边”:“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句之诂(“文”)”。
而上述“两边”(解“文”通“志”与得“志”通“文”)的“交互往复”,便构成“阐释之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
如前文所言,“阐释循环”是西方解释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从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以降的解释学大师,基本上都探讨过这一命题。但该命题的基本定义或在西方学术圈内的通行解释却大致不超出古典解释学大师狄尔泰(W。Dilthey)的界说:“为了理解某个语言单位的组成部分的确定含义,我们必须对整体的含义有预先的把握;然而,我们只有了解了部分的含义,才能了解整体的含义。”而西方解释学之“本体论转折”的肇始者海德格尔对 “阐释循环”的重新定位,即,“解释”“不得不活动在领会了的东西中,并且从领会了的东西那里汲取养料”(48) ,则赋予了“阐释循环”以“本体论的积极意义”(ontologically positive significance)(49) 。
钱钟书所论述的“阐释循环”命题,就其出处而言,主要来自于狄尔泰的《解释学的形成》(Die Entstehung der Hermeneutik)及《关于描述心理学和分析心理学的观念》(Ideen uber eine beschreibende und zergliedernde Psychologie)等著述。这就意味着,钱钟书在《管锥编》论《左传正义•;隐公元年》一则中对“阐释循环”的理解,基本是狄尔泰意义上的,或者说,是以西方学界的通行解释为基础的。换言之,钱钟书此时视野中的“阐释循环”这一命题,主要限于方法论而非本体论范畴。
为了准确交待狄尔泰本人所界定的“阐释循环”命题,钱钟书特意引了他的一段德文原文:
“Aus den einzelen Worten und deren Verbindungen soll das Ganze eines Werkes verstanden werden; und doch setzt das volle Verstaendnis des einzelnen schon das des Ganzen voraus” (50)
(“通过一个一个的词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就可以使一部作品的整体被理解,并且这种对个体的把握,其实已经建立在对整体的理解的基础上。”)
又引了帕雷松(Pareyson)在《美学:构成的理论》一书中的一段意大利文原文作补充:
“La parte e contenuta dal tutto solo in quanto a sua volta lo contiene; e il tutto e formato dalle parti solo in quanto le ha esso stesso reclamate e ordinate” (51)
(“一个局部被总体包容,只是因为总体将之包容;总体由多个局部组成,只是因为总体本身将之有序而整齐地拥有。”)
在充分把握狄尔泰所谓“阐释循环”的“原义”的基础上,钱钟书借助本土诗学话语,对此命题作了重新释义:“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者是也。……正如自省可以忖人,而观人亦足自知;鉴古足佐明今,而察今亦裨识古,……。”值得注意的是,钱钟书以“人”/“我”互观、“古”/“今”互观为喻,说明“阐释循环”这一“局部”(“小”;“末”)与“整体”(“大”;“本”)互动的解释模式或现象。“人”/“我”互观所强调的,乃是自我中心意识的突破,也即超越“我障”。“古”/“今”互观所强调的,则是今人或现代人对古人或古代文献的“同情之了解”。而人/我、古/今互观的结果,也就是哲学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谓的理解者(自我;今人)与被理解者(他者;古人)的“视野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