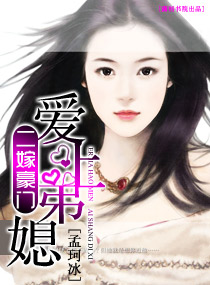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因乎政俗,齐乎人心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30)这种论调可说是开了前述十教授“本位文化”宣言的先河。换句话说,三、四十年代的“本位文化”论,也许不过是晚清“国粹”思潮的老调重弹。它当然并非是文化思想贫乏的表征,而毋宁是说明了如何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调整好中国文化的前行步态,是一个自19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后发现代化”国家如中国的文化难题。
可以看到,无论日本还是中国的“国粹”思想,都与“民族性”、“独立性”、“特性”之类概念相关联。而对这些概念的强调,其实都体现了对文化“特殊性”的执着与坚守。因为,人们谈“民族性”也好,谈“独立性”也好,谈“特性”也好,都是在两种以上文化相碰撞或相比较的背景下进行的。而人们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也就是强调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各有其“特殊性”,不应也不容混同。人们倡导文化的“独立性”,往往意味着应在外来文化冲击下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人们谈论文化的“特性”或“特征”,则常常会开出一张本民族特有之物(即,能体现文化“特殊性”之物)的清单,如日本的“国粹”论者主张“和服倭屋不可废”,而晚清“国粹”派则力斥“醉心欧化”者欲废“汉字”、“中医”之非。(31)
一般而言,某一历史时期中的强势文化常常被视为“普遍性”的体现,作为回应,以弱势文化守护者自命的人往往习惯于强调本土文化的“特殊性”。从十九世纪后期以来的种种东西文化观来看,西方文化为人类文明之楷式的论调不绝于耳,如“全盘西化论”的代表陈序经就认为:“西洋的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它是世界潮流的趋势。”(32)再从当前全球范围内的文化讨论来看,诸如“本土化”、“保持文化特殊性”之类取守势的观念,总与发展中国家或西方世界中相对弱势的国家“形影相吊”。(33)而象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则以其基于强大国力和全球影响力的民族自信,热衷于强调美国文化的“普世性”或人类文明的“美国化”。(34)
前文已指出,钱钟书看待中西文化的基本立场是尚“普遍性”而轻“特殊性”。但钱钟书在文化领域所宗尚之“普遍性”乃是指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或诸民族文化本质上是相通的,而不是指某种文化如美国文化具有“普遍适用性”。例如,他曾指出,那些热衷于谈论“东西文化特征”的人常说“某东西代表地道的东方化,某东西代表真正的的西方化”,而“真实那个东西,往往名副其实,亦东亦西”。譬如“中国旧文学中有一种比兴体的‘香草美人’诗,把男女恋爱来象征君臣间的纲常,精通西学而又风流绮腻的师友们,认为这杀风景的文艺观,道地是中国旧文化的特殊产物,但是在西洋宗教诗里,我们偏找出同样的体制,只是把神和人的关系来代替君臣了。中世纪西洋文学中尤多此类比兴的作品,但丁就是一个刺眼的例。”钱钟书进而总结说:所谓“国粹”或“洋货”,往往并非中国文化或西洋文化的“特别标识”,而是和“哈吧小狮子狗”的身份一样,“亦东亦西”。(35)这一观点与钱钟书所谓“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以及“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等文学观文化观,均表明钱钟书所宗尚之文化“普遍性”并非意指某种文化具有“普遍适用性”,而是意指诸种文化本质上是相通的。这就意味着,钱钟书尚“普遍性”的文化立场有别于“文化普遍主义”(cultural universalism)。“文化普遍主义”的特点是首先设定了“某一不容置疑的基本价值标准”,“一旦遇到论争”,它确信能够以此为依据找到“解决办法”。而其所设定的“普遍标准”,“看来象是某一种特定的文化(如一种宗教,一种哲学,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36)这种以“某一种特定文化”为依据设定“普遍标准”的观念模式显然有悖于钱钟书沟通东西文化以寻求“普遍性”的基本思路。
由于钱钟书“尚普遍性”的文化立场乃是着眼于诸种文化本质上的相通性,因此,它就不但与“本位文化”论者针锋相对,亦与“全盘西化”论者所谓西方文化为普世文化的论调“貌同心异”。因为,钱钟书固然强调“国粹”并非中国文化的“特别标识”,而对所谓“洋货”,亦持如是观。并且,在钱钟书看来,那些推崇“洋货”而鄙薄“国粹”的“欧化”论者,往往犯有把新旧之别来替换中西之别的逻辑错误,他们“说到新便想到西洋,说到西洋便想到新,好象西洋历史人物,跟他老人家一样的新见世面”。钱钟书进而指出,“具有这种心眼来看文化史,当然处处都见得特点了。”(37)
那么,钱钟书强调诸文化相通性的立场及其以“求同”为特征的沟通中西的文学研究模式(38),是否如一些西方汉学家所怀疑的那样有抹煞“文化差异”之嫌呢?(39)笔者以为,钱钟书并无意于抹杀“文化差异”或东西方文化各自“特征”的存在。只不过,在他眼中,中西文化或诸文化之间,“同”固然远大于“异”,且表面之相异不掩本质之相通。钱钟书曾指出:“中西对象不同,理论因而差异,我们不该冒失为特点,因为两种不同的理论,可以根据着同一原则。”他举例说,“中国文章讲平仄,西洋文章讲轻重音;西洋诗的禁忌,并非中国的四声八病,而两者遵守着声调和谐的原则;虽不相同,可以相当。”(40)这就是说,“讲平仄”与“讲轻重音”这两种中西修辞学上的“不同理论”,乃是“根据着同一原则”,可算“貌异心同”,因此,不应将这两种理论“冒失为”中西方文评的“特点”,也不应将它们视为中西文化中“特有”或“独有”的东西。(41)
第三章 “善沟夷夏谈何易”:钱钟书的中西文化与文学观第15节 “出位之思”与文学研究(1)
如果说,钱钟书对“中体西用”论、“本位文化”论等保守的中西文化观所作的反思,为其重中西会通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思想依据,那么,他上承章学承为学贵“通”之说所提出的“打通”论以及有关“比较文学”的论述,则显示了他对会通中西的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自觉。
钱钟书《游雪窦山》诗云:“天风吹海水,屹立作山势。……我尝观乎山,起伏有水致。……乃知山与水,思各出其位。”(《槐聚诗存》)笔者以为,钱钟书文学研究意识的基本特征,就是能够看到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的相通性,就好比山有水致,水有山势,因此,我们不妨以“出位之思”来概括其文学研究意识。
1、“打通”论溯源
钱钟书在文学研究中常常以“外来之观念与本国之材料相参证”,不少研究者因此将他定位为“比较文学”学者,并致力于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考察他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成就与贡献。钱钟书本人对此颇不以为然,他在介绍《管锥编》的研究方法时就明确指出:
“弟因自思,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而是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弟本作小说,结习难除,故《编》中如67-9,164-166,211-212,281-282,321,etc。etc。,皆以白话小说阐释古诗文之语言或作法。他如阐发古诗文中透露之心理状态(181,270-271),论哲学家文人对语言之不信任(406),登高而悲之浪漫情绪(第三册论宋玉文),词章中写心行之往而返(116),etc。etc。,皆‘打通’而拈出新意。”(42)
这段话首先表明钱钟书提出“打通”论,乃是为了将他的研究方法区别于“比较文学”;其次表明,“打通”的目的,乃是为了“拈出新意”;还表明,“打通”研究的层面有三,一是在国别文学关系上打通“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一是在文类上打通“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一是在学科关系上打通文学与哲学、心理学等各人文学科,如《管锥编》中“阐发古诗文中透露之心理状态”、“论哲学家文人对语言之不信任”等四例即属此层面。而对于“打通”中外文学及各人文学科的可能性,钱钟书则早有论证。他的著名论断“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为裂”,即为“打通”中外(西)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他所谓“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43)的观点,则显明了各人文学科的相关性,而正是基于此种相关性,以“打通”各人文学科为特征的文学研究才成为可能。
笔者注意到,钱钟书将打通“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的方法解释为“以白话小说阐释古诗文之语言或作法”,而究其实,则是以“白话小说”与“古诗文”的“语言或作法”相类比、相“参证”。例如,《管锥编•;毛诗正义•;卷耳》一则(67-9),即是以章回小说“话分两头”或“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述手法,说明《卷耳》一诗“男女两人处两地而情事一时”的意境;又如,《管锥编•;左传正义•;杜预序》一则(164-166),乃是以“后世小说、剧本”中的“对话独白”体,拟之于左氏在历史叙事中“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的“代言”方式;再如,《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鲁仲连邹阳列传》(321)一则,为了说明“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一语中的“乃今然后”四字看似“堆叠重复”,实则“曲传踌躇迟疑、非所愿而不获已之心思语气”的修辞效果,乃以《水浒》第一二回:“王伦自此方才肯教林冲坐第四位”一语中的“自此方才”四字与之“连类”。
如果说,“打通”“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实则是指“白话小说”与“古诗文”的“语言或作法”相类比、相“参证”,那么,与此相应,“打通”“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则主要应指以“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相类比、相“参证”,这在《管锥编》以及《谈艺录》、《七缀集》等其它钱著中触处皆是:如以西方现代主义流派“达达派”所创的“同时情事诗”体,《堂•;吉珂德》第二编第五章中的一个情节,《名利场》中有关滑铁卢一役的“结语”,与中国古典文学中常见的“人异地而事同时”的情境相类比、相“参证”(《管锥编•;毛诗正义•;卷耳》);以华兹华斯、雨果、施莱格尔等浪漫主义诗人以“向不入诗”之“字句”、“事物”采取入诗的作法,与唐韩愈、清末黄遵宪等中国诗人的“以文为诗之意”相类比、相“参证”(《谈艺录•;三》);以大仲马等西方作家擅于在“每章结束处特起奇峰”的小说笔法与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回末起波”的手法相类比、相“参证”(《七缀集》之《读〈拉奥孔〉》)。
前文提到,钱钟书提出“打通”论,乃是为了将他的研究方法区别于“比较文学”。那么,“打通”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打通”研究所包含的研究层面要比“比较文学”研究丰富。比较文学研究主要是指超越语言、国界或学科界限的文学研究,而打通研究则不仅包括语言、国界或学科界限的超越,还包括对文体界限、古今界限的超越(44)。因此,从研究层面来看,“打通”研究可以说是涵盖了“比较文学”研究。其次,从方法论的角度着眼,“打通”研究之“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这一层面虽然近似于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但也存在着微妙差异:比如,对中外文学的“打通”研究往往止于罗列“外国文学”现象以印证“中国文学”,而“平行研究”则还需要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分析,或辨别异同,或双向阐发,或总结出普遍性的规律。再次,从目的论上来看,“打通”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固然都试图通过越界对话以求有所新发明(“拈出新意”),但一则专务“求同”(45),一则兼重辨异,差别是显然的。
如果从中国学术史的角度着眼,钱钟书的“打通”论与传统学术思想中尚“会通”的观念可谓一脉相承。回顾学术史,从刘知几的《史通》,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到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