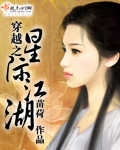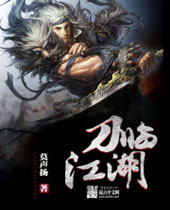江湖中国-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假若还解决不了,那就再转托一次,委托“关系的关系的关系”,循环往复以至更多……将大量人员牵连进来产生链式的社会合作模式。在合作中,凸显一种链式人际关系:A→B→C→D……你传我,我传他,正是关系网突破了家族窠臼,扩大了人们交往的空间。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家族主义文化,从“薪火相传”价值观到“宗法”制度,再到经济生产组织,都离不开家族二字。至现代以后,生活格局改变了,国际环境开放了,传统家族生活解体了,唯有家族主义文化延迟落后。在此背景下,出于家族胜于家族的关系文化应运而生,适时地扩展了国人交往的范围,大幅度增进了社会交换。换言之,国人不依靠西方式的契约和法律,而依靠旧式人际关系的反复传递,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以达到个人扩展交往的目的。从这个角度看,关系网和关系社会在中国必然会发生,而且会长期延续下去。
关系传递突破个人熟人的局限,使原本不容易办成的事变得可以办成。这种功能把传递链上所有人的小关系网串联起来,变成一张硕大的网——复合关系网,产生组织人数上的“规模效应”,使得小关系网望尘莫及。关系网有能力与当代法治相抗衡,譬如“递条子”、“打招呼”通达法院和检察院,死刑能跑成死缓,无期能跑成有期,就因为它在小城市组织的人群规模和累积的权力,与宪政和行政程序等量齐观,形成一个对峙的局面,形成一个“体制外”运行的惯例制度。关系网最大的江湖属性即在于此。
打折扣,传递加速衰减
我们看一个典型例子:
甲受他人委托办一件事,请乙帮忙。乙通常要问:“他同你什么关系?”
甲的回答通常有两种:(1)“他是我很好的朋友。请将这件事当做我的事来办”。(2)“他同我一般关系。能办就尽量办,办不了就
算啦”。
此处看到,不同关系享受不同待遇,关系传递在传递过程中可能被打折扣。
作者跟踪大量实例,发现如下规律:
经熟人介绍,委托间接的熟人办事,效率和成功概率都比直接熟人办事降低,不论具体路经和情景,只要不请客送礼,大势必呈衰减。
如果再辗转二三道,关系被转托两次以上,几乎只剩下情面上的应付和敷衍,办事效率极低,实际上经常办不成事。关系在传递过程中,它的动力逐渐减弱,办事效率和成功概率呈加速衰减趋势,此处称之“传递加速衰减”。“加速”是指衰减趋势呈几何级数,越衰越快,而不止数学级数的均匀衰减。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没有金钱礼物作推助剂。没有金钱的传递,称自然传递。
假使一切用金钱作推助,凡事靠利益驱动,经关系转托达到的程度几乎无限,转托的次数也无限。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这涉及到一种制度下交易费用问题,假如交易费用大到超过事务价值本身,这样的行为是无价值的,不能凡事都靠金钱开路。金钱开路,仅限于吃小亏占大便宜,譬如行贿。以市井头脑的精明计算而言,除非特别重大事项,没有人请客送礼会不计成本,成本不能大于办事的价值。除了政客和商人,老百姓要办的事都是日常生活小事。既然要计较成本,托人办事打折扣便是大趋势。市井生活的期望值,总是以收益来确定成本,决不做亏本生意。收益固定,所以成本最好也固定,托N次最好跟托一次开支差不多,因为事情还是那件事情,它的价值不变。所以,在没有或者有限利益驱动下,关系的自然传递呈现一种渐次衰减规律。所谓“没有利益驱动”,即纯粹基于人情关怀,纯属情面作用的关系越传越弱,辗转多次后跟没委托一样,几乎办不成事。不可能转托一百人后还能办事。不论如何长袖善舞,都需承认关系是有限的,长袖之长,终有鞭长莫及之时。
为什么衰减?
属于直接关系的两人处在义务压力状态,当甲求乙办事,乙不能直截了当地拒绝。这是习俗,是一种惯例制度,即便不情愿也要勉力为之。习俗压力被表述为碍于情面。但是,当丙帮助乙的朋友甲——丙并不认识甲——办事时,这种义务状态立时松绑,由“义不容辞”变成一个问号:“那人跟你什么关系?”潜台词说:你的事情麻烦我尚可;别人的事也来麻烦我,那得看方便了。
这个问题很重要。此时,乙已经基本松绑,原本由关系网惯例制度赋予的压力此时步入悬疑区。如果甲与乙关系密切,丙愿意承担的义务就多一些,办事卖力点;如果甲与乙不那么密切,丙就择顺水推舟态度,方便就做“顺手人情”,不方便就不了了之。
这个问号显出一种微妙意味:关系被传递到第三人后,第三人的动力取决于第一、二人的亲疏。前二人关系亲密,第三人就积极;前二人关系一般或疏远,第三人态度就消极。这是在自然传递下的情况。假若再传到第四人,规律还是一样,他的态度比第三人更加消极。总结下来,纵使关系不停传递,办事的动力却一层层衰减,变得越来越应付了事,越来越像走过场。对于丙而言,甲(原始委托人)纯属于陌生人,无论甲、乙两人关系何等亲近,甲和丙的关系都不可能比和乙更亲近,因为丙只认识乙,不认识甲。未曾谋面,能认真吗?能办事完全看在乙的面子上。因此,丙帮甲办事时的精气神儿,超不过帮乙的情形。至于丁、戊……的态度,就一个比一个更消极。这就是关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传递衰减现象。托来托去,最后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关系传递一次,效率究竟衰减多少?加速的速率是多少?
根据作者对有限样本的观察统计,在自然传递条件下,假设没有利益驱动,关系传递一次后,效率衰减大约一半,成功率也降低一半,这里模糊地表述为50%,当然这只是近似值。继续推理,关系转托一次成功率,大约相当于直接认识人效率的50%;再转托,再衰减,效率只有(50%)2=25%;转托第3次,只剩下(50%)3=12。5%。这是一个估计近似值。
关键是,当事人托人前那一瞬间的思维也依赖粗略定量,托还是不托,基于当事人的模糊计算。人们总是先估计某条线索成功的可能性,判断可行,然后选择委托的关系链。譬如,有人翻盖旧屋要办手续,他决不会向一位毫无路子的人委托此事,他会找建委式房产局的人。期望值为零的事情不会开启委托,毕竟欠人情于己不利。又譬如,办“农转非”肯定首先要找公安方面的关系,而不会是找医院方面的关系。所以,“万一”的事情没人做,“百里挑一”的也没人做。一般来说“十之其一”也就是10%概率的事情有人做,而且是多数人会做。10%也就是大约三次传递后的成功率(12。5%),它意味着还有可能性。对于一般人来说,事情辗转三次以后还办不成,基本上属于没指望。不如改弦更张,另寻门路。改弦更张本身,反映了传递的前景是有尽头的,这种思维方式不打算追求无限,也无能力追求无限。这是关系网的局限,关系网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管理的极限仅仅是一个小社区和小行业,它的人口规模是由三至四次传递到达的人口规模,正如上面谈到:这大约是50万人口。考虑到估计衰减率估计值的误差,更谨慎地说应该处在30~70万人口之间。一个完全靠关系运作的社会,人口至多30~70万人口。
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作为一种由家族主义文化蜕变而来的开放网络,关系网运行依赖“面对面”的相处,“面对面”是关系网的支柱,也是其运行的引擎。搞关系开口闭口不离见面“应酬”,一旦抽掉“面对面”,关系网运行就遇到障碍。俗语说:“人一走,茶就凉”。人走了,没了应酬,所以凉了。以上述甲、乙、丙三方为例,丙与甲因未曾谋面,所以缺少“面对面”基础,替甲办事的信念和做法都有障碍,效果必然衰减。这还仅就传递一次而言,若传递两次以上,困难就更多。常言道:“关系隔几层,办事不容易”。
怎样才能不衰减?
一是利益驱动。通常送礼物、红包,且礼分量足够。所谓足够,既看要办事情难度,也看事情对自己的价值。送礼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关系转托的衰减,逢山开路,遇河搭桥。民间也称这种办法为“金钱开路”。投下的金钱增多,就要盘算这趟办事的价值,不合算的事情没人做。
二是通过努力,变间接关系为直接关系,这叫“关系引荐”。只要牵涉重大或长远利益,譬如寻找官场靠山、投资办企业,上项目弄批文,就值得费功夫,把朋友关系弄成自己关系,然后求得办事不打折扣。此法与前法大同小异,都要请客送礼。不同之处,这种方法要经中间人撮合,大家“见面”。相反,前法不一定见面。前法基于送礼,此法却基于请客,还加送礼。同是请客送礼,道理不同。有见面,便开始“面对面”交往,相互关系在渐渐认同中发展。
不同城市的关系生态
按一般习惯,城市人口千万以上称特大型城市,百万以上称大型城市,50万上下称中型城市,20万以下称小型城市。人口以城区为限,不包括周边农村。
关系网的运作模式和兴盛程度都与社区的人口规模有关联,由于关系传递的衰减现象存在,关系系统的整合能力仅限50万人口以下。一旦城市人口规模超过50万,关系网的控制功能随即衍生两种趋势:一退出社会舞台,由城市公共体制(宪政和市场)取而代之;二转入50万人口以下的社区(譬如城区、街道、居民区)或者行业(譬如文教、交通、公安、商业、制造、服务行业)。
在50万尤其在20万人口以内,关系网可以从容地组织、控制城市社区生活,借能人口话说:“只要在本城,哪里都可以找到熟人”,或者更狂妄地说:“在本地,没有办不成的事”。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在中国的中小城市推行法制和现代市政体系非常艰难,主要阻力来自全城居民业已形成的关系网络和惯例制度。要推行现代城市制度的社团化、法制化,原有关系网络就会毁坏,这不仅改组原有居民互助体系,更涉及利益分配重新洗牌,触动既得利益者的神经。
人口超过50万后,关系网控制力就开始削弱,也削弱了人们托关系的意志。此时,城市生活出现关系真空,能托关系办的事情越来越少,不可避免要寻求一种新体制作为替代,而合适替代物只能是宪政体制——社团、法律程序和市场经济。城市越大,补偿需求越大。随着补充的宪政成分增加,它就与旧的关系网产生冲突。当城市超过100万人口,关系网体制就无可奈何的退出主导地位,而让位于正式规则。
这里,作者谈一谈对中国南方地区,主要是福建和广东的一些城市的印象,同时以特大城市上海、北京为参照。本书主要是以这些南方城市城镇为观察样本写成:
特大城市:上海、北京、广州;
大型城市:深圳、福州、厦门、佛山;
中小型城市:东莞、惠州、肇庆、汕头、潮州、江门、建阳、泉州、漳州、莆田、三亚。
上海
上海搞关系的风气相对最淡薄。有事找市场或找里弄,而非找关系,是普通市民的正常心态。普通上海人也有托关系的时候,频率比较低,不当作生存依靠。如果是土生土长的老居民,或者握有实权的权贵,搞关系的便利多于新移民。但上海地域相当广大,即使老上海也觉得找关系很困难,以前的同学、相识、熟人平时很少来往,毕业工作后数十年杳无音讯。这个城市的巨大规模以及殖民地时代延续的市政传统,限制了关系网的潜力。在全中国,上海人最少诉求关系网,这个事实既起源于超大规模城市人口,也起源于租界的公共管理传统。在改革开放以前,上海的城市社区服务功能最健全,求助于关系的事务也最少。
北京
北京也很相似。除非是特权阶层,在北京营造关系网也不容易,原因同样是地方太大了,从东到西几十公里,熟人之间平时难得串门,“面对面”互动模式难以维持。除此之外,北京又是一个新移民城市,市民赖以做关系17种人——亲戚、同学、朋友等等多在原籍,到北京后缺乏人际关系基础,这也决定了移民们营造关系网的困难。所以,在北京能够附着关系网生存的主要属三种人:权贵、老北京和老移民,而且局限于小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