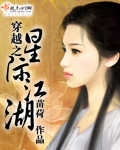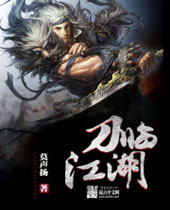江湖中国-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网的周边形成一道泾渭分明的界线,它就是“自家人”理念,它是关系网的边际。“自家人”和“外人”两个概念关涉两种截然不同的伦理体系和游戏规则:“对待‘自家人’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外人’就像秋风扫落叶”。
什么是自家人?什么是外人?
自家人就是关系网里面的人,特别是关系圈里层那些亲近人;外人就是关系网以外的人。二者之间有一片过渡的模糊界区,界区又有三道概念作防线——狭义、中义和广义,形成不同的规矩和语言环境。狭义“自家人”就是自己家族的人,这是辞源本义,是家族主义文化的起点。若是乡里有械斗,当然是帮亲不帮理,同姓帮同姓。中义“自家人”是认识的熟人——哥儿们、姐儿们,平日来往频繁,有事情相互帮忙。广义“自家人”是本地人,或延长到操同一方言的人群。譬如潮汕人听到乡音便称“自己人”,热情异常。在泰国,讲潮州方言就可以得到潮州人照顾,可见潮州人乡谊之盛。凡称“自己人”必定待遇不同,遵循的规则不同。一旦界定“自己人”,脑海马上进入特定语境、价值体系和情感体验。“自己人”有优惠,有互助,遇到“自己人”与外人纠纷要先帮“自己人”,而不论是非曲直。
相反,如果对待自家人的基本态度是“照顾的义务”,那么,对待外人基本的态度就是漠视和排斥,这种二元伦理的本性是排他。
北方人常说南方人排外,尤指广东人和上海人。改革开放以前,外地人在广州以普通话问路通常没人答理。改革开放伊始,外地人到广州高第街买东西通常在价格上要吃亏,若问价后不买,粗野的商贩绝不轻易放过。在前现代化时代,南方地域多排外。沿着海岸线看中国地图,北至上海,南到广西,排外心理十分普遍,南方地方文化普遍具有排外性格。
譬如,闽南人对闽南以外地方一律称“北方”或“内地”,称闽南人以外的所有国人,包括本地讲普通话的移民,一律称为“北方人”、“北仔”或者“内地仔”,甚至歧视称“北仔戆”,即北方傻。一次,两个小青年骑摩托车不慎撞倒了一辆自行车,二人起初面带愧色,不想被撞人踉跄站起来,用北方话嘟哝一声“他妈的”。两个小青年不干了,交换了一下眼色低声道:“北仔戆,揍不揍?”另一个答:“揍!”两人转身回来,又对骑自行车人拳打脚踢一顿,随即逃之夭夭。俩人能瞬间达成一项打架默契,关键在歧视理念背景。按他们想法,本来低人一等的外地人,撞了也白撞,我能面露歉意已经不错了,还敢骂我娘,绝饶不了你。
以上,我们分别谈及关系网的三条“有别”原理:“亲疏有别”、“上下有别”和“内外有别”。概括来说,三个“有别”原理是一种广义的费氏差序格局——即由异质性和特殊主义原则建立的格局。半个世纪前,费孝通总结了中国乡间社会的特殊主义:差序背后的梯度性和异质性,而不是现代法治社会强调的平等、均一和普遍主义。而这种“有别”差异在中国的前现代社会是普遍的,不局限于乡间家族,更涵盖江湖,包括帮会和关系网。
见面熟人二百余
前面谈到,关系网由亲戚、朋友、同学、校友、街坊、邻居、结拜、世交等十七种人脉组成。不同背景和个性的人,关系网规模大小肯定不同,它标志了个人的活动能耐。老实、不善交际、好清静的人,关系网肯定小;活动能力强、有本领、长袖善舞,关系网肯定大。然而,不论个人关系网有多大,它总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无限扩张。一个人在河南呼风唤雨,不可能到河北还能搅事,按行话来说:“这不是他的码头”。一个普通人的“码头”,可能遍及一个小城,但不可能涵盖一省。
关系网迥异于现代法人团体组织,后者的规模在理论上没有限制。以跨国公司为例,它究竟可能容纳多少员工,在世界法律制度上没有明确限制。譬如,当今麦当劳加盟连锁店全世界总数已达到三万以上,员工总数过百万,坐落在美国伊利诺斯州Oak Brook总部的老板们纵使一辈子不停地巡视,也不可能逐一莅临旗下分店。然而关键是,不去分店还能赚钱,以中国文化背景来看,真是绝活。在那些靠关系起家的中国老板眼里,麦当劳等跨国公司不啻一宗奇迹:老板投资一块不打算去的地方,居然有本事财源广进,简直匪夷所思!擅长裙带关系的中国小老板坚信,做生意第一靠自己亲力亲为,第二要靠任用亲信来弥补不足,譬如老婆管账,小姨子管货,兄弟管客户。每有新人开店,总有老行尊善意规劝:外人不可信,否则权力旁落外人,早晚被人架空云云。家族人手不够用怎么办?要么维持生意现状罢了,要么去“契”——即“干”几个儿子,或者拜几个把兄弟充数。这实际上是两种组织观念的差异:企业组织到底是依赖面对面的熟人,还是不需要面对面的熟人,只要铁板板的制度。
“面对面”是关系运作的局限,它决定了关系网的规模十分有限。
如何寻找关系网规模的代表样本呢?我们以现代团体类推。一个团体,由章程、契约、证书设定界限,成员角色明确。欲调查团体规模,可以观察该团体的会议,会议是团体的集会,要详细了解团体大小和成员构成,到会议室里一目了然。但是,关系网不同于现代团体,它不开会,没有纲领、章程和纪律,没有成员证书,没有合同契约。实际上,关系网只是一个松散的、边界模糊的人群,它以自我为中心,从不以任何集体为中心,每个人的关系网各自不同,相互之间通过人情纽带编成一张虚拟的“网”。也就是说,社区内部同样一拨人,在我看来是一张网,在你看来又是另一张网,在他看来则是他的网,网与网不同。它是虚拟的,属于各自内心的知觉,甚至是康德式的先验图式,只有网中流动的利益是客观的。关系网是社会心理的,没有物理凭证。
关系网虽不举行会议,但总是有一些场合“召集”成员出席“会议”。对于有志于观察关系网的人来说,结婚吃喜酒是一个特殊机会。除喜酒外,拜年、婴幼儿满月周岁、丧葬等民俗都可作关系网集会样本。以拜年来说,春节期间的拜年人,可涵盖家庭大部分关系网成员,尤其地位低于本家长的成员,一般来说关系近的集中在前几日,稍远的集中在后几日,但凡拜年的都属于关系。相比较而言,依然以喜筵场合下熟人到得最齐,其数量最接近一家一户关系网。下面我们以福建南部地区为例,以喜筵宾客来解读关系网。
在闽南社会,喜筵依例办两次,一次男方,一次女方。个别的,也有由双方家庭联袂操办的,宾客总合双方亲戚熟人。我们只讨论单方操办的情形。
闽南人的婚俗,沿袭古礼之“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聘、请期和迎亲。改革开放后,老规矩有所淡化,剩下来主要是“吃酒”:宾客奉分子红包,然后按固定菜谱饕餮一顿。至于纳彩、问名、纳吉在城市很少人奉行,纳聘有部分人遵守,请期的人较多。至于喜筵,精髓绝不在菜肴,而在排场,摆桌越多,人气越旺,气派就越大。那么一般喜筵请多少桌,来多少人呢?近十年来,作者发现闽南地方普通市民喜筵大多数在20~30桌之间,这个数据采自许多酒店管理层和市民口述。以平均每桌10人计算,宾客人数约摸200~300人。这相当于个人关系网规模的约数。
然后要做一点校正,剔除其中不属于关系、根本不能办事的人,譬如孩童和老人,以及那些凑热闹的间接关系——譬如“关系的关系”、“亲戚的朋友”、“熟人的熟人”,这部分来宾与新人并不熟悉,将来不能直接互助,依赖别人介绍。依闽南习俗,喜筵以父母名义操办,是“某府喜筵”而非“某人喜筵”,这是一种家族主义文化,是家族里的大喜事,部分宾客属于父母朋友或其他亲戚熟人。剔除这部分人后,剩下来基本上是新郎官个人关系。对普通市民而言,这部分人平均大约在200人左右。
换言之,个人关系网的平均规模大约是200人。这个半定量数值虽不精确,但勾勒了关系网的大致规模,决定了关系网作为一种组织体制在制度上的前景,最终制约了关系网不可能成为一种开放社会。通俗说,搞关系搞不出现代化,因为它才运作了200人,这是关系社会的天限,尽管改革开放初期关系网大有用武之地,但它必然会被现代制度代替。以200熟人为中心,经过人际传播的层层传递、引荐,重新配置资源与合作,最大也就能涵盖数十万人的规模。关系网繁荣兴盛之地,总是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或城镇。50万人口这个约数与200人平均关系网有内在联系。在中小城镇,关系经过介绍人三传两递,就可以通达本城任意角落。常听人说:“咱们这地方真小,说起来都是熟人。”相反在1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不可能找着这种“遍地熟人”的感觉,茫茫人海偶然遇着一位旧识,直可比古人“他乡遇故知”,其欣喜丝毫不逊色。在大城市,尤其对于大城市的新移民,因为熟人太稀少,托关系的难度也增加了,这个格局抑制了作为城市主体的新移民们利用关系网的活动。譬如北京和上海,新移民最难搞关系谋取特权。
通俗说,城市越小,关系越好搞;越大,越难搞。关系运作难度与社区规模呈反比。
关系传递:寻觅熟人的熟人
过去几十年来,经常发生如此这般凡人小事。你办一件事情,遇到难度便要托人,如果自己的熟人当中无人胜任,就要委托熟人再寻找关系,然后前赴后继,一直请客送礼推动下去。譬如,早年出国办护照不容易,你跟出入境管理处不熟,便可能找公安局其他部门的朋友:“最近要出国办事,你跟出入境管理处熟不熟?”如果熟,这事交给他去办,事后你负责答谢。这就是关系网默认的社会规则。申领护照本来是你的权利,但是改革开放初期,诸多法律制度尚未建立完全,公共制度的交易费用高得惊人,于是个人保障权利不光靠法律,也靠关系。直接关系不行,就靠间接关系。老江湖道:“有关系要上,没有关系创造关系也要上”。这不是俏皮话,而是江湖的真谛。
在中小城市生活,市民都需要托关系,极少例外。这些托关系情形,又可分成两类:一类在自己的熟人小关系圈内就可办成;另一类直接托熟人还办不了,须请求熟人转托他们的关系才可办成。将事情通过熟人转托他们熟人的过程,这里称作“关系传递”。前面说过,普通人的关系网规模一般在200人左右,且因职业、家居等原因集中在职业、居地的周围。譬如,教师的关系网多集中在教育界,艺人的关系网多集中在娱乐圈,警察的关系网的多半在公、检、法,东城区居民在东城认识人多……这是由生活圈子及其“面对面”交往性质决定的。与此相反,现代社会生活的特点恰恰是突破狭小群体,实现更大范围的生存合作,什么都讲究一个“大”字,大经济、大合作、大循环、全球村。在哲学上,读者可以将关系网的发明和诞生理解为全球现代化的一条岔路。现代制度、关系网制度都诉求突破传统家族,扩大社会合作。开放社会和现代宪政制度是一个世界通解,关系网是一个儒教特解,由儒教家族主义制度蜕变出的特解。这是关系网的特征,对家族视野而言,它是外向型的,是努力超越家族的。为什么拉关系?就因为家族帮不了忙。希冀通过关系网承办的事务首先是外向的,全方位的,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幼儿入托涉及幼教,子女读书涉及教育界,购房涉及地产和家装行业,看戏涉及文化界,看病要有医院熟人,买便宜货跟商家打交道,出国跟公安局联系,开店办厂要工商税务有人照应,开发房地产要跟规划局、土地局打交道。一个普通人不可能认识如此多的熟人,如果正统渠道走不通,就只有托人。
两相对比,问题就来了。
一个人认识的人有限,而要办的事情无限。所办事务,如果恰好能在熟人中解决,便属万幸;如果熟人解决不了,只好再托人,求助于“关系的关系”,请“熟人的熟人”帮忙解决。从社会学说,这个间接方法等于将一个人关系网带入另一人的关系网,为了一个临时目标,暂时并网运作。此时,假若还解决不了,那就再转托一次,委托“关系的关系的关系”,循环往复以至更多……将大量人员牵连进来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