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墨脱-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轻轻地走上阿尼桥,感受一下过索桥的滋味,桥下激流翻滚,伴着轰鸣,令人目眩,走过桥去又是一派葱郁的森林。
“啊,呀——”两个门巴族女人站在对岸向我招手,人声在深谷中飘荡,非常亲切。
回到木棚内,煮好的玉米糊和土豆正冒着热气,两个女子低着头给我盛了满满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玉米糊。他们三人默默地看着我,时而笑着低语。人与人之间最纯朴的真情此时此刻已融入我的血液中,今生今世我能忘记他们吗?那深情的目光、纯朴的笑容,那充满激情久久回荡在内心深处的歌声……永远无法忘记这一切。
当我又踏上行程,走过索桥,他们三人还站在大石边。我朝他们挥了挥手。几乎同时,他们三人都举起了手,两个女人还向前跑了几步。
“啊,呀……”他们的声音在山谷间回荡,这些我听不懂的呼唤一定是在保佑我,保佑我平安到达墨脱。
9.闯过塌方区
晨雾渐散,气温慢慢升高,布满额头的汗珠滚滚而下。不出意外的话,今天我就可以赶到墨脱县境内最大的一个乡——背崩乡,就可以看见生活在背崩乡的门巴族和珞巴族人了。
三小时后,二号桥到了。深藏于群峰峡谷中的二号桥很孤寂,索桥上的木板残缺不全,桥头的荒草淹没头顶,桥下仍是汹涌奔腾的激流。
我坐在桥头休息了一会儿,让浑身的热汗慢慢冷却下来。穿过峡口的凉风吹拂着索桥两岸的野藤枝叶,红、绿、黄相映的枝叶被阳光、雾气、露水所浸染,水灵灵地透溢出勃勃生机。在这幽深的峡谷中,野藤枝叶的花草竟会如此绚丽诱人,在自然野味的万花万果中穿行,真是一种享受。
我小心冀翼地走过二号桥,前方的路径仍然是上坡,草丛树林渐渐稀疏,一阵阵山风卷着泥腥味扑面而来。我抬起头,发现眼前的树丛突然消失,这座被树丛包裹着的山峰也会出现断层,怎么回事?
到断层崖边一看,我大吃一惊,这是一处大塌方段,边沿还有一股激流从山顶倾泻而来。从高处冲下的水推动土砾碎石朝深谷滚动,平均不到十分钟滚动一次,被泥石流掀翻的大树连根拔起,将整个山峰撕裂得惨不忍睹。垮塌的泥石流跨度超过二百米,我别无选择,必须走过这两百米宽的泥石流,因为通向墨脱的路在塌方段的另一边。
墨脱沿线的地质结构很复杂,在七百里的穿越途中两端山峰海拔由近六千米至一千多米,几百个塌方区就分布在这些路段中。由于每年都有新的塌方段出现,此段根本无法修筑公路,墨脱也就成了全国惟一不通公路的县城。
我提着摄影箱小心地进入塌方段……深一脚浅一脚,极为小心地在泥石流的土砾碎石上慢慢前行,脚下碎石的滚动使我不断滑倒。我一只手深陷泥石中支撑身体,另一只手紧紧握住摄影箱扣,不敢停息。
突然,头顶上的山峰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山上巨石滚动,泥石流汹涌而下,脚下的泥石也在颤抖。我本能地蜷缩在一个巨石后面,泥石流在离我仅十米远的地方呼啸而过,碗口般大的石头从天而降,寂静的深谷变成了炮火连天的战场。
在铺天盖地的飞石中,任何躲闪奔跑都是徒劳的,我将整个身躯和头龟缩在巨石后面,屏住呼吸等待危险过去。
此时此刻,生命在这里显得如此渺小和脆弱。
四周又恢复平静,我探出头来四下张望,眼前的一切已面目全非。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赶快离开!终于,我涉过了塌方的最后一程。轰隆隆的声音又在身后响起,我紧紧地闭上双眼,不忍久看这惨烈的大自然创口。
10。 迷途三号桥
在派乡的时候,人们告诉我,从二号桥至三号桥途中,有一条不易被人察觉的岔路是通向印度边境的。并提醒我要特别注意,如果迷途走上通向边境的路,非常危险。因为在野山丛林中的边境线并未有明显的标志,全是无路径的野山、悬崖、深谷,这是大自然设下的陷阱。
其实,二号桥离三号桥不算太远,二小时就可走到,现在我已经走了三个小时,仍未看见高悬两山之间的三号桥,眼前始终晃动着垂挂露珠的草丛,以及那些不停摇晃着细长身子令人肉麻的蚂蟥。
走着走着,满山冈的刺草丛忽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塌方创口。我不得不停住匆匆的脚步,稳住焦急狂跳的心绪,趴在塌方创口的边沿向四处张望,我走错路了,三号桥绝不可能架设在山崖之巅。此时,焦急、紧张、恐惧一齐朝我袭来。该朝哪里走?
眼前是近五十米高的崖壁断层,要下去是非常困难和危险。即使侥幸下到了崖壁底部,发现无路可走,也再不可能退回到崖壁上端,那我就会被困死在崖壁峡谷中。
我慌忙穿好胶鞋,顾不得脚上正流淌的鲜血,对着崖层和森林失态地大喊起来:“有没有人……”
我那一遍又一遍的喊叫声在丛林中回荡,变调的声音飘过眼前的崖壁,消失在远山中。
在派乡的时候,听当地人说曾经有一个外地人在去墨脱的途中迷路失踪,后来人们推测此人被森林中的猛兽吃了,他的部分行李一年后被人们在一个崖穴洞里发现。还有一个门巴族背夫背着近百斤重的水泥袋,晕头转向地走错了山口,走到离中印边境很近的山峰,瞎转了两天也仅是在峰口处打转,然后他扔掉了水泥袋,只身翻崖爬壁才回到了原路上来。还有很多的人由于各种原因死在了途中
我停止了喊叫,因为每一次喊叫,心灵深处就增加一分恐惧。显然,我有些失去理智,此时此处根本不可能有人出现。
火红的太阳正至中天,汗水浸透了全身,我慢慢地冷静下来,直觉在提醒我,必须按原路返回,别无选择。
我忘却了疲累,忘却了蚂蟥的叮咬,走啊走……很快我的全身爬满了黑色的家伙,有的蚂蟥已经爬上了我的脖子,顺着领口爬在我的胸膛上。这一切我都感觉到了,我不愿在丛草中停留,只是一个劲地赶路,再赶路……
奇迹终于出现了,一条朝山下拐的岔路在丛草中出现了,这是一条从来的方向无法辨清的路,它被丛草掩盖了大半,当我从180°相反的方向靠近时才能较清晰地看清它的轮廓。
我兴奋得几乎大叫起来,天哪!我终于走上正确的直通三号桥的正道。
这一趟误途的折腾,耗去了近五个小时的时光。当三号桥的身影终于出现在我的视线中时,我的精神陡然一振。
三号桥是一座横跨峡谷的桥梁,也是一座钢索桥。桥身高悬在峡谷半腰,静静地横跨在两山间。我轻轻地走上桥面,桥身两端无护栏,高悬的索桥随着我的脚步、随着峡口的阵风在晃动。遥望远方,峡谷的开阔口隐隐可见,幽深的峡谷快走完了。
11.走进背崩乡
走过三号桥还有最后一座桥要跨过,走完四座桥,就是墨脱地区最大的乡——背崩乡政府所在地。此刻,我的心灵深处溢满喜悦,通往背崩乡的最后一座桥也许就在山谷尽头。
走过垭口,走过山谷,山峰与山峰的连接处被一条大河截断,眼前豁然开阔起来。
横在眼前的是一条像野兽般咆哮的大河,这是雅鲁藏布江的下游,河段宽阔,江水汹涌,白浪翻滚。一座长长的铁索桥横跨在雅鲁藏布江上,这就是解放大桥。铁索桥的另一端巨石林立,石林后是一小崖坡,坡的背面又是高耸云端的山峰。在山峰上,一条几百米高的瀑布从山崖裂口处喷涌而出,神秘的背崩乡就从容地端坐在坡与峰之间。
解放大桥是通向墨脱县中心的四座铁索桥中最大的一座铁索吊桥。它横跨雅鲁藏布江,又临近中印边境线,是墨脱地区的运输命脉,驻守着边防军。这是在通往墨脱途中我第一次看见边防军。
从印度洋方向刮过来的风逆雅鲁藏布江流动的方向而上,热风搅和着灼热的阳光,把雅鲁藏布江南北两岸烤晒得滚烫。我几乎脱去了穿在身上所有的衣服,大踏步地走上了大桥。
铁索大桥另一端的高坡上,一个人正注视着我。这是一个穿着短裤、裸着肩背、挎着冲锋枪的边防军士兵。阳光下,这位身材不太结实高大的边防军士兵在桥头的土坡上来回地走着。他黑黝黝的皮肤被峡谷上空的烈日烤出一层油汗,远远望去,就像电视记录片中的“非洲战士”,乌黑的冲锋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见我过来,士兵停住了脚步,他睁大眼看着我,又抬头远望,去寻觅我身后的远山,寻觅隐藏在山中的小径,他似乎不相信我独自一个人走到此处。
就在我登上土坡的那一刻,用石块砌成的圆形碉堡内迅速地走出了两个高个子军人,穿着白色背心,手握望远镜,腰间挂着手枪。
“老乡,你从哪里来,有没有边境证?”一个高个子军人用标准的四川话问我。看来我这身装束已显露出我的身份。我放下箱子、行包,从包内翻出我那包裹得非常好的、能证明我身份的证件递过去。三个军人凑在一起,仔细地检查了我的证件说:“你是一个摄影记者?就你一个人来的吗?”
我点点头。他们三人惊奇地看着我。
“你走了几天了?”另一个人问道。
“从派乡出发,今天是第四天。”我喘着粗气说道。
“你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打开看一看。”军人的口气平缓而冷静。
我蹲下身打开箱子,说道:“里面全是摄影器材和胶卷资料。”
箱内,照相机、胶卷、资料在阳光的直射下光彩耀目。
一个军人拿起照相机连连说,这个相机一定很贵,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我告诉他们是佳能相机,并指着佳能的字母让他们识别。他们都兴奋起来,握住这个相机眯着眼朝远山瞄去。
半小时后,我告辞了这三位军人。他们告诉我,翻过眼前的高坡,就可以看见背崩乡。
我顺着石道爬上石林坡崖,一座小小的土坡遮挡了我的视线,仍看不见背崩乡。转过脸去,脚下的雅鲁藏布江翻腾得正欢,一只美丽的小鸟掠过头顶,朝云端深处飞去,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当我再转过头来时,我被一股潜进肺腑的气息所吸引,这分明是生命的气息,是人的气息。背崩乡袒露的胸怀正散发出炽热的体温向我召唤。我弯着腰朝小土坡的顶端爬去,此刻,我那期盼的眼光已流溢出胜利者的喜悦。
我爬上坡顶。坡顶是一派翠绿的草坪,前面是一排排绿阴葱葱的柏树,用树干搭建的木房,错落有致地坐落在绿阴之间。
我的眼睛模糊了,耳旁全是轰鸣。我闭上眼,瘫坐在草地上,无法睁开沉重的眼皮,头枕着乱草,张大嘴呼吸着背崩乡的空气,我实在太累、太累……
12。 背崩乡的歌声(图)
是什么声音那么美妙动听,从天上飘下来,紧贴我的耳膜?是悦耳的音符?啾啾鸟语?仿佛什么都像,又什么都不是。我仍然掀不动紧闭的眼帘。
过了一会儿,我费劲地掀开眼帘,模糊中,不远处一排排跳动的色彩在起伏,一阵阵悦耳的声音掠过,我慢慢睁大眼睛,原来是一大群蓬头赤脚的小孩,手握树枝、野花,喊着、笑着正朝我跑来……
蓦地,我站了起来,重新背好行包,紧提摄影箱,抬起头,朝着背崩乡,朝着眼前这群孩子们走去
寂静的背崩乡沸腾起来,门巴族人纷纷从各自的木屋内走出,腰挂砍刀、肩背弓箭的门巴族汉子睁着迷惑不解的眼睛看着我,随即友善地向我点点头,咧开嘴笑着;那些门巴族老人移动不太灵活的脚,扶着木栏摇摇晃晃地走下扶梯,弓着背、靠着扶栏望着我,眼睛里流露出茫然与凝重;几乎在每一个木楼洞开的小窗户上,都探出一张张黝黑的脸;有时,小窗户上会同时出现两张紧紧相贴的脸,他们都专注而惊讶地注视着我。
我的到来惊动了这些深居木楼内的老人,也许此刻他们正按照深山内的生活规律,蜷曲在木楼内静静地享受休眠呢。
穿越木楼,穿越村落,我从错落有致的木楼群西端走到东端,又从南面走上北坡,在一大群衣不遮体、蓬头赤足的门巴族小孩的簇拥下,在高脚竹楼间走来走去。
背崩乡的中心地段大约居住了七八十户人,每户人家的木楼建造几乎一模一样。用树木搭建的木楼高高地悬在半空中,笨重的木梯连接敞开的门户与黑油油的湿地,牛、猪就圈养在木楼下。一根根碗般粗的竹子被人们从中对剖开,首尾相接,将远处飞溅的瀑布水引接至村落的中央,解决了全村人的生活用水。
村落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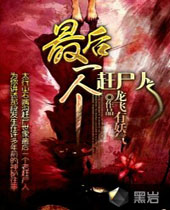
![[快穿]给我一个吻封面](http://www.nstxt.com/cover/0/72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