һ���˵�ī��-��3����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Ŀ־�Ͳ������������ֲݴ�����ĺ�����������ȥ�������Ѿ��ָ���ƽ�����Һ�����������ӡ�Ƚ����Ĵ�Ͽ�����Ҳ��һ�������������������������������У����ж�������������������ﷱֳ��Ϣ�����������������á�������
����6������Խ���ɽ��ͼ��������
�������ϣ����ϣ�ɽ�ȵij���ͨ���Ϸ�����һվӦ���Ǻ����ˣ��ߵ����ڣ�ͨ��ī�ѵ�·�̻�δ��������֮һ���ҿ�ʼΪ�Լ���ʳ����ˡ����м���ѹ�����ɣ���֪�ܷ�֧����ȥ��ÿ�춼�ڳ�ѹ�����ɣ�������ζ���Ǹ��տ�ȴһ�㲻�Զ���ɽ�����Ϫˮ���˲��٣���ʱһ�����ȵö��ӷ��ͣ��ʺ��Ը�ɬ���̡����廹û�г�������������ʮ����ص����Ӻͱ���ѹ�ڼ���һ��һ����Խ���ߣ��ҳ������������Լ�����˴�ĵ������������ŵ���������
������ʯС�������Ͱ��Ĺ�ľ���֣���ɽ���������죬�ֿ�ʼ��ɽ�ˡ���
������ɽ��ʯ����ʵ����һ����������ˮ��Ϫ������������ȫ�ǹ�ľ�Բݣ�ÿǰ��һ����������������ץ�����ߵ����٣����Ź��ڵ�ʯ�黺�����ϣ�ӭ����к����ˮ��ûС�ȡ����͵�Ϫ���Ȳ���վ������������ֻ�ò�ͣ������������
��������ɽ������ǰһ��ãã���ҷ����а���˳������ʪ������������ֱ������������Զ����ƣ�ȫ���ɳ����������������ú���Ϣһ�������
�����ž���ɽҰ�·�Ҳ����һͬ��˯������������ʪ�����Ĺ���������������������
����ͻȻ�����׳���һ������ʹ��һ�������Ҳ��������ʹ����һ��������С�����ڲ��������С�������һץ����һ����ɫ���������棬Լ�����׳�����
��������ʲô�棿�������ڲ�����ʹ������һ�£���Ѫճ�����ϡ��Ҵ�Ѹ�����������Ͻ��Ь�����鿴���ס��üһ�߰�ֻ�������渽����Ƥ���ϣ��һ�æ���������棬��ϸѰ�����ܣ������ĺ������������У��ҵ��а�����Ӱ����Ҳ�����⡣��
�����ҵ��������ҵؿ�������֪����Щ����һ��������̸��ɫ��ĺ�����ô���ѵ����Ѿ��������������
�����ڽ�ī��ǰ��������̸�����ij��������Ρ�ѩɽ��ڡ�ԭʼɭ�ֵĺ��ܺͺ��ӣ�������ʳ��Ѫ�ĺ�����Щ�������ǵأ��κ������߽������֣������ܵ���ʳ�����������˵ļ�������ʱ����ͷ�����Ĵ������ſ�����������ס�������˵�ѪҺ����ôһ��һ�εر��������������ڣ�����������֮һ���������˵�Ƥ�������У��Ͳ��ײ������Ϊ�����Ѫ���������̲���ôʹ����
�����������������ҧ�����岿λһ�㶼����ݴԽӴ����еĽ��ײ�λ����������ʯ�����ߵ��о���ı����ó����IJ������ſ�ڰ��������ҵ��������ȴ�������ɢ���ر��DZ�Ϫ�����ݺ������ã��߽�ԭʼɭ��ʱ�����ӵ�����������ʱ������鷳���ˣ�ֻҪ�ҵĽ�һ̤���ݴ��У�˫�����Ͼ��������䶯������
�����н�80��·ң�����ɽ������������������ʱ��������Ĵ��ָ�ɽ�����ʳ����ѪҺ��ɽ���̫��̫�࣬�ʵ���Ϊ���ɽ����
���������ɽʱ����ͣ����������������Ϣ���������ʱ�������Ѿ������������Ը���Ӧ�õ�ȼһֻ����ȥ��������β����Ȼ�������Ĵ��Ȳ����������������ͻ�����ͷ�����������������ǣ����������ȣ���ȥ���ӣ������Լ���˫��������ʮֻ���Ȳ�������Ѫʱ�������Ѿ�����֣���ȼ���̡��Ĵ���ֱ����˫��ץ����
�������ܲ�ͣ�ؼ���š�ץ�ţ����Ǻ��Ľ������Ա����������ҧ����Ѫֱ������ɫ�����ӱ�������ֹ����Ѫ���죬�ҵ���Ҳ�ܵ���ҧ���е���������������������Ϻ�����ͷ����������ݽ����������������һ�����ڵ㡣�˿̣�ټ������ɽֻ����һ���ˣ�����Ѹ�����룬�ұ��ް취��������
����7�����������¡�����
�����߽��˺��ܣ���ɽ�����м�������ľ����Ƥ�����ɵ�С��������������Ъ�ŵĵط������ڵ�ͼ��ռ��һ����Ŀ��λ�ã��������������š���
�������˺��ܣ������������յ���ʮ�ŵ��ռ����ɾ��ڵĻ����¡�����һ�δ�ɽ��ֱ��ȵĶ��������ߵ��˱������ֳ����±ڣ����ͱڷ���Ļ���С�����������������ʯһ�����»����������棬����еļ�������һ���������������⡣��
������ʮ�ŵ�����ˤ��ȥ���ˣ�һ���DZ������˴���ˤ����ȥ����һ����;���˴����Ű����ˣ�����Ⱥ�ʬ����ȫ����ī��;��ÿ�궼Ҫ���ˣ���ʮ�ŵ���ˤ������Ҳ����������̸���е�ƽ���¶��ѡ���
�����ұ��ų��ص��а���������Ӱ�䣬һֻ�ַ������棬����ǧ�ߵ�ɽ�������»���ÿ����һ�����ľ��ᵽ��ɤ���ۣ����µ�������Ԩ���˵�������һ�δλ������·�䡣��
�������ڻ����ʮ�ŵ��գ����������������ߡ����쳣�����г�������������ģ�ͷ�Ρ���Ϣ��ƣ�����þ�����������������Խ��Խ���ԡ����������������������߹���λ����˼�֮·���ҵ�������ܵõ���Ч�IJ��䡣��
������֪�����߳������º�ͻῴ���˼���ǰ��һ���а����ŵĵط����˾�ס����˵����һ���Ű������ڴ˴����ľ����Ѩ��Ϊ·���˴��ı������ṩЪ��ʳ��֮�㡣һ�뵽���˾�ס�ĵط��������ӿ��һ�ɳ嶯������ϣ��������굽ī�ѵ�350��·��������
����8��ֻ�������˵İ����ţ�ͼ��������
������������һ���˹��������ţ�Ҳ�Ǵ�����ȥī��·���еĵ�һ���ţ�����λ�÷dz���Ҫ����ɽ��ɽ֮�����Ҫͨ����������ɽ���ཻ�ĵײ���һ��������ӿ�ĺ���������ӿ��Ͽ������������������˷�����һ�ܼ���ҡ�ڵĸ������ź������ɽ֮�䡣��
�������治�����ţ��ڵ�ͼ������������λ�õİ�����ԭ�����֮С��С�ý�����������ʹ�˰����ܷ��С�С�ý��������˾�ס������ǽ����Ͽ�Ⱥ��һ���������Ű����˾�ס�İ����ţ���
����ƣ����˫��������ʯ���п������˿��DZ�Ť�˵Ľ���ʼ��ʹ�������Ҵ��Ŵ�����ҧ�����س�ľ����ȥ����
������ͷ��һ���ƽ̹���µء����������������������ľ����������Ű������ڴ˾�ס����Ůһ�У�����Լ��ʮ���꣬��������ɹ�·���Ů�˽��ж�ʮ���ꡣ��
�����������˾þõؿ����ң�������ã����������˵����һ�仰�������Dz���������ǰ����ʵ��һ���米����ƣ�������ĺ���ֻ���ߵ��˰����ţ���
�����ҵ�ȫ�����������������а�������Ӱ�䣬���а��ڵ���Ʒһһ̯���������¡�������ľ��ǰ�Ĵ�ʯ�ϣ������ۣ�������������䡣�г��ѹ����죬ȥī�ѵ�·��Ҳ����һ�룬��ʱ�˿̣����ڰ����ŵĴ�ʯ��ɹ̫����������������Ϊ�����һ���չ�ԡ����
������������Χס��ָָ��㣬�����ҵ��·�������ؿ������ڵ���Ӱ���ġ�������ɫ�Ľ����С��������Բ�ͨ����ֻ�������ƱȻ�����˵�Ҵ�ʲô�ط�������Ҫ��ʲô�ط�ȥ���Ǹ����˾���ؿ����ұȻ������ƣ���������һ��ָͷ������ǰָ��ָ���ֳ�Զ��ָ��ָ��Ȼ��ָ���ҵ����š��ҵ��˵�ͷ����֪�������������Ƿ�һ�������˵ء������ֽ�̸������������Ů�IJ�ͣ�ذ�����ѽѽ�ؼ���š���
�����������Ű��������Ѻõģ����Һ������������������DZ����ҧ�ð߰ߵ������ȣ�һ������ҡͷ����ѽ����ѽ����ѽ���ؼ�С����ӻ���ȥ��һ�Ź���������һ������ͣ��������һ�Ѵ��ߵ�����ǰ����������������ǰ���˻Σ���ָ�Ű������µļ�������������Ҫȥ�ӱߵ��㡣��
�������ӴҴҵ����ˡ������Ű���Ů�ӱȻ������ƽ��ҽ�ľ����Ϣ����
����ľ���ڵ�ʯ������ȼ���Ŵ������Ϸ�������һ�ںں����Ĵ��������ð��������ˮ���·����š��������ҵ�һ������ˮϴ�ţ���ľ�ĽŽ����ָ���֪�������ó����ֻ��Ƶĵ�ͼ�����滭��ȥī�ѵ������š�̯����ͼ����ָ�ű����������˵����������������ͬʱ��ͷҲ˵���������������롰�������������Ҳ���Ǵ��Ű�����������ġ���
�������˿���ˮ�����ڹ���ľ���ϣ��ҵ����D���쳣�������Ҿ�Ҫ�ߵ��������߽���˵�еĴ��䣬����Ŀ���Ű����������������ϰ�ס���һ�ж�����ģ������Ҿ�Ҫ�������磡�Ҽ����ô�ľ����վ�����������ڻ����Ե��Ű���Ů��Ц�����������ң�ľ���⣬��һ��Ů����������˫մ��Ѫ���Ľ�Ь�����ӳ��ӱ���ȥ����
����̫������ɽ����Ͽ�ڳ�Զ����ȥ����ϼ��Ͽ��������Ⱦ��ͨ�죬��ɭ�ָ��ǵ���ɫɽ�����˽��ɫ��Ͽ������������ˮ������Ʈ�ݣ���ɽ�е�����������ɽ�Ȱ������γ�һ����ɫƮ�����ҳ��Ž��߳�ľ���̯�ڴ�ʯ�ϵ������װ����Ӱ����һһ��ʰ�ã���Щ������������Ⱥ����Ķ������������߽�ī�ѡ���
����ľ�������Ű���Ů�����������֡����߽�ľ������ڻ���ԡ����ڵĻ��ƺܴ��������س�����������̣��ֳ����ڵ���һ��ľư���ף��������ϸó��������ˡ���һ���Ű����Ů�ӴӺӱ�����������ϴ�ɾ���Ь����ڻ����Կ��ţ���һ��������˵лл������ȫ��Ц�ˣ�Ц�ú�����¯��ӳ���ں������ϡ���
������ʵ���Ű����Ů���Ǻ����ģ���ʪ��������������������滷����ʹ�����Ե��������������������š�������Ը��෴���������Ǻ�Ц�ؿ���һ�У�������˵һ�仰������������һ������ʱ�����Ǻ�Ц�������㣬������Զ�����������顣��
���������ڹ������˻������²�ͣ�ط�����ľ����Ʈ����һ����������һ�ɾ�Υ�˵���ζ����
�������ǰ�Ǹ���������˻����ˣ����˶�����㣬ȫ�������㡣���������õ�����ϴ����һ����ȫ�����������Ĺ����
������ȵ�ҹ�����٣�����г�����һ����Բ������������ľ����Ʈ�ݳ�һ���������ζ���Ű���Ů�����ó��������ι����С�ϣ��п���Ҳ�������ڡ����Ƕ�������Χ���ڹ��ߡ���
�����������Բ�ͨ������֮��û˵һ�仰�����ǵݸ���һ�����룬��Ϊ������һ���������ס�ÿΪ����һ���£����ǵ����϶�������˷ܶ�������ɫ����
������Ȼû�����Խ��������ж�����������֮��ľ���к�İ���С������ȼ�յ�������ʱ�����˺��˷ܣ��ܼ���������ס�ҵ��ֳ��������ҹ���ĸ������Ż��������������������ú�Ͷ�롢�ܶ��飬����߿գ����������Ź�â���߿��ĸ���һ����һ���������ڻص��������Ű���Ů��Ҳ�����ڸ����С���
�����Ҿ����ˣ��������������Ĵ��࣬�����ƣ������ĵĸ���һ��������ɸɾ����ĸ���Ʈȥ��
�������������Ϊ����λİ���˵ĵ������������������ÿ����Ҫ����������������������Ҳ��ö�֪���������ĸ���ʹ�ұ������У�����Ҳʮ����ο�����㡣���룬���ǵ���������������������ԡ����衢���䣬�ػ��ţ�����Ŀռ���ʼ��������Ȼ�Ĵ������ڣ�����ˡ���
����ҹ����Ͽ���Ͽյ����º�����������ľ�������������Ʈ�ݵIJ��ң���Ӧ��ƣ�����������������ѷ�����������
������ʱ���Ǽ���߸��һ�ж�Ů���ѻص����������Լ���ľ���ڣ����ǵ���������������Ȼ���ξ����
��������������һ��ľ���ڣ���ǰ�IJ���յ������������ҵñ���ľ�ܣ�������Ʈ���ļܻ���һ���ˡ��ž���Ͽ��ɽҰ����Ϫ�ӵ�������������ڻ����ը�����⣬���������������
�����ҵ�˼���������ֻ����н����ξ���������һ��ľ����ڵ��͵���������Ϩ�𡣡�
��������˯�е�һ����Ů��ʲô��ϵ��������һ���������������Ұ��Ͽ��������˶����ꣿ��
������ʵ�����е�������������Ĵ�Ͽ�Ȼ������Ѿ��Եò���Ҫ�ˣ���ʵ�У����������������ڣ���Զ���˼���Ƨ���ݵ���������˭Ҳ�벻��˭����
�����ڶ��죬��������������о������ر�á����������˻���˯��ľ���ϡ����߳�ľ�����غ�������������¿������峿�İ����Ź�����Ӱ��������ɽ��������С���˵���Ź�ȥ��������ǣ������������һ��ľ�壬������ɽ��ı������ľ���ϻλε��������ߣ����Ѹ�Ϊ�����š���
��������������ϰ����ţ�����һ�¹����ŵ���ζ�����¼������������ź���������Ŀѣ���߹���ȥ����һ�ɴ�����ɭ�֡���
����������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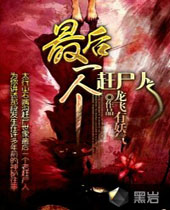
![[�촩]����һ���Ƿ���](http://www.nstxt.com/cover/0/72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