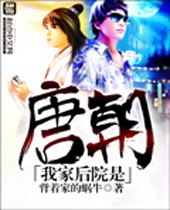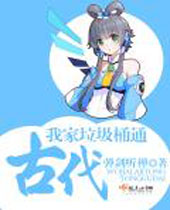�����Ҽ���Ӱ��-��6����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
�����������������꣬ѧҵ��æ֮�࣬��DZ�������ʽ�������Ļ�����������ݡ���Ժ����������꣬��Ũ�����Ȥ������Ԫ�������硣�ڲݴ��������÷ѣ����š��ҹ�����;��ȥ�����������������ٳ��С���ϲ������ŦԼ����������ǧ�Ĵ��з����Ϊ����Сʱ��ס���Ϻ��������ɳ��ı������Ļ���������������֮������ϧ�������Ѿ���Զ�Ȳ�������Ů����������Щ�������ĵ������ˡ���������
����������Ϊ�����ʢ���ġ������ٴ�ѧ��֮һ����������ȫ�¹�����ܼ���ѧϰ��ʽʹ��é���ٿ�����ʱ������˰�������������顶�ҵĸ���ë�����Ҷ���ë������Ů�Զ������ѧϰ������29��������������ǡ��ϡ���ѧ���������������������С��ѧ�����ǵ�ʱ�����ż���ͬ������أ�����������
����������֪�������ж����˶������û�к�ͬѧ����һ���÷��ڹ���ѧ����ϧ���ֶ����������ٳ�����л�����������������⡣������Ϊ�������ţ�������й�����Ķ�Ϥ��������ѧ����ʱ�������Ļ���ѧϰ����������й������ͽ��������ô��Ҫ��Ӱ�죡��������
����������Ȼ����ʷ�����š���������������Լ���ѡ��Ҳ�������ͨD�DΪ�˽��й�����ʱ�����������������Ѷ�Ů�ͳ���ȥ���������Ƿ�Ҳ�в����Լ�ȱ������˼��������ѧϰ�����Ŭ������һ��δꡡ����š��˾˺��������ѧ�ص㣬��ʱ������ֻ���������������ˣ������ͣ��������������Ʈ���������פӢ��ʹ�ݵ����������������֮�������ֺ����������ѳ���ѧ��ÿ��ʱ�����˶����Լ��Ļ��ᣬ��������ڰ��ջ���Ĵ�ʦ���������þ���������˵����Ϊ��ĺ��ˣ�����Ҳ����ס�ˡ���������
��������������ѧϰ���������Ρ������Ҷ��Լ�������D�D�й������������ʵĸо�������ʶ®ɽ����Ŀ��ֻԵ���ڴ�ɽ�С����й����㵽����ʲô��������ʲô��Ϊʲô������������ѧϰ�γ�ʱ�������ĵ����⡣�����и���������ͼ˵���й�������ʼ����Ϊ��Ҫ�˽��й��Ľ��죬�����˽���DZ����й������ߡ���������
������������˵�ë���й������������˵�ӡ�ǣ�����˵���й��Ĺ�ȥ�����ںͽ������Ѿ��������������һ�������ߵ�����������߲��ɷָΪ̽��ǿ��֮·�����ǵĸ����������ױȵġ��ǵ�һ�������������˵��û���Ļ��������û��������ǰ;���Ҳ����Լ�����������û�����������������һ����̽�����ĵ�·�Ǻ��˲������еģ�������·����·����Ϊ����Ӧ�ߵ���·ָ���˷��ο���������·�ϻ���������ô�౯����ϵĹ��¡���ʷ����գ���Զ��������Ӧ�õ�λ�á���������
���������ع�֮������Ȼ�����Լ���ѧҵ��������ڱ�����ѧ������ʿ��ǡ�ɣ�����һ����ë����Ե��ѧУ�D�D���������ý�������ѧ���ë����ͼ��ݹ�ְ��������ګ����ʷϵ��ҵ����������Ӱ�����������������˱�����ѧ����ʹ����Ũ���ѧϰ���������ɺ�����ǰ��˼������ӡ���������
�����������������֣����մ������Ҵ��Ļ��Ƕ��о�����ë���Լ��й�����ɫ�Ļ�����������ľ������ǵ���������ͣ����������������������ѧ�ᡢ�Ļ�����ȵȡ�����Ŀǰ���г����û����У��Ҵ���һ�����������о������������洫ýΪҵ�������ǶԼҷ�ܺõļ̳к�����������Ϊ��ѡһ��������ĺ����֣���һ�����˺���Ϥ�����ƾͷdz���Ȼ�����У��Ǿ��ǡ��������ݡ�����������
���������������ݣ����λ�����Ϻ���������������������������������衢���������ʮ����ĵط��������ع���ҵ���ң������ĸ��������Լ�ע��Ĺ�˾�����С���������ƾ���ʷ�Ļ����۵�һ�����ӣ����������Ҳ����ġ����ҳ��˺����ж�������Ȥ����һ�����������о���֮�⣬��û��Ҳ����Ҫ�����κ���Ȩ���Ҿ��ã����������ڵ������������ȫ��������D�D�κ�Ȩ������Ϊ������������ڵı�Ҫ��
�ڶ��¡����༰��������ګһ����뽭��
�������������ǣ���������״��Ϻ����Ӱ��ģ���ʱ�����ź������ѳ������գ��������û�м����������������������ë����ʶ�����������꣬������³Ѹ����ѧԺ��Ϸ���ʦ�������������˽�顣��������
��������ë���������ڣ������黹�Dz����ġ��������������ί�������飬��Ҫ�������չ˾�ί��ϯë�������������
�������������������ګ�������������ǰ����ʮ�������Ҷ�����ս���������ֻ�м����ݵ�ʱ�����ܹ��ѵõ�����֮�֣��������ź����估����˾ˣ�����ʵ֤�����ҵ���Ǹ��ܰ����ӵĸ��ף�����ij���������ȶ������������Ӱ���Ǿ�ġ���Ů�Ŀ�οʹ�������Ϣ���Ӷ����о�������Ϊ�й����š��������Ĵ��¡���������
�����������ս�����ڣ��������תս�±����ݾ����������ʷ�����˻��䣺����Ϊ�����о��ڼ䣬���ı��ֲ�ǿ���⣬������һ�����Ӻ�ĸ��Ӧ�����Ρ���ʱ���ʿ�����żǵã���������ګĸŮ���ݾ��硶����ɱ�ҡ����ô����ȴ���о����ۡ���������dz���һ�����������ǧ�ﲻ���������������о������������Ӳ�ͬ�գ���������ͬ�������յ��ǣ���Ϸ����������
���������Ψһ�ἰ��������ʫ������������
������������•��ϲ�Žݱ���������
��������һ�����������ﲽ�˺��ϣ�������Ұս���ո������������������
�����������Ⱥ��ϣ���Ұ�������������
�����������������������°�����������������
�����������������������δͨ������������
������������Ƶ������������߳ǡ���������
����������������ʱ���������°������Ȳ���������һֱ���á��������ټ����������Ƽ��������ڣ���������������״̬�����������꣬�����мҺ�����������������Ƭ��Ϊ��������ʫ�����ɹ������˵ڶ��꣬�������������������������������ʦΪ��������Ӱ���Ӵˣ���Ӱ֧����Ϊë��һ����������Ϊ�˲��ò�ѹ��Ϊ�Լ��������µķ��á���Щ������ڽ��깫�������ͥ��Ŀ�ж�һһ��������������
�����������⣬�����֪����Ӱ��Ʒ������Ϊ�����β��롱�������գ���ģ�ض���������ġ��Ӱ��ˡ��ֱ롣���ձ���Ĺ��£����ǡ��ĸһ���հ������˵��̫����������ʹ���˿��Ƕ���ʷʱ���Ծ����硰���������С�����ô��һ�����Dz��ᡰ���������ĨD�D������Ȼϲ����Ӱ����ӰҲ�����ɾͣ��������������ڴˡ���������
���������ݽ������뽭��Ͻӽ������ս���ʿ¶���������Ϻ�̲��Ӱ���ǵ������º�Ը������Ҫ����һ�ٲ���Ƭ��Ȼ��������֪��ʮ�������þ���˼Ϊ���������ݳ����ģ������˲�������Ϸ�����ѡ���������Ա����Ա��Ҫ��̨���ɱ�������������̨�ĽŲ�ȴ������������̨�����ϴ���̨������������Ϸ����һ�����ǡ�ʮ��ɸ�����ϡ��D�D�⣬���������еġ��ĸ�뽭��Ĺ�ϵ����������
�����������������꣹�£��գ���������ǡ������£��գ������˰����������顱�������£�����ͼ����ΰ�������͵�ʦë����ϯ�������ࡱ����ȫ������������������Ĭ�����쵼�������У���������˱���֮�Կհס���������
����������ʵ�����ָ߶����λ��Ĵ����������ǡ��ĸ���������������Ҳ����ʹ�õģ��������֮ǰ���������ǶԴ�Ӧ��İ������������֮����������֮����������ľ���Ӧ����������ѵ������Ȼ�����������ĵ�һ���ˣ�Ҳ�������һ�����Ƕ���ʷ�������˵ģ����������ġ�����Ѱζ�ķ�˼��
�ڶ��¡����༰��������ګһ���ҵ�������ګ
���������ҵ�������ګ����ͽ����Ů�������������������Ӱ�����ʱ���47�꣬������Լ�ʮ����Ů����С�ĺ����ر�ϲ�����������İ�Ů���͵�����Ժ��������˼���Ωһ����ȹ�ȫ��ͯ��ĺ��ӡ���Ů����dz��ǣ��������ޡ��͡�С�ְ֡�����������
�����������������꣬�������˾�д�ţ��ص�ΪСŮ���˼���˵���������ʺ��㣬��������롣���ļ�ֽ���ĸ������š��������Ӱ�ʱ�������Ǵ�����Ůһ���о�����ʱ���Ի�������С�����衣��������������ʵ���Ͼ�������Ů������һ֧����ɻƺӵ���ɽ�������������꣬��ڸ���Ӣ�˾˵����л��ر����˵���������ګд��û�У��������ǵľ����Ѻܽ���ʱ�������������Ļ����������Ȱ�֮��ԾȻֽ�ϡ���������
�������������Ů���������ǰ�֮���֮�ϡ������С���Ҫ��ȥ��ʳ�óԷ�����ѧ����Dz���˿�������⡣��Щ����̫��̫���������ʱ����ʿ������������һ�����ɣ��ܵ��������������һ��������ĩ�ؼ���������ʱ������ѧ���ڵĺ�������ƫƧ���������Ѿ�û���ˡ�����������ʿ�ɳ������Լ�һ�£����֪���Ƣ������������
���������д��������������ô����ѽ������˵���������ֳ����ġ�����ʣ�Ŷ���������ֵ�ʦ������������Щʲôѽ�������û˵ʲô���������ģ������ҵġ��ҡ��ҡͷ˵��Ҫ����ѽ��һ����ʦ���ú����ġ���������������˸���һ�����ģ���������Ů�������⻯������֤����ΰ��ΰ���Լ�Ҳһֱ�������˵��������������
�����������������ѷdz���������������Դ���Ů�����ڵļҳ�ֻҪ�������������������ǰѺ��Ӱ�����������ǧ����������Ů�ϴ�ѧ�����������������Ϊ�����̴��ĸ�ĸ�ǣ���������Ϊ��������쵼�˵�����Ҫ���Լ��¶������Ů���D�D����dzɾ�ΰҵ��ë��һ����ȷʵ�����Դﵽ���ĸ߶ȵġ����ڣ��Ұ���Щ����д������Ҳ���ܶ�����������ʾ���ǵ������������Ϊ������д���Ը������ϧδ����Ը����Ϊ���������ˣ�����Ҳ����������Ը�ɡ���������
�����������Ů���İ�����������������Ů���ľ���Ʒ�½����ϡ�������С�����ಡ������������ڲ���Ҫ�м�ǿ����־�����������������ä���ף��������д��������־���Կ˷����飬һ��Ҫ������־���D�D��Ҳ�����ľ���̸֮����������
�����������������꣬������������У�ʹ���������ڵ�ȱ�㣬�㱨˼���ջ�˵�Լ����ˡ�ׯ��•����ˮ���ĸ����ǣ��Ը��Դ��Dz���ȡ�ġ��ΪŮ���Ľ������ˡ������ŵ�������������ţ�ϲο������ʹ�����ˣ��Ǽ����£��Ӵ������ϣ���ˡ�ʹ�ࡢ���ˣ���ʾ���������£������Ρ��ĸɾ���һ������ת����β�͡�����Ϊ�ǡ���Ƨ���������˵ķ���ȥ��������������
��������������ź���ٻ�һ�ţ��������ˡ�������ɫ����������׳־��������������������ʹ�ࡢ���ģ����Ǻõġ���Ӵ�վ�������ˣ���ˣ��Ҽ�Ϊ���㣬Ϊ��ף�ء���dz����������Ⱥ�����ʣ�����ͬѧ��̸�����ģ�ѧ��֮��������֮�̣����п�Ϊ���������������Ҳ������ȭȭ֮�ġ���������
���������ҵ����������������������������ס��һ�𣬽��ù�ϵһֱ��Ǣ������������ر��ǰ�����Ϻ��������ͱȽ����ˡ������Ƕ�����ʮ�꣬����ǵ��������������ί�У�����ǽ֮�⿴���Լ�����������
�����������������Ǹ���Ů���Ĺ��У��������öԽ���ף����Ҳ��ֻ������������ˣ���������ʱ������ɣ���������
�������������������Ǹ��Զȹ��˶��µ�����ʱ�ڡ���������꣬�������������������ó��л�����棬Ҳ���dz�ϯ����������������ź������һ������ӣ���˵����Ļ��⡣��������
�����������裱��������ӱ�����ʷϵ��ҵ���Ρ������ĸ��һ���鳤����ĸ����ѡΪ���֣�һ�ȳ�Ϊ�պ����������Ȼ������ѧ��˼����ƽ�͵������벨���ƹ�ٿ�Ī��������Ե�������Э������������Ҳ��������ƵĻ��ظɲ�һ�𣬱��·ŵ�����•���ߡ���У�Ͷ�����������
�������������֮�������й�һ���쳣�¶������ѵ�ʱ�⡣���ڽ����ھ���Զ���سǼ������̣�������Ҫ���������ʱ�䣬�˹�������ȥ����̽�ࡣ���ǣ����Dz�û���������������ʿ�������ŷĴ��������£����裱��������������ڵ��̷�D�D�������飬����ס�ڱ����������ּ��Ӷ��ִٵķ���������ϰ���ƽ�������ɵ�����D�D���⣬���������ô�����ġ���������
��������������һ���ӣ�������Ч֥���ҵ�Ч֥���ܼ̳���ë�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