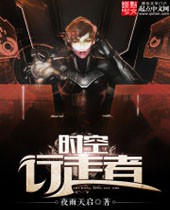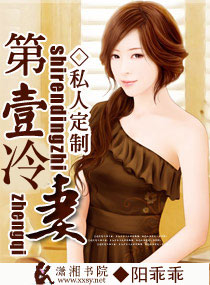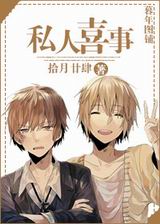私人行走-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老太太一边给我称樱桃,一边唠叨“樱桃好吃树难栽”,买了一斤边走边吃,实在是良多趣味,其实樱桃并不怎么好吃,微酸,甜味也淡淡的,喜欢吃的人多爱那种感觉吧。
10时,到达县政府,看黄永玉返乡作品展。正门进去,题有画家的诗句“我的心,只有我的心,亲爱的故乡,它是属于你的”。这是画家诗集上的句子。画家的经历也是一部传奇。只是现在年纪越老,越喜欢天真烂漫做秀也。展出的作品不多,只数十幅,木刻一幅也没有。画家晚年喜欢做大幅画,用笔也随心所欲。如《哀郢》《西洲曲》《黄英》等,自己喜欢的还是他70…80年代的写实作品,山城风物、碧水荷花、小溪雪晴无不撩人乡思。许多画家喜欢衰年变法,但能超越前期的极为寥寥,最成功的也就黄宾虹耳。而造作、恣睢、不守陈法的比比皆是。黄近期的作品多有此病,还喜在画幅上大段题字,古人云“大匠不言”,信然!
一上午大雨滂沱,沿文星街前行,过一三岔路口即到了沈从文故居。故居为一小四合院,前面3间,后有主屋3间。主屋正中有沈先生汉白玉塑像。两墙上挂有沈的章草,实在妩媚可爱。沈的姨妹张充和的字挂在正面,这女书家确实不凡,字真风神逼人。小小天井左侧为书房,陈列不同年代的文本,右侧是陈列室,有手稿,照片。正屋左侧是卧室,1902年12月28日,一代文豪就诞生在后面的雕花大床的蓝布床单上,正屋右侧陈列沈在北京的一些东西。
从14岁离开家乡,去寻找一本“大书”,作家中途只来家四次。1931年因母病返乡,在沅江上颠簸了2个月,留下了可爱的湘行通信。现在读来依然让人感动。1956年再次返乡,那时只好栖身于客栈了。80年代最后一次“犹及回乡听楚声”虽然是实至名归,已经有点凄凉的味道了。最后一次返乡,家乡人简直想不到该怎么招待这位可爱的老人,特地给他捉了一只色彩斑斓的锦鸡,沈先生爱极了,但没想到到了晚上,锦鸡成了桌子上的一道菜!50年来家国,作家一直深深爱着自己童年生长的这片土地,这个可爱的边城。所有的作品无不和这土地有关。
离开故居已经是12时,在一街边小饭店买锅贴10枚,味极可口。有一撑船的渔夫过来问是否想住江边,于是便随他去看旅社。在一家庭客栈,找一房间,3楼,为主人卧室,里面衣柜梳妆台俨然。老板娘知我远道而来,答应为我整理。价30元。到枫林宾馆退完房间来这里。房间临江,风景绝佳。
放下行李,依然去街上。沿民间工艺街走,满街买苗族或土家族的印染和编织物。有很多图案和造型都是精美之极。可是当地人并不看重这些东西,50年代沈先生回故乡时看到满街充满“丑不可言的上海轻工业品”就发出本地人把“沉香木当柴烧”的感叹。而现在,帕来品更多了,满街的“流行”,小巷深处里都是网吧,早先的古风只能从年代久远的老房子外观去感受了。踩着青石板路,在小街上漫步,想象少年的沈从文也曾在这里走过,那种感觉是奇妙的。
江边的家庭客栈(摄影/温柔)
可能是地处偏僻,没遭过多少战乱,凤凰的古民居保存的还是蛮好的。在老街上还可看到城隍庙天王庙的匾额。北城门和东城门依然完好雄峙,屋檐凌空欲飞。从东城门门洞下走过沿江边是一道城墙,站城墙上四望,烟树朦胧。小城四围被青山包围,清澈的沱江像一条银色的腰带,从县城的北门再迂回到东门,绕小城而过。在城墙上漫步偶尔能看到身着盛装的苗族少女走过,满头的银饰让人眼睛一亮。苗族的服饰图案真美,基本上是黑或海蓝土布做的。斜襟长摆,裹头束腰,衣袖的裤腿多短而宽,穿来非常有风致。在襟际,袖沿和裤腿上往往绣有非常精美的花纹图案,大方,朴素,美丽而俏皮。在北门城楼下看到2个带着小孩的苗族少妇,淡青绣花的帕子,内置银饰,端庄娴静,非常美丽。不由得想起沈先生小说里喜欢把漂亮的女人形容为观音。她们的举止实在够得上正大仙容的比喻。问可否给她们照相,两个女人都羞涩地低着头不吭声。
老房子总不免让人驻足,去感受那份沧桑。熊希龄的故居依然完好,看他的故居,倒老是在想苦苦折磨老夫子吴宓的毛彦文,真是莫名其妙。凤凰的文风很盛,尽管没有出过多少显赫的人物,门前的对联多有可看之处。在一大宅看到这样一幅“霞君离我三年整,老叟思缕万里长”横披是“梁孟情深”。这样的东西,要是让沈先生看到了,大可编一篇小说了。3时涉江过对岸去看田家祠堂,祠堂已破败不堪。祠堂前坐几位妇女,看我背着相机,就邀请坐下来闲谈,买门票的女孩到过广东,算是见过世面的。晚上在祠堂的戏台有演戏,坐中就有几位演员。她们盛情邀请我来看。便答应晚饭后来看并照相。
回到主人家已是5时,一家人围着地炉在烤火,我则穿着衬衫。他们简直娇惯坏了,一点小雨便燃木炭烤火。主人热情相邀,只好围炉而坐,烘干湿鞋。告诉主人明天拟走,还没有去看沈从文墓。主人马上差遣儿子划船带我去,老板娘妹妹妹婿也一起同行,四人走下码头,解开一叶小舟在水里滑行。
水清见底,水色如蓝,可看见青青的水草在水下摇曳,那情景真是动人。水,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处处可以感受到。在《自传》中,他说“我情感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学会思索,认识美,理解人生,水对于我有极大的关系。”他的学生汪曾祺的作品,也能让人感受弥漫的水汽,师生一脉相承。
墓在沱江岸上,沿青石板路上行,在半山处就看到一块不规则的巨石。巨石的正面刻着沈先生的两句话,背面就是张充和夫妇悼念沈先生的著名挽联“亦慈亦从,星斗其文;不折不让,赤子其人”。站在墓旁,身后山泉潺潺,对面青山如黛,沱江下浣女的捣衣声依稀可闻。
走在返回的青石板路上,雨已经不下了。《自传》里和后期的沈从文经历不断在脑子里盘旋。14岁前是爱打架逃学的野孩子,20岁前当兵吃粮,在沅水上游的湘西一带做军队文书和收税员。20岁时夹着包裹,凭自己的一只笔来北平打天下。到了30岁便已经出名并成了大学教授。晚年命运多难,最终以文物专家名世。这本身实在是人生的传奇!作为一个本质上的人文主义作家,沈从文一生都萦怀这片养育他的土地:他用爱和同情去描写乡土、亲人、士兵、农妇、妩媚爱娇的少女。充满感情去写湘西那些码头船栈,荒邑边城,缆火楼灯。他熟悉那些底层小人物,士兵、铁匠、纤夫、水手、江边吊脚楼妓女的悲欢离合,歌哭欢笑。直到现在,很多人还能含着眼泪和叹息去阅读他为一个摆渡人小孙女的爱情不幸写出的田园牧歌般的叙事诗的故事《边城》。7时半去江对岸田家祠堂看戏,观众略有100名,坐在露天,戏台是清代的。下午看到平常装束的小女孩抹上油彩,穿上戏装在灯光下明媚娇人。旁边一老头告诉我,这是元阳调,是早先的江西弋阳腔。可惜自己实在一句也听不懂,只能拍几张照片。离开时从前台俯身走过,台上的花旦正是下午坐在门前的小女骇。
天开始变晴,从老街的屋角偶尔能看到新月惊鸿一现。到主人家已是10时,楼上的房间已经换了新床单和被子,里面的陈设依然一如以前,这样的古风不能不让人感动。推门出去就是阳台,坐在阳台上,对岸的灯光,满河明灭的渔灯就在眼前。想想明天就要离开这个可爱的小城,不禁怅怅。点起一只烟,夜色中捣衣浣女的声音响在耳际,北城门角悬挂着一枚新月,闭上眼,一时间不知是今夕何夕!
…
凤凰·边城湘行七日:游走凤凰(图)
…
□菊斋主人
初到凤凰
路边俱是一色的田(摄影/温柔)
10月4日下午,有一班从广州方向来的车,路过张家界,两个小时多到达凤凰。于是背了所有的行囊登车,途中经过猛洞河边的芙蓉镇,可惜时间紧,来不及去了。火车显见得是在连绵的山里穿行,才从黑暗的隧道中睁开眼,一会儿的功夫又是一抹黑,只得看车窗上映出的对面女子的脸。
晚上7点30分到湘西自治州首府吉首,去往凤凰还须一个多小时车程,已经没有公共汽车了,包了一辆小面的往凤凰开。车在夜色里颠簸,里面的人都静静的,路边俱是一色的田,连田头树一起给路灯照得白惨惨的,有点凄凉。
到得凤凰,想不到市中心一带的酒店招待所全部住满,街上比起吉首也要热闹多了,到处是背着行囊的人,卖串串烧的生意摊子灯如白昼。来凤凰前听说这里是中国最美的小城,又听说满街是苗家风味的吊脚楼,又听说随便可以看到盛装的苗民……阿福且让我当心人群里四五十岁的蛊婆,来路上十分之悠然神往,但此时放眼四望,哪里有一点想象中的边城感觉!
失望归失望,食宿是民生大事,车子绕了半个城区,最后在城郊的新凤凰路,找到一家名字很大气门面很小样的长城宾馆住下来,老板娘说我们晚到了一日,本来今天白天是有集市的,集市上便可以见着原色的苗民,原来湘西是最大的苗民聚居区,除了每年四月初八的节日,每隔五日,逢三逢八有集市,今日正是十八,却是来不逢时。
山江寻苗寨
德夯苗寨(摄影/温柔)
第二天起床,竟然下起小雨来,4号在张家界才穿短袖,5号到凤凰已必须穿外套。我在宾馆的柜台上看凤凰地图,出城的路线要集中在今天去,一条往南长城方向,黄丝桥古城也在这条线上,另一条是往山江、天星山一带的苗寨。
楼上又下来两个少年问出城的车子,老板娘回答他们可以往汽车站去寻车,大概在150左右,这时刚好有一辆小面的停在宾馆外面,我们讲妥了“110,不超过下午5点”的价格立刻上车。司机是山江苗族人,看不出和汉人有何区别。我们去的两条线都必须经过阿拉,然后往西到黄丝桥,往北到山江。阿拉处在贵州、四川、云南、湖南四省交汇地段,是真正的边城,尤其与贵州铜仁只有八十二公里。
我们商议之后,决定先去阿拉吃早饭,然后往黄丝桥,再回头看南长城,然后折向北往山江苗民家里吃饭。阿拉的早集和一般汉族的农村没什么两样,杂散,小买小卖地交易着,我们坐在破烂的门面里吃米粉,苍蝇在头上飞,然而热气腾腾的肉丝辣子米粉真正可口,吃得人心满意足,民以食为天始终是对的。
有人说,好的果子要留在最后吃,这样始终有希望。看过黄丝桥与南长城之后,我就一直怀着这样的信念上路。说实在,南长城与黄丝桥太普通了。南长城样子与北方的长城相似,盘曲在山峰上,但是雄伟险峻则断不可同日而语。黄丝桥古城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区,保存了一段完整的城墙,城里仍有人居住,虽然下着小雨,仍有不少旅行者穿行其间,我上了城墙一路瞰去,感觉好像以前玩仙剑奇侠传时,带着林月如在扬州的城墙上捉女飞贼,斜的瓦片屋顶就在脚旁边,颇令人想一脚跨上去,可是坡度真陡!一户农家门口挂着“看三脚牛,参观一元,拍照二元”的牌子,还有一户门口挂了大堆的牛头,从城墙上看到它的后院,白森森的牛头更加不计其数,后来问了问,一个牛头大约一、二百,我想起三毛从沙漠里拾回的骆驼头骨了,装饰在房间里大概是一样的效果吧,回去的火车上果真见了有人捧着头角峥嵘的骨头从车箱里走过。作为湘西旅游景点的一部分,黄丝桥也毫无例外地在卖蜡染、扎染、绣花包,顶多的是各式各样的绣花包,因为太多,厌倦到让人不想买。不过比较起来,张家界、黄丝桥、凤凰都有卖这些东西,张家界多而平庸,黄丝桥与凤凰精致些,数量略多,价格也便宜些。
司机说山江是保存得较为完整的苗族村落,我听了十分兴奋,眼前开始浮现出苗族男女载歌载舞,关于神秘的盅术和对歌的情景也自动地从脑子里翻腾出来,于是赶紧催着他往山江赶。
凤凰是山城,这一路行来,连环十八折,两边尽是青的田地和山岭。山峰上掠过忽密忽疏的村落,司机说路右边是苗族区,左边是土家族与汉族区,分得十分清楚,而土家族更有“铜不沾铁,苗不压客”的古语,竟是老死不相往来。
在路上,三三两两地开始出现一些背着篓子的中年妇人,穿的是陈旧的苗服,上衣多作深浅不同的靛色、蓝色,裤子则是黑色,头上随便包着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