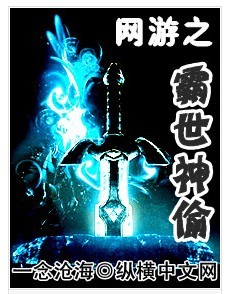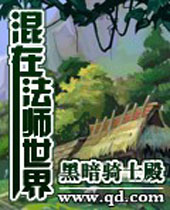饥饿的盛世-第3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雍正认为,一杀掉杨名时,有可能使杨名时成为“比干”,遂了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心愿。所以对付杨名时此等“种类”,重要的不在“治其身”,而是“治其名”“治其假誉”,不择手段地恶心他、作践他,让他“假道学,真光棍”的“丑恶面目”大暴露,让周围的人都以为他确实虚伪可鄙,也让他本人都自惭形秽,精神颓丧。承审官按照雍正的授意似乎全做到了,不仅让当堂观审的“闻而笑之者亦甚多”,(《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而且整得杨名时哑口无言,低头认罪。
乾隆之审问尹嘉铨,其灵感完全来自此案。乃父乃子,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雍正对待大臣之严酷苛刻,本已经登峰造极。乾隆又青出于蓝,后来居上。为了保证大权独揽,乾隆皇帝上任之后一再拉大君臣距离,造成皇帝高高在上,群臣匍匐于下的政治局面,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畅通无阻。乾隆朝大臣的地位,比雍正朝,又有大幅降低。
历代帝王都期待名臣、功臣、忠臣的出现。比如雍正就屡屡称他的臣子李卫、田文镜、隆科多等为“国家伟器”“朕之功臣”“不世出之忠良柱石大臣”“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
然而乾隆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乾隆认为,臣权的上升就必然意味着君权的低落。“名臣”往往出现在国家出现危机,君主大权不独揽之际。许多名臣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扶国家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但同时,名臣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君主的无能和朝纲的混乱。对张居正这位明代的名臣,史评大抵功大于过,他却大不以为然,说:“大臣强辞立威,逆行罔忌,实为弁国纪。神宗竟尔任其施为,虽童昏不应若是。”
为了消除尹嘉铨所做《名臣言行录》的影响,乾隆特下长诏斥责尹嘉铨的“名臣论”。他说,“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如果“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意思就是,在真正有作为的皇帝统治下,不应该有为患作乱的奸臣,同时,也不应该有彪炳史册的名臣,只可以有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
雍正皇帝既深刻阴鸷,又有天真淋漓的一面,冷起来一块冰,热起来一团火。严肃起来,谁也不敢喘气;高兴起来,有时又没大没小。他在李卫的奏折上批过这样的话:“好事好事!此等事览而不嘉悦者除非呆皇帝也!”给年羹尧的朱批有这样的话:“从来君臣之遇合……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他对大臣固然以苛刻闻名,但对某些投脾气的人也有热情如火、视如朋友、信任不衰的一面。比如对鄂尔泰和张廷玉。
但乾隆却极重君臣之别,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面孔,从来没有与大臣们建立起什么私交。也许晚年的和砷算是唯一的例外。
对于大臣的“好名”之习,乾隆和父亲一样向来痛恨。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训斥陕西巡抚陈宏谋:“嗣后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饰,仍蹈沽名钓誉之恶习,必不能逃朕洞鉴,恩再邀宽典也。”
在打击限制大臣“好名之习”方面,乾隆不但学习了父亲制造冤狱的办法,还有所创新。
传统社会有一个不成文的政治习惯,就是那些政绩卓著的地方官离任后,当地官民往往会通过送万民伞、立碑、建祠等形式加以表彰和纪念。然而乾隆皇帝却通令各省,将各地的去思德政碑“概行扑毁”,并严禁为官员建造生祠。在他的严令下,全国各地纷纷将康、雍以来所建祠堂、石碑摧毁,仅云南、山西两省,就近六百座。乾隆认为应该由皇帝垄断所有的伟大、光荣、正确,不给其他人留一点荣誉空间。乾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着的大写的人,而仅仅是工具和奴才。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十七日,尹嘉铨案审结。在“妄比大贤,托名讲学,谬多著述,以图欺世盗名,又复妄列名臣,颠倒是非,隐启朋党之渐”的罪名之外,乾隆还审得尹嘉铨犯有许多其他不可饶恕的“大罪”:
尹嘉铨在书中写有“为帝者师”四个字。乾隆嘲笑他学习浅陋,让大臣们评论,他“能为朕师傅否”?
尹嘉铨自号“古稀老人”,“古稀”二字典出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不巧乾隆帝也恰逢七旬大寿,自称“古稀天子”,又写了《古稀说》颁示天下,把“古稀”垄断了。年逾七十的尹氏以此自号,被认为是“僭妄”。
乾隆十分欣赏明太祖废除相权之举,认为这一划时代的创举,大大提高了君权的稳定性,实在是造福百世万代帝王,因此,他十分反感人们把清代的大学士习惯性地称为相国。尹嘉铨在自己的著作中屡称大学士为“相国”,乾隆批评说,宰相之名久已废置,本朝自皇祖、皇考以至朕,太阿在握,权柄不移。在朝大学士,作用不过是承旨记录,有哪件事曾借助大学士的襄赞?
既然尹氏犯了如此多的“大罪”,大学士、九卿等在反复审讯后,奏请将尹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照律缘坐,也就是说,16岁以上的子孙都要杀头,家中的女人们以及16岁以下的子孙要发配为奴。不过乾隆大仁大德,加恩免其凌迟,改为绞立决,亲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
同时命各省查缴销毁尹著述或编辑的著作,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一律铲削磨毁。对此,鲁迅说:“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计应‘销毁’者有书籍八十六种,石刻七种,都是著作;应‘撤毁’者有书籍六种,都是古书,而有他的序跋。《小学大全》虽不过‘疏辑’,然而是在‘销毁’之列的。”这项工作牵涉各省,一直进行了半年之久。
不论尹嘉铨是“真道学”还是“假道学”,本来都不干王法。生活在除乾隆之外的任何一个时代,他都会安享天年,寿终正寝。然而很不幸,他遇到了乾隆。
任何事情都有另一面。乾隆极力扩张君权,虽一时收到稳定之效,却造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清代后期士大夫道德与精神的迅速堕落。
儒学既有强调等级秩序的一面,也有高标社会正义的一面。社会正义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历代以来,士人都以守护社会良心为己任,能够在传统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却以虎视之态,粗暴剥夺了儒学赋予读书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护良心之责,只给他们为稻粱谋这一个生存任务。从那时候起,士人群体便被抽空了灵魂,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本来,进入清朝之后,士节士气较之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已经大为降低,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更为松弛。乾隆朝的大臣,虽然不乏能臣,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乾隆之后的中国,一蹶不振,人心沦丧,在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说与乾隆打断了官员和士人的脊骨表里相关。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如果说专政政治的经济原则是剥削与压榨,那么操作秘诀就是控制与压迫。皇帝控制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压迫着整个社会。一旦高压减轻,则社会秩序必然出现剧烈反弹。随着官僚体系的废弛,乾隆晚年社会治安迅速恶化。
一 尹壮图的奏折
文字狱的消失和它的兴起一样猝然。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全国的封疆大吏在皇帝的一再鞭打下,集体陷入了亢奋乃至疯狂状态。他们放下日常工作,昼夜不息地审查着帝国内所有的汉字,而皇帝却在这个时候不动声色地转向了。
这年年初,河南光州祝万青被人举报。举报者称他家祠堂所悬的匾额对联有严重问题。其匾额曰“豆登常新”。其对联是“吾祖吾宗,贻厥孙谋;若裔若子,增其式廓”,这类气势宏大的文字只有皇帝用起来才合适,平民百姓怎么可以妄用?
指控当然十分可笑。可是如果祝氏因此家破人亡,却绝不会令人意外。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之后,类似的荒唐冤狱数不胜数。地方官不敢怠慢,将此案列为大案火速上报,等待着皇帝对他们办事勤敏的嘉奖。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皇帝说,闭着眼睛都能看出这是一起诬告案件:“此等扁对杂凑字句,谓之文理不通则可,指为语句违碍则不可。若如此吹求字句,天下何人得自解免?此案所控情节,看来竟属险诈诬罔,断不可因此拖累无辜,致长刁风!”
既然皇帝不为已甚,地方官当然也就乐得不再伤天害理。乾隆四十八年之后(1783年),文字狱稀稀落落,显著减少。
乾隆五十年(1785年),借《慎余堂集》案,皇帝又一次向天下督抚大员郑重重申,文字狱不可扩大化:“外间著有诗文,果有如钱谦益、吕留良等,其本人及子孙俱登仕版而狂吠不法者,自应搜查严办;若并非有心违悖,不过字句微疵,朕从不肯有意吹求。”这道谕旨之后的《奈何吟》一案,竟成了乾隆朝文字狱的绝响。腥风血雨终于停息,读书人提了几十年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全国上下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清代文字狱档》)
皇帝为什么停下了杀戮之手?
因为文字狱运动已经成功地达到了目的。
如前所述,乾隆朝文字狱的目的是以超级恐怖为手段,消灭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一切有胆量、有头脑、有野心和他较量的人,都已经从肉体上消失;一切稍涉异端的书籍字纸,都已经被烧光;连绵不断的惨痛绝伦的大案,已经吓破所有活下来的人的胆。
一张一弛,宽严相济,是乾隆的一贯统治原则。严了三十年,终于可以宽一宽了。不但高压锅内臣民们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崩溃的边缘,就连他这个给高压锅加火的人,也实在太疲倦了。
更何况,文字狱运动的胜利结束,就如同一幢超级雄伟壮丽的建筑封了顶,标志着乾隆盛世构想的全面完成。物质的盛世很容易昙花一现,只有扫灭了一切精神敌人的盛世才可能永恒。而文字狱运动的成功标志着乾隆物质精神的双重胜利:物质上,他已经把传统社会的物质生产潜力发挥到了最大;精神上,他创造了消灭一切异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乾隆盛世由此超越文景、贞观、开元等其他盛世,登上了顶峰,他的子孙后代将要继承的会是一个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十岁的皇帝御制了一篇《古稀说》,对全国的形势做了如下的描述:
三代以上弗论矣,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见之近作矣。至乎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即所谓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哉,是诚古稀而已矣。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赐乎。
意思是说,中国开辟以来,夏商周三代年代古远,事不可稽,暂且不论。就拿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后来说,两千年间,活到了七十岁的皇帝不过才六人。然而这六个人中,汉武帝晚年失政,梁武帝不得善终,唐明皇仓皇幸蜀,宋高宗偏安一方,皆算不上伟大的皇帝。只有元世祖和明太祖称得上真伟人,不过他们当开国之初,有武功而乏文治,仍然不如乾隆朝之盛大。大清王朝,政权建立的合法性牢固,领土达史上最广,周围国家普遍宾服,民众安居乐业。社会虽然没有达到大同,但是已经进入小康。而且历代专治政治中的重大弊端,比如强大的地方分裂势力,敌国外患,权臣,外戚,后宫,太监,奸臣,小人,都已经消灭。国家之安,前所未有。这种富庶和平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诚可谓“古来稀”了。自己确实是古往今来最有福气的大皇帝。
七十岁的乾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从七十岁到八十岁这十年间,老皇帝仍然是那么精神矍铄,仍然是那么勤政不懈,不过他没有再兴起大的政治运动,而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