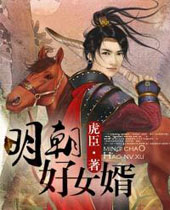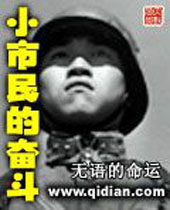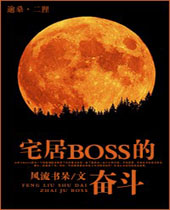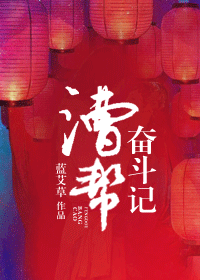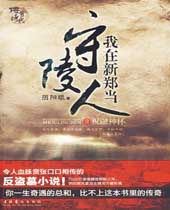奋斗在新明朝-第1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今天真是没有白来,没想到能知晓归德长公主也惦记分票中书的心思,李佑暗暗想道。与朱部郎说笑时,他好似清心寡欲、淡泊名利、洒脱无谓的样子,其实心里并非如此……
在天官府时,李佑主要精力都放在应对许尚书层出不穷的试探上面了,对担任分票中书没有深想。一方面受不了步入中枢的诱惑,另一方面缺乏直接拒绝吏部尚书的胆量,所以才应承下来。
退出来后,他深思熟虑一番彻底看透了其中奥妙,便下定决心势在必得。因为这对他的官场生涯是一次非常难得的际遇,具有非凡的意义,不容错过。不然吃饱撑着为不会写字发愁?
以李佑的出身,这年头能混到六七品已然是相当逆天了。再想进步,唯有的一丝若有若无可能性就是天赋异禀讨得皇帝欢心成为传奉官。
所谓传奉官,便是不经吏部铨选和大臣推荐,由天子发中旨直接授予的官职。
按着近几十年形成的默契,七品以下闲杂官职、以及尚宝司、光禄寺这些内廷闲散官职,也包括两殿中书舍人,天子愿意赏也就赏了。总有些技艺精湛的专业技术官员和勋戚之后需要特殊照顾,人君必须得有这些权力。
但要到了七品及以上外朝文官和地方官,那就不能中旨擅授了,至于吏部尚书和大学士这两个特殊官职,倒是有可以由天子特简的选项。
正好李大人如今到了七品这个文官集团的门槛……
吏员出身的李大人,一不是勋戚之后二没有功名在身三不是太医工匠之流。假设像无数穿越小说那样被脑残皇帝莫名其妙青睐了,一道圣旨提拔为实职六品,而李大人又欣然接受,这个世界会怎样?
他会被口水奏折淹没,会被贴大字报批判,会被写进笔记流传丑化,会被士大夫们进行种族隔离……还有,随时要提防着数不尽的秋后算账可能性。
想当年成化年间,皇帝大搞传奉官搞得有些过火了,弄出四位数的从三品到九品各种传奉官,至今仍被士大夫视为妖风邪气的时代。
话又扯远了,总而言之如今是天下太平时候,不是乱世出英雄的时代,体制的惯性和稳定性超强。李大人虽然是带有光环的穿越者,但也没有本事去彻底颠覆传统。
即使坐监升级,处境又能有什么变化?当个比方,当六品通判和七品推官有什么本质区别?
若想寻找突破点,只有在不囿于传统的地方才能找到。
分票中书,乃是七八十年来未有的新事。虽打着复崇祯朝旧制的名头,但前朝旧典都散佚不可考。
故而想因循守旧也没有可以因循的章法,又因为靠近中枢,所以这个职位不确定性极大,或者说这里面的可能性很多,可塑性很强,也许是好的也许是坏的。
上面这些特点才是李佑彻底想明白后最看重的地方,不去试试看怎么知道是好机遇还是坏机遇?焉知不是突破点?
为抑制权臣高官,国朝很有以小抑大的传统。例如七品左右的六科给事中,以及十三道监察御史,上可封驳诏令,下可监察百僚,都是位卑权重的典型,又焉知分票中书不会走上这个路子?
既然机会出现了,为什么不抓住?哪怕是被许尚书拎出来当前台木偶,那也是应该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不过这个时候,那归德千岁却令人意外的冒出来了……
要说李佑懊悔自掘坟墓,一不小心把林驸马刺激成竞争对手,这纯属搞笑肤浅之语。没有林驸马也有别人,本质上都是归德长公主在插手。就像没有李佑也有张佑王佑,本质上都是许尚书在插手的道理。
相反李大人还得感谢林驸马这个政治小白,随随便便就把这事吐露给底细不明的外人知道了。
当然,如果是其它衙门的位置,李佑就不担心了,再强势的公主也不敢和朝廷法定的铨政大员吏部尚书抢。毕竟有个不成文规矩,内廷是皇家的,外朝是文官的,合起来就是朝廷。
但以这个角度论起来,内阁和下属两房在朝廷架构中却属于不内不外、又内又外的范畴,可以称为是外朝和内廷中间的缓冲区。这是国朝体制与前代相比最奇特微妙之处,也是内阁号称宰相,其实最不像宰相的地方。
缓冲区的另一种意思就是角力场……
想至此,李佑对轿夫喝道:“换路!去天官府。”
归德千岁对驸马私语应该是很机密的事,现在不该外传时让他知道了,就是最大的劣势了。怪就怪,你选的这个不争气的驸马罢。
第四集 京城风云 第215章 偷得浮生几日闲
景和七年秋,苏州府推官李佑离任入京。放鹤先生时任礼部副郎,偶遇佑于部堂,闻其指物作大树诗而赏之。
及后坐而论诗,佑顷刻立就绝句十首,皆载诗道也,发尽古今意旨。放鹤先生叹而服之,谓己不如也,并亲书于酒家,自此不以诗词自诩。
帖幅高悬,一时名动于京师文林,前往观览揣摩者甚众。
时人云,近代诗词渐微,久无佳作可摹唐宋,幸有李虚江遮羞,不至惭于后人。怕是本朝也只有此一人敢大言“公道持论我最知”、“时文正宗才力薄”等句。
又有江南名妓玉玲珑,以艳色曲艺名噪于京师,皆视为南魁之选,他人非数十金不得见。其与李佑有旧,盖因成名得李佑之力也,得讯往会馆谒故人,然闭门不纳。
妓在院门白曰:“闻先生初至京师,起居多有不便,愿为侍婢以报旧日恩情,因何拒奴于门外耶?”
李佑使左右传语曰:“相见不如不见。”
又隔墙以诗述其心迹云:“故国乡音竟杳然,浮叶飘萍剧堪怜。斜依芳树岐王第,虚度春华贺老弦。红豆不思行乐夜,锦缠殊忆奉恩年。君何细数梁园事,旧时金粉往如烟。”
妓泪湿红妆,涕泣于门廊之下道:“奴自知卑贱,不敢误先生前程”,遂三拜而去。
闻者叹曰:“此可为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之注释。”
门的另一边,快两月不知肉味的李才子,心情复杂的扒着门缝,看着送到嘴边的美人远去,不由得纠结悱恻、唏嘘不已、感慨万分。
娇滴滴的美人什么时候也敌不过权势的。许天官发话了,这段时间低调些,不要惹出什么能被弹劾的事情……
话说吏部选官有规制,双月一次大选,进行比较正常的升迁授官,单月一次急选,处理因为去世、致仕、丁忧等意外事故引发的官位空缺。
本来许尚书打算把李佑塞进下个月,也就是十月大选中,至少不那么扎眼。不然没特殊情况下,单独为李佑一个人奏报选官,显得有些急不可待和任人唯私。更何况前几天早朝,无辜的许尚书还被人抨击了包庇李佑。
但老大人听了李佑连夜急报,便意识到夜长梦多,不可再拖延。万一归德千岁突然说动了太后,发中旨直接任命人选,那就被动了。
要知道,内阁毕竟不同于外朝衙门,不经铨选廷推以中旨任命个中书舍人也说得过去。所以这不是讲究品味脸面,而是需要赤膊上阵的时候了!
次日,吏部便拟了奏疏加盖印信后封进奏报,直接把李佑推上去抢一个先机,占住先到者先得的理。
这种时候不要脸本身就是一个态度,别人若识相便不会再打主意了。
吏部之所以与内阁、都察院并称为三要,不是没道理的。
内阁从国朝初年设置以来权势渐张,其他五部的部权到如今被内阁侵夺许多。只有吏部的铨政大权还能相对独立于内阁,吏部尚书还敢与阁老叫一叫板,况且从制度上内阁不能直接指挥吏部。
当然,遇到了个人威望极高的强势首辅,例如张居正、严嵩这号的,吏部尚书也得当孙子。毕竟国朝的事很多时候不是制度说了算,是人说了算的。
反过来,吏部尚书强势时候,内阁也无可奈何。吏部的奏疏,一般都给面子批了“可”。不然的话,吏部尚书动不了阁老本人,但变着法子折腾阁老的门生故旧,也能令人恶心到极致。
正值此敏感时期,可能还牵涉到朝廷角力,深晓内幕的李佑(为终于不再是懵懵懂懂的酱油党而泪流满面)焉敢公然行眠花宿柳之举,什么能比乌纱帽要紧?
所以李大人面对美人盛情,只能按下满腹欲火,装腔作势的、拿出几分薄情寡义的范儿吟道“红豆不思行乐夜,锦缠殊忆奉恩年”了。
婢女小竹走到李佑身后,“老爷,要不要奴家追上去对那位姐姐告知一声,叫她夜深无人时悄悄的进来?”
“咦,这个主意……”李佑下意识说了半句,从门缝回过头时猛然改口道:“老爷的事不要管那多!你看看你自己,成什么样子。天越来越凉,你却越穿越薄。也不怕冻出病来,到时还得老爷花银子。快回屋加一件外衣去!”
小竹扁着嘴回屋,李佑来到屋檐下桌椅上,继续练字。
那天张三确实带回了几根鹅毛笔,也问了鹅毛笔制法。恰好韩宗前两年被征召在京服役时,干过几天手工活,这几天搜刮了一把鹅毛正在试验。
李佑这些日子,偷得浮生几日闲,一直在抓紧时间熟悉鹅毛笔手感。
虽然这东西仍然与钢笔不一样,但好歹都属于硬笔范畴,总比毛笔容易适应。
李佑也不求成名家,能像模像样的写稍微规整的字就行了,反正正式的诏书怎么也轮不到他来挥笔书写。
不过今日李大人的访客真不少,坐下写字没多久,又见会馆轮值管事领着一个中年文士来找他。
那文士一张口,便让李才子吐血三升,“大树先生,久仰久仰!”
这便是大树一诗带来的负面作用了,不逢大匠材难用、肯住深山寿更长,人皆以为李大人以大树自喻自比,便号之为大树先生。
大树先生……李大树……听起来实在让李佑不入耳,不禁怀念李探花的叫法。但在京城,可是有真探花的,李探花便叫不出去了。
原来这文士是开了书坊的,想要印李佑至今诗词全集卖,但一时搜集不全,托了会馆管事绍介前来找李佑商谈此事。
出集子当然是好事,那中年文士也爽快,价钱公道,李佑便答应了。约定好近日将自己所有“大作”整理一遍后,付予书坊,刻一本《李虚江景和七年集》。
送走了书商,李佑转身不及回屋,又听闻身后几声欢笑,“小李大人,几日不见,别来无恙。”
李佑回头望去,居然是前上司苏州知府王老头,忍不住的满怀讶异。上前见礼问道:“老大人怎的也到了京城?”
他与王老头合作一向还算愉快,虽然最后关头由于某推官太过强势产生点小小的不自在,但也不算什么仇怨,总是没有撕破脸。何况在陌生的京城忽的见到个熟人,自然带有几分亲切感在心里。
老知府笑道:“下月轮到本府入朝,听说你住在会馆,特意来相见。”
李佑便明白了,地方官从陛辞之后,三年一朝。估计是王知府因为情况特殊,就地接了毛知府的位子,没有陛辞。所以只能按着毛知府的时间段入朝,恰好是下个月轮到,顺便补一下陛辞的过场。
但还是有奇怪处……你是四品,我是七品,你是前上司,我是前下属,然后你主动屈尊来拜见我?对王知府知之甚详的李佑揶揄道:“老大人有话但讲,有事但说。”
王知府赞道:“不愧是你,本官确实有桩……”
话才说一半,又从门外闯进两人,叫道:“苏州李大人何在?”
这十分无礼的打断了老知府,王老头愤而想指责几句,却发现对方是内监打扮……便闭了口。
有一人正是前些日子受归德长公主送五百两银子给李佑的那位,他上前一步细声细气道:“李大人,归德主千岁有请!”
长公主?王知府心头跳了几跳,眼皮也跳了几跳,小声对李佑耳语道:“你在苏州沾花惹草也就算了,竟敢在京城扯到公主,不要脑袋了?”
第四集 京城风云 第216章 垂拱而治的含义
李佑扫视两个公主府使者,又停顿片刻道:“王老大人对本官有大恩,于情于礼,本官必须要接待。尔等在此稍候,等本官与王老大人谈完。”
随后李祐将王知府请进屋内喝茶闲谈。
两个内监被晾在院中,面面相对无可奈何,只能心里不停意淫道,要是身在天启年间何至于此……何至于此……
公主随便召见外臣,这不合常理。但归德长公主本身就已经是个不太合常理的存在,大明三百年没见哪个公主在皇宫当管家的。
千岁敢公然派人来请,李佑却不敢去。这倒不是心有畏惧,主要是去了能干什么?有什么好处?
若是被劝说投靠归德千岁,他是不可能答应的;若是被劝说将分票中书位置让出来,他更做不了主。
或者说,公主千岁应该去与许尚书对话,而他李佑去见长公主实属多余,一个不好还会惹出什么嫌疑。
“你和长公主之间……难道与中书舍人有关?”到了屋里王知府追问道。
李佑奇道:“你怎的知晓此事?”
原来王知府此次入朝,还抱着另一个心思,那便是改年龄……他已经六十了,刚当上四品正堂大老爷,心里正快意,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