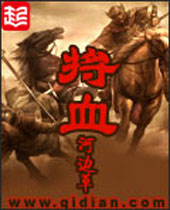将血-第116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张培贤停住话头,示弱的感觉并不美妙,尤其是对他这个大将军而言。
当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商议此事了,但并非如赵石所猜想的那般,张培贤有意拖延,而是张大将军太忙了。
而赵石来到河洛,轻车简从,不像个钦差不说,而且,也没带来朝廷圣谕,光靠赵石自己的说辞,很难让张培贤信服。
朝廷给了你多大的权力?巡访使,那又是个什么玩意?来河洛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都需要仔细琢磨,和这两位幕僚商量了两次,两位幕僚猜来猜去,也没多少新意,于是,张培贤觉着,应该先晾一晾,瞧瞧赵柱国的反应再说。
也不能让一位钦差就这么闲着,正好,张先生这里出了个主意,不如将河洛国武监分院那里的事情交给其人,也好试探一下。
而借着这个功夫,等派去到长安打探消息的人回来,瞧瞧有没有什么有用的。
如果确实了解赵石心性的人,定然知道这是个地地道道的馊主意,但张培贤和其他人一样,对于赵石的了解,多数限于传闻,接触了两次,却并不能深谙其人秉性,也就这么做了。。。。。。
实际上,这无疑将已经等的不耐烦的赵石得罪了,若是一切公事公办,反而结果会好的多。
聪明人办蠢事,没什么稀奇的地方,不用多说什么。
“是晋国公”
主意是张先生出的,自然回话的也是他,杜老头儿则抱着茶杯饮着茶,没一点说话的**。
张培贤微微点了点头,“赵柱国正在索要国武监分院名录,是去年一战之前的,而且,还要注明那些河洛生员的家世,要干什么,也就不用”
张先生皱了皱眉,立即便道:“那怎么成,以如今河洛之局面,正应抚民。如果再激起民乱,这河洛之地,我大秦还要不要了?”
这话算是说到了张培贤心里,虽然他也深恨河洛百姓不知好歹,但在他看来,乱事过后,民心思安,正是抚有河洛民心的好机会,只要渡过眼前的难关,就像当年蜀中一般,将不会再为河洛人心反复所困扰。
这也正是他不愿跟赵石再次深谈,将事情拖延下来的主要原因,因为他在赵石的话语当中,闻到了浓浓的血腥味儿。
而赵柱国在蜀中,河中,河东,乃至于西夏所做的,在他看来,除了杀人,就没别的两眼的地方了。
残暴的名头,已经被张大将军早早暗自送给了赵石。
可以说,两个大将军掌军,抚民的理念完全不同,隔阂也就在所难免,之前种种恩怨,也并非完全是两个大将军的权位之争造成的。
如果放在平日,张培贤肯定巴不得赵石激起民乱,好顺势将其赶出河洛地界。
但今时不同往日,河洛不能再乱了,而且,不管他对赵石为人多不喜欢,如今在朝堂上,能为他张培贤说话,又有那个份量的人,非晋国公赵柱国莫属。
所以说,与赵柱国虚与委蛇,才是现在最好的办法。
这些东西在他心里装着,很明白的事情,所以这番话虽然很合他心意,但张培贤还是有些不满的看了张先生一眼。
沉声道:“赵柱国到了哪儿,皆有风雨相随,所以说再多也没意思,你们还是帮我出点主意,说说该怎么应对,才能让他闹的动静小”
张先生有些讪讪的住了口,张培贤的不满,他听的出来,也明白关节之处在哪里,但有些话,真是不能明说。
为什么这么为难,根子上不在别的什么地方,而在于。
时至今日,几位大秦上将,无疑以大将军赵石赵柱国为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即便张培贤身在河洛,又经营多年,但赵石一旦来到河洛,还是让张大将军不得不暂避其锋,畏首畏尾之下,还能有什么好的应对之法?
换句浅白些的话来说,就是根本奈何不了人家,只能屈从其意罢了。
张大将军自己不明白吗?估摸着只是不愿意承认。
但这话却又不能明说,张先生心里苦笑一声,顺势沉默了下来。
大帅好颜面,对下也宽容,不过一旦有了不满,疾言厉色的时候也不少,他可不想一头撞上去,让老杜看这个笑话。
静了片刻,在张培贤显出些不耐之色的时候,杜先生才慢悠悠的开了口。
“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跟晋国公谈一谈,也未尝不是。”
(今天有客户端名家名作推荐,也不知这个推荐位好不好,不过阿草觉着,有客户端几个字,就应该不错,呵呵,月头月尾两个客户端推荐,这个月的成绩应该不算坏,就是阿草更新不太给力,怨不着别人,阿草依旧努力中。)
第十三卷龙盘虎踞春秋事第一千四百一十七章商议(二)
ps:看《将血》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张培贤沉吟半晌,杜先生话里话外的意思,他自然明白。
赵柱国来河洛,所行所为,应该有益于河洛,甚至有益于他张培贤。
赵柱国身份到底不比其他人,虽然如今手中没有兵权,但人家是正经的枢密副使,河中杜山虎,河东张峰聚,皆乃其旧部。
而且。。。。。这次朝中风云变幻,赵柱国一众人等,竟是搬倒了同门下平章事李圃,吏部尚书郑元亮等,在朝中声势大涨。
和他这样常年驻守军前的大将军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在朝中说话,一句顶旁人十句百句。
这也是赵柱国如今最令人忌惮的地方。
不过这样一个人来到河洛,只要不常留于此,没有想着掌握河洛大军兵权,那么,他做一件事,就顶旁人做十件百件。
只要他与赵柱国谈的好了,几乎可以不用顾忌朝廷那边,这对于风雨飘摇的河洛上下来说,自然是好事。
但话说回来了,权柄至此的钦差大臣,带给河洛的不可能全都是好处,以赵柱国的为人,也不会那么好心。
像他刚来的时候,便斥责了河洛布政使韩聪,几乎没留下任何的余地和情面,那么之后,处置的又是谁?对于他这个掌握河洛大军兵权的大将军的威望。又会造成怎样的损害?
这都是张培贤犹疑不决的原因所在。
盏茶过后。张培贤才揉了揉额头。身心俱疲的感觉,让他心绪越加低沉。
而对着两位心腹幕僚,除了稍稍顾及到自家颜面外,到也不用太过藏着掖着,他开口道:“与赵柱国相谋,无异于和猛虎要顾及的,其实是赵柱国一旦大开杀戒,这血腥味儿到底会粘在老夫身上”
说到这里。张培贤长叹了口气,“岁月不饶老夫自知年事已高,在这个位子上坐不多久了,老夫征战沙场数十载,这功过嘛,自己不好说,也只能留待后人罢了,但临了,老夫还就想求个善始善终。。。。。。赵柱国为人怎么样,谁不清楚。他能容老夫独善其身?”
这话说的丧气,但也极为明白。
短短的几句话。实际上是张培贤对自己的剖析,这些话旁人不能说,只能他自己来说。
两个幕僚听了,不由对视了一眼,屋中好像齐齐响起一声叹息,英雄迟暮,多少名臣猛将,到了暮年,怕都是这般模样,让人见了,难免生出伤感惋惜之意。
而像他们这样的心腹幕僚,感触犹深。
不过话说到这个份上,却不能没有人作答。
这回张先生闭紧了嘴巴,只能是杜先生来回话了。
这位老人琢磨了下措辞,才平静的道:“大帅也许多晋国公向来敢作敢当。。。。。。如今入我河洛,诸般行事,也都还算光明正大,以在下观之,有为大帅全名”
“也许。。。。。。晋国公要的,只是您点头。。。。。再者说了,之前晋国公与大帅及韩大人相谈,第一个提及的就是春耕之事,不若,借机问于晋国公。。。。。此等事,于大帅而言,千难万难,但晋国公身在朝廷,受陛下倚重,许不过举手之劳”
听了这话,张先生在对面撇了撇嘴。
张培贤也皱了皱眉,随后便有些心动,春耕,现在就是河洛的头等大事,河洛官府做的已经极多,赈济饥民,分发无主田产等等等等,甚至于张培贤已经准备,不顾军中律令,想着上书朝廷,能名正言顺的叫一部分大军开始屯田。
如果这么做了,麻烦可就也有了,屯田之事如果在西北,在河东边镇,都不会有人说什么,但在河洛这样的膏腴之地。
大军一旦开始屯田,后患极多,这里毕竟不是边镇,乃是中原腹地。
而一旦收复整个河南,大军屯田的弊端也就会显现出来,一个处置不当,便有可能引起兵变这样的大事。
这里面的官司,想想都让人头疼,朝廷那么多大臣,一个个聪明绝顶,会看不到吗?根本不可能,所以大军在河洛屯田,就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甚至于,这封奏章一上去,就会遭到无数攻讦,不用想,第一个有人便会跳出来质问,大将军张培贤的。
但不得已而为之,张培贤也无可奈何,今年秋收之后,还要靠朝廷救济过活,河洛上下还怎么自处?
不用朝廷说什么,河洛这里自己就得闹起来,这可是事关无数人前程宦途的事情,以后这波人出去,人家一听你是成武七年在河洛呆过,不用问,定然会另眼相看,这谁能忍受得了?
想到这些,张培贤终于微微点头,心中多少舒畅了些,既然你赵柱国来了河洛,总不可能光想着动刀动枪,那么别的事情,你也上上心吧。
思路一打开,看到张培贤神色缓和了下来,张先生这里也没闲着,微微一笑道:“既然如此,河洛匪患还多,其中闹的最凶的几处,匪首皆都是国武监分院生员,不如一并,交给晋国公”
这回张培贤没犹豫,干脆的摇了摇头道:“无论赵柱国,还是我张培贤,所行所为,皆为公义,不涉私仇,这么做不妥。”
杜先生悠悠然的看了一眼当即被堵了回去的张先生,心里暗骂了一声,小人,这样阴损的主意,也能说出来,你认为两位大将军闹着玩呢是吧,结仇不够深?真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没理脸色有点发红的张先生,他直接岔开话题道:“在下话还没”
张培贤脸上终于有了笑模样,点了点头,“嗯,先生接着说。”
杜先生还是那个样子,话音中透着老年人特有的平静。
“要说如今春耕啊,咱们河洛什么都不缺,就之前大帅有意上书朝廷,欲使大军屯田,在下就劝过大帅,为河洛大局计,大帅不顾一身荣辱,着实让在下佩服,但现在事情有了转机,我想,大帅也就不用行此无奈之举了。”
“先生说的是,那也是万般无奈,才会行此下策,如果赵柱国真有良方,可算是去了老夫一块心病,其余的,老夫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这回,杜先生脸上露出了些笑意,点头道:“大帅心胸宽广,实乃河洛上下之福也。”
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道:“所谓良方,晋国公再有能为,也不可能凭空变出来,在下到是可以猜一猜。”
这一下,张培贤真的起了兴致,追问了一句,“先生说说,老夫洗耳恭听便是。”
“那。。。。。。在下便姑且言之,大帅也姑且”
“说起来,农耕之事,困扰我河洛的不过是人,晋国公若有良策,跟人也脱不了干系,嗯,听闻朝堂有意整编殿前司禁军,细节处不太清楚,但汰弱留强之势已成,而晋国公又为枢密副使,只要他上书朝廷,有些事办起来应该很快,旁的不说,解河洛燃眉之急的法子应该多了才对。。。。。。”
听到这里,张培贤有些失望,却也心中渐渐敞亮了起来,失望的是,这法子自己用不了,敞亮的是,只要赵柱国有意为之,确实有可能解河洛危局。
他之前确实也没往这个上面琢磨。
一个呢,是因为殿前司整编的事情还只是风传,留在枢密院的字面上,另外呢,即便殿前司禁军开始整编,也耗费时日的工夫,他这个大将军插话的余地不多不说,河中,河间,京师东路这些地方,也非是他能影响的了的。
而赵柱国想到此处,张大将军也是暗自叹息了一声,赵柱国其势已成,实非他所能比了。
不过,若赵柱国真打的是这个主意。。。。。张培贤不免有些恼火,事关社稷的大事,其人竟然没跟自己露一点口风,不知打着自己多少的小算盘呢,如今虚耗许多时日,可曾为这一地百姓着想过半分?
不过,虽说心里有着诸般滋味儿,嘴上却还是笑道:“先生之言,果真让人茅塞顿开”
他心里虽有些不满,甚至可以说有那么几分嫉妒,但杜先生这番话的意义在哪里,他清楚的很。
这次跟赵柱国相谈,心里便有了些底气,能争的也就可以试着争一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这个意思了。
此时,张先生则来了一句,“杜兄果然大才,小弟着实佩服,当初可也正是先生,劝大帅立下了洛阳国武监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