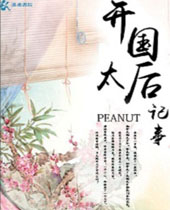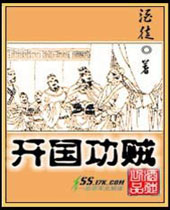开国功贼-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者:酒徒
简介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
一个码头上扛包的苦力,只想着吃上碗饱饭,娶个媳妇伺候老娘。命运却一次次地将他抛上天空,然后又一次次摔下来,鼻青脸肿。
历尽艰难,梦想却依然燃烧在胸。他,是巨贼张金称麾下的小头目。他是窦建德麾下的治乱能臣。他是大将军李旭眼中的爱民好官。他是唐高祖李渊眼中的………开国功贼。
他,什么都不是。
他只是他自己。
一个小人物在乱世之中寻找梦想的故事,希望大伙喜欢。
第一卷 好人歌
引子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话说唐人皮日休寄宿汴水河畔,闻桨声船歌而夜不能寐。感今日之繁华,悲往昔之民生,遂为一曲《汴河怀古》,以评运河开凿之功过。此诗一成,天下传唱。都道皮先生一语中的,说尽了前朝衰亡亡之因。却不知这前朝之败,远非一条运河所能承载。至于其中详细,各位看官且听我慢慢道来!
那大运河分为南北两条,南名通济渠,北为永济渠。南方直抵扬子江,北方勾连涿郡,宽二百四十余步,长三千五百余里,实为天下一渠也。自建成之后,日运财货百万,惠及两岸千年。唯独杨广这一朝,却丝毫没得到什么好处,反而种下了亡国的祸根?民间众口相传,杨广是梦见了江南的琼花,所以才不惜冒着亡国之险,修筑了运河。但隋帝杨广如果只是为了水殿龙舟直达江都,沿途玩耍享乐,又何必南北运河一同开挖,惹得天怒人怨?
各位看官有所不知,事实上,大隋之运河从杨坚当政时便已经开始挖掘,挖掘的原因也并非乃为了享乐。事实上,向北运粮,以对付辽东大国高句丽,才是其真实目的。
那高句丽国据传为箕子后人所建,起初不过弹丸大小一个村落。两晋之后,中原战乱不休,高句丽王依附于鲜卑人之下,不断向西侵夺。到了大隋建立之时,该国已经成了塞上仅次于突厥的第二大国,趁着杨广父子忙着对付南陈,无暇北顾之机会,不断挑起边衅。
开皇十八年,大隋君臣忍无可忍,派遣高颖带三十万兵马东征,无奈军粮不济,惜败于坚城之下。三十万将士埋骨荒野,归来者尚不到三千。
大隋二代皇帝杨广杀兄夺嫡,得位不正。急于建立功业,以塞天下人之口。所以登基之后,君臣上下一直谋划的便是如何讨伐高句丽,以完成先皇未竟之业。为了避免重蹈上次粮草不能接济的覆辙,从大业元年起,先后征集了近三百万民壮,将杨坚当政时的运河扩展开来,南北同时开挖,誓把扬子江、淮河、黄河、滹沱河、桑干水等天下大河连接为一体。耗时数年,终于凿成了一条沟通中原南北的水上运输要道。
运河修成之后,杨广立刻颁布征兵令,共募集将士一百零三万,民壮两百余万,沿河北上,浩浩荡荡杀向了辽东。怎奈东征的决心虽然大,君臣上下在骨子里却极其轻视高句丽人的抵抗之心。想着一战竟百世之功,又想向塞上诸部展示中原圣君的仁慈。结果高句丽王将士降后再反,反后又降,仅凭着一招诈降计,便将战事拖延了四个多月。
情急之下,杨广派遣心腹爱将宇文述带领大隋镇国之精锐,三十万府兵绕路偷袭高句丽王城平壤。那宇文述虽然在军中资历数一数二,却远非大将之才。再加上一个好大喜功监军自旁边擎肘,居然被高句丽人稀里糊涂地切断了补给线。导致三十万百战精兵无粮无援,全军尽没。
三十万府兵一失,大隋根基立刻动摇。杨广君臣急于挽回损失,第二年开春,立刻再度召集将士,展开了第二次东征。一时间,害得天下百姓困穷不堪,安居则不胜冻馁,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这二次东征还没等开始,天下已乱。河南有王薄、河北有孙宣雅、张金称、窦建德、陇右有高和尚,两淮有杜伏威,各举义军,攻城掠地。每到一处,屠尽富豪之家,洗干平民之门,官府屡屡征剿,均无建树。害得平时连大声说话都不敢的农夫商贩只好托庇于流寇之手,与之同流合污,以求苟延残喘。
消息传到朝廷,杨广召集群臣议论对策。群臣面面相觑,齐刷刷将目光看向了两位参掌朝政的重臣,素有天下第一、第二聪明人之称的裴矩和虞世基。裴、虞二位早就知道天下盗贼蜂拥而起,却一直瞒着不肯让杨广看见地方上来的告急文书。此刻被同僚们盯得毛了,焦急之下,果真生出一条妙计来。
这条计策便是:命令地方百姓统统迁居到城内,不给盗贼下手的机会。至于居住地点离城远的,便筑堡而居,闭门自守。贼人攻来,让他无钱财可劫,无壮丁可抓,坚壁清野,自然饿也将其饿死了!
杨广一听,觉得此计甚佳,立刻命地方上竭力执行。政令下达不到半个月,各府县城内人满为患,地价飙升,南北货物供不应求。乍看上去,居然比太平盛世的光景还繁华了数倍。至于城外的农田中是否有人耕种,草长得是否比麦子还高,却是顾之不得了!
第一章 城南(一)
六月的天气,太阳一出来,地面上就好像下了火。馆陶县的力棒们喝了半瓢凉水,又紧了紧系在腰间越来越显长的草绳子,三三两两地向运河边上走。(注1)
昨天后晌城西周善人家传出话来,说今日码头上会有一个大活儿给众人做。这兵荒马乱的年头,能赚到钱的活计可不好找!因此全城的力棒昨夜几乎连家里的婆娘都没碰,憋足了劲儿准备今天大干一场!(注2)
还没走到码头,有人心中的热乎劲儿已经消了一半。远远地就看见近几百个与自己打扮相仿,身材年龄类似的汉子蹲在河岸边。将官府平日收河捐的土台围了个水泄不通。同样是找活干,得讲究个先来后到的规矩。迟了一步没抢着好位置的人懊恼得直跺脚,骂骂咧咧地抱怨了几句,垂头丧气地蹲在了人群后。
失望之余,没有任何填补的肚子愈发显得干瘪了。临出家门时灌下去的那半瓢冷水早被头顶的日头给蒸成了汗,顺着毛孔滚滚排出。肠子肚子却咕咕噜噜,响声隔着二十步都能听得见。丢人丢到这份上,照理说大伙不如躲得远远的,等肚子里的动静消停了再过来排队。可那周大善人的货物没来之前,还真没人舍得走。万一活多得令排在前边的人做不完呢?多等一会儿,说不定就能赚上个三瓜倆枣儿。家里的米缸已经扫过三遍了,今天再不弄点儿吃食回去,明天就得给儿女头上插草标。
这样想着,肚子里的响声听起来渐渐也不那么窘迫了,反正周围的肚子你响我也响,大伙儿谁也别笑话谁。捱到太阳升上头顶的时候,河面上突然听到钟声。“叮叮当当!”听起来令人心里说不出的舒泰。早有眼神儿尖利者跳将起来,指着宽阔的水面高喊道:“船,船!快看船,好大的船啊,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
几百双茫然眼睛立刻放出了精光,不用招呼,大伙一个接一个跃起,摩肩接踵向岸边凑。靠近土台的人立刻被挤得站不住脚,一边用尽全身解数死撑着,一边扯着嗓子大叫:“别挤,别挤,老少爷们儿,再挤就出人命了。哎呀,我的鞋,老子昨天刚卖的新鞋啊!”
“得了吧,王二毛,你还有钱买鞋穿?讹人吧你就!从你光屁股满街跑那一天起,爷们就没见你穿过鞋!”后边的人接过话头,带着几分酸酸的味道调侃。腿上的力道却本能地缓了下来,以免真的将最早来占位置的王二毛等挤到河里边喂了蛤蟆。这运河刚修通没几年,水深得一个猛子扎不到底儿。万一出了人命,大伙都是街坊邻居的,谁心里也不会好受不是?
眼巴巴地,众力棒看着二十几艘特大号货船慢慢向码头靠拢。原本很宽大的码头立刻显得狭小起来,两艘头船被前面的人七手八脚用纤绳拉靠了岸,其他船立刻没了地方停,只好落了帆,如争食的鸭子般挤在河道里。
船多意味着活多,力棒们高兴得直跳脚。互相簇拥着靠近官府收河捐用的土台,等候周大善人的管家诚伯开价钱。早有家丁们支起了凉伞,桌案,伺候诚伯在胡凳上落座。梳着一缕山羊胡子的诚伯慢吞吞地喝了几口茶,将嚼没了味道的茶梗吐到地上,然后轻了轻嗓子,大声强调:“船上装的草袋和箱子都有五尺长,两尺宽,身高不过七尺的,就别向跟前儿凑乎了,免得累坏了你们,伤了我家老爷的阴德。”
“哪能呢,这方圆百里,谁不知道周大善人心肠顶尖儿好!就是诚伯您老,也是出了名的菩萨心肠!”众力棒们在脸上堆满笑容,异口同声地拍管家马屁。
“别翘脚,别翘脚,翘脚也没用。看看你们那身板儿,一旦把箱子摔到地上,连带着老夫也吃挂落!”诚伯举起端着茶盏的手,用小拇指挑着人群中几个身量不足的少年喝道,“回去歇着吧,大热天的别耽误旁人挣钱。平时多吃点儿好的,身体长足了再来!啊!”(注3)
说罢,他又满脸慈祥地坐了下去,低头品茶,再不看台子下一眼。
大伙不敢辩驳,纷纷用怜悯的目光看向那几名身高不足七尺的少年人。被大伙看得窘迫不过,几个少年低下头,黯然退出了人群。日光依旧烤得人难受,但少年们消失在远处那单薄瘦削的背影,却让人心里直发凉,从心窝凉到每个毛孔。
听家丁们汇报说“害群之马”走远了,“活菩萨”诚伯放下茶杯,笑着向大伙拱手。“感谢各位老少爷们帮忙,咱们周家也不会亏了大伙。路不远,只要将船上的木箱卸下来,从码头搬到官道旁,就算一趟完工。咱家的账房在那边等着,每人每趟会给大伙发一根竹签!”
说到这儿,他故意顿了顿,留点时间供众人将自己的话理解透彻。众力棒早已被船上吹过来的米香烧得如坐针毡,立刻七嘴八舌地回应,“诚伯,你老就接着说吧。规矩我们都懂!不就是按竹签结算么,自打有了这河,哪回不是这样?”
“对,您老接着说。我们明白,绝对不给您添乱!”
“诚伯,说吧,大伙听着呢!”
见众人没有异议,诚伯高兴地点点头,笑着从家丁手中抓起一根长半尺,宽一寸的竹签,举到面前:“老夫也是防患于未然,免得起了误会,坠了我们老周家的名头。竹签,大伙看好了,是这种涂了漆的竹签,上面有衙门的花押。大伙千万别拿错,免得被刘捕头抓去打板子。这乡里乡亲的,我也不能害了你们!”
“不会,不会,谁敢弄假的充数,大伙第一个不饶他!”众力棒们有求于人,心里骂老家伙狗眼看人低,口头上却不得不说些场面话来响应。
“那就好!”诚伯继续点头,脸上的笑容看起来比庙里的弥勒佛还慈祥许多,“干完了活,凭竹签到我这儿领工钱。每二十根竹签换糙米半斗。或者换肉好五个,即点即发,绝不拖欠!”
话音落下,刚才还兴高采烈的人群立刻如泼了冷水的炭火般炸了开来。“什么,二十趟才给半斗米,诚伯,这也忒黑了些吧。上个月给官府干,还一根签子换一个钱呢!”
“就是,诚伯,这价钱压得太狠了。大伙没法干啊。去年这个时候,可是七根签子就给一斗米!”(注4)
也不怪众人抗议。码头距离官道的确不算远,却是个大斜坡。背着百十斤的草袋爬坡,即便是有经验的老力棒,一天也顶多走二十个来回。辛辛苦苦一天只赚半斗米,累坏了的人自己就能吃掉其中一半。剩下的那点儿拿回家去,也就够老婆孩子们喝上几天稀粥的。若是类似的活经常有,大伙还咬着牙能答应。可这种大活儿一年也就干一次,今天做完,明天就再无其他营生可做。那就意味着一家大小要挨饿,意味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让众人怎地不为自己而争?
“去年!”诚伯将脸色一摔,冷冷地道:“去年是什么黄历?去年一斗新米不过五个钱,今年这馆陶城里,少了十个钱你能买到陈米么?小老儿我是看在乡亲的份上才开这个价儿,不信你们去武阳郡城里边打听打听,不给工钱,光给顿饱饭吃,也有人打破脑袋抢着干!”
对这些从小没离开过家门四十里外的汉子们来说,郡城武阳与皇帝老爷领兵征讨的辽东差不多是一样的遥远。没凭没据,谁也不敢与管家硬犟,纷纷低下头去,在心里计算自己努力干上一整天,能否给家人赚回一顿饱饭。个别胆子大的,则坚持诚伯按照官府先前的旧例支付工钱,否则大伙就干脆都不接受,任船上的货在河道上晾着。
那诚伯怎是个受要挟的主儿,咧嘴冷笑了几声,用小拇指点着土台上的众人道:“呵呵,还真有人不知道好歹,拿官府来压小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