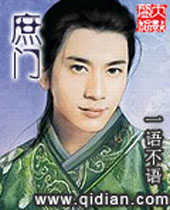庶门-第40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柳丽娘轻哼一声,道:“若真有那么一天,十二少你哪还会容得下奴家……”
刘愈一笑,柳丽娘的政治觉悟很高,知道朝廷容不下一个独立于朝廷强大宗教“圣女”存在。
刘愈笑道:“那到时候,你做圣女,我做教主,咱们夫妻同心……打遍天下无敌手。”
听到刘愈这么说,柳丽娘也就释然了,她心想刘愈也只是开玩笑,不是真让她去做什么圣女。
柳丽娘指了指楼上道:“十二少忘了红颜知己还在?”
“对,倒把她给忘了。”刘愈不是没记性,是在柳丽娘面前故意表现的没记性,“走,丽娘,一起到楼上去,让我见识一下你和璇儿的舞姿,到底谁的更优美一些。”
柳丽娘听到“璇儿”的称呼,再轻轻一哼道:“还有谁,当然是你家璇儿更胜一筹。”
“丽娘,别说我打击你,你这些年来走南闯北,舞蹈上的功夫怕是早就生疏了,但我也对你有信心。如果你输了,今晚……就好好惩罚你,非让你下不来床。”
柳丽娘听刘愈这么一说,恨不能踩刘愈一脚。这么一说,她本能能赢,也或许不想赢了。
等刘愈和柳丽娘回到三楼厅堂,司马璇儿正专心致志在鼓架子上跹跹起舞,浑然没察觉到刘愈和柳丽娘的折返。
柳丽娘在旁看了一会,低声对刘愈赞道:“别说,你家璇儿的舞蹈还真不赖呢。”
“那当然,也不看是谁的眼光……”
柳丽娘白了刘愈一眼,转回头继续看司马璇儿的舞姿,司马璇儿也是太忘我,一曲跳完,正要收势,突然察觉到刘愈和柳丽娘在旁目不转睛看着,心下马上又慌了。
别人看她跳舞,她没觉得怎样,但在越想表现舞姿的人面前跳,心中越是紧张局促。一紧张,脚下不稳,自然而然又从鼓架子上摔下来。
“小心。”刘愈喊了一声,正要上前去扶,却见一个身影速度比他快了许多,往前而去。
那身影抱住司马璇儿,原地一个旋转,好像英雄救美一样,刘愈心想天上再撒点花瓣,那就更像才子佳人的某种相会场景。只可惜,这位风姿翩翩的公子,却是女扮男装的柳丽娘,而她跟司马璇儿之间,也不是才子佳人,只是互相较劲争夺他刘愈宠爱的女人而已。
第六百四十六章叛逃与叛军
欣赏过柳丽娘和司马璇儿共同起舞的舞姿,刘愈也觉得此趟没有白走一遭,只可惜他不能得偿所愿一时共拥双美,心中不免有些遗憾。回到宫里,司马璇儿还在回味着之前与柳丽娘跳鼓上舞时争艳的场景,在她看来,学舞蹈这么多年以来,这一天是最有意义的。
臭棋篓子跟臭棋篓子下棋,比谁的棋更臭。而舞蹈大家自然想跟舞蹈宗师一较高低,来证明平生所学不是白学。
司马璇儿虽然已经猜到刘愈跟柳丽娘的关系,但她很识趣,什么都没说。回到宫里也三缄其口,连李遮儿问询她也做了隐瞒。
时间很快到了十一月下旬,自从柳丽娘在晓花楼当了三清教挂名的教主,刘愈所编写的新教义便在三清教内部传播开来。自开始肃清三清教开始半个多月时间,刘愈也一直都在观察情势的转变,细作也会将三清教内部的情况反馈给他。
到十一月底,长安城内已经恢复了太平,原本的戒严也变成宵禁,长安城百姓的生活也趋向于正常。在长安城内,到处都充斥着对“邪教”的鄙视,甚至连叫花子,都能说出邪教的巨大危害,刘愈知道这是京兆府的功劳,王虎在宣传这件事上做的不错,该做的也都做了。
而从十一月下旬开始,派驻到地方上六部的官员,第一批也已经回来了。
回来的这批人,基本都是到地方走了个过场,看了看风土人情。说是要肃清三清教。很多官员连三清教教徒的影子都没看到。便已经打道回府。不过刘愈显然没那么轻易放过他们,六部第一批人刚回到长安城家里,屁股还没坐热,刘愈便已经在雅前殿召集,令他们在一天时间内,把地方上肃清三清教的经验和总结写出来,第二天朝会上就要上交。
刘愈也明言,若谁写的不好。敷衍了事的,官也不用当了。
这批官员一听个个自危,他们也真怕刘愈借机会肃清朝中敌对政党,都怕惹火烧身。
在回来这批人中,并没有六部的尚书,领头的都是侍郎及副官级别,刘愈也特地让六部的主事人在地方上多呆些时日,多了解一些民生。
自从李延年离开长安城后,李遮儿便从来没有过问过父亲的事,看起来她对家里人丝毫都不关心。不过刘愈却发现私下里,李遮儿收到家里的一封家书。似乎说的便是李延年的事。李延年当初得脱不死,妻离子散,重新在朝为官之后娶了几个小妾,且已经有小妾为他生下孩子。也就是说,李遮儿现在已经有了同父异母的弟妹,现在李家当家人不在,而李家又人才凋零,李家有什么事自然要求助于已经身为皇宫中女人的李遮儿。
在饭桌上,刘愈也问了李遮儿家中是否有事,李遮儿表示没事,不过私下里,李遮儿也把家属拿给他看,刘愈才知道李延年离开长安城后便跟家里断了联系,连封信都没写回去,她的那些姨娘都担心丈夫回不来,才向她打探李延年的事,但因为宫闱深宫大院,李遮儿的姨娘只能写了信,托了关系才把信送进皇宫。
“你父亲离开长安城后,没跟家里有联系?”刘愈在看完李遮儿的家信之后,觉得有几分诧异。
李遮儿点点头,没多说话,虽然表面上她装作对家里不关心,但实际上,她也的确断不了李家的亲情。李延年以前再怎么浑,那也是她的父亲。
平日里李延年的父亲,对家里那些女人也算疼爱,这点朝中上下也有传言,说他为了延续家族血脉,对家里的女人是百般呵护,一些老臣也开玩笑说,毕竟李延年是老牛吃嫩草。李延年离开长安城后,给朝廷的汇报不少,这些汇报是不用尚书本人来写,所以刘愈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李延年写的,又或者是李延年已经“叛逃”了。
“回头,我找人到地方上见见你父亲,让他带个平安给李家的人,让她们暂时不用担心。”
刘愈拿着那封家信出来,直接找了负责情报工作的瞿竹,让他去调查李延年到底还在不在地方上。让他查清楚第一时间过来回报。
刘愈也知道朝廷大臣叛逃的危害性,之前在他完全没有想到时,他所信任的杨烈突然失踪,踪影全无,那时候他就留下一个心眼,不能过多的相信外人。不管怎么说,他在搞情报调查别人不为人知的秘密,别人也一定在反调查他,这些事他必须要做的小心。比如在调查情报上,他就把人物分给瞿竹、瞿书和柳丽娘三系人,然后综合情报来分析局势。三系情报中关于三清教内部的,柳丽娘的最为确切。
在瞿竹着手调查李延年是否叛逃的第二天,腊月初一,刘愈突然得到柳丽娘的线报,说是三清教内部有不寻常的聚集活动,并且已经在两天前开始,聚集的方向,便是刘愈曾去过一次的朗县县城。
柳丽娘的住所里,柳丽娘把从三清教内部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传给刘愈,这消息,其实本来三清教苏哲派系的人也在保密,从上面下达下去的指令是,让被朝廷压迫的教民跟着神的指引往西走。开始时,柳丽娘只是分析,这是苏哲派系为了把长安城周边的教徒调开,不曾想,在腊月初一这天,柳丽娘得到最新消息,说是这些教徒其实都是在往朗县的方向聚集。
“大约有多少人?”刘愈直接问道。
“长安城周围大概有上万人,若加上关中教徒的话,在三四万人左右。”柳丽娘心有余悸道,“幸好我们及早得到消息,而且奴家已教主的身份,让下面一些人通知最底层的教徒,中止了他们这次的朝拜活动。但即便这样。还是有几万人往朗县去。十二少。奴家估计这批人是要到朗县,举反叛之事来跟朝廷对抗。”
刘愈心中暗忖着,同时他也点点头。柳丽娘分析的基本也是他所想,因为朝廷这次肃清行动太过迅捷猛烈,自上而下,三清教教徒已经到无法容身的地步,苏哲感觉到大势将去,不得不提前发动这样一次聚集朝拜。来完成聚事反叛朝廷的目的。
刘愈叹道:“可怜这些教徒,还以为去朝拜避难,其实是被人利用了而不自知。走上武力反叛朝廷的路,他们也就彻底没有活路了。”
刘愈没有马上调兵往朗县去,倒不是他对柳丽娘的情报不放心,而是刘愈怕这是苏哲放出来的一次烟雾,故意让他知道,调虎离山。苏哲在朝中肯定有同党,在军中也未必不会有。若是他把朝廷的精锐之师调去朗县,会造成长安城军事上的真空状态。虽然朗县距离长安城不远,但长安城周围的戍卫军队距离长安城更近。一旦被叛军以某种理由进城,控制了长安城,就算是刘愈身在朗县,一时也无法叩开长安城大门。而到时候长安城一旦落入苏哲手上,正统的问题就要发生更改,天下到底向谁的问题也就不好说。
刘愈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三清教聚集叛乱之事,这些日子以来扶着戒严长安城的是新军,但这次刘愈却不想调绝对亲信的新军去朗县平乱。
“本将军经过慎重考虑,将以南长安大营和东水营军队后后盾,往朗县方向,若遇到流民闹事,或者是有武力对抗着,一律按剿匪处置!”
参与军事会议的不必但包括刘愈的嫡系,还有些本身是旧朝将领嫡系,又或者是边军嫡系,他们虽然名义上是刘愈的属下,但跟刘愈向来也是貌合神离,刘愈要差遣哪只军队平叛,是刘愈说了算。不过刘愈所下的任何一道指令,这些人也都会揣摩,到底是亲疏有别,还是另有目的。
这次刘愈调长安城两大戍卫军队去,虽然看似正常,毕竟朗县距离长安城七十里,在这两支军队的巡逻范围之内,可毕竟现在长安城中人所共知的精锐军队是新军。把精锐留下,而派次一级的军队去平叛,到底是瞧得起还是看不上?
刘愈这一说,会议上的氛围又不太好。一些旧朝将领似乎在闹情绪,不过他们也不敢公开闹,只是提出一些看法,比如说是对这次是否将有匪事发出质疑。再者,他们也对武器方面提出一些要求,比如更新换代一些武器,或者是训练不足什么的,总之就是跟刘愈提困难,提条件。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不过这次去的是朗县,距离长安城不到百里,快马一天都能跑个来回。这么多条件在刘愈看来,就是这群将领不识相。
刘愈也早就料到会有人有意见,不管刘愈调那支军队去,其他军队都会想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这年头的军人是很敏感的,他们既追求容易,又不想当炮灰,既想建功立业又怕马革裹尸去了战场回不来。总的来说,这年头的军人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体,做什么事他们也满意也就怪了。
“是否有匪事,不劳诸位操心。”刘愈道,“这次平叛,不是小打小闹,虽然所面对的不是凶悍的突厥骑兵,也不是逆王的精锐之师,却都是关中平实的百姓。若是能仁慈,也尽可能仁慈,不要对同胞下手,也许当众就有你们的父母兄弟。”
刘愈这么一说,各军的将领才感觉到这是烫手的山芋,接不得。平叛失败那是失职,平叛成功却又是残害关中百姓,反正是两面不讨好的事,谁去做也别轮到自己做。
有这想法的人,占了与会人的大多数。
“此次平叛,必须立下军令状,若是哪军哪部没有完成既定战略,而平叛中发生什么差池,那一律按照军法处置,不论是士兵还是将军,一视同仁,该怎么罚怎么罚!”
与会的毕竟不都是刘愈的嫡系,这样的会议也失去以往刘愈所开嫡系会议时候的庄重。一些将领甚至觉得不屑,认为刘愈是小题大做,不过是有一群流民想往西南的方向走。就被刘愈看成是要去聚事反叛朝廷?什么立军令状的。难道朝廷的正规军。连一群乌合之众都对付不了?难道那群流民不怕死?
只有刘愈知道,虽然关中教徒聚集,即便反叛,也只能揭竿为旗斩木为兵,战斗力不强,甚至教徒中还有很多妇孺和老弱病残。但这些人背后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刘愈依然记得当初第一次拜访楚王府时,所见到的情景。苏哲治下的严谨,就好像病态狂一般苛刻。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哲会培养起一支完全效忠于自己,且能跟朝廷一战的大军也未尝不可能。一旦这些先头部队取得胜利,会让背后的教徒以为他们是刀枪不入无往而不利,那时候一群流民也能干翻一整支正规军。
刘愈老早便听说过,旧社会一些打着宗教幌子的“义军”,他们胸口贴着黄纸便以为是铜墙肉身,那股不怕死的紧不是装出来的,是因为他们真的就相信。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刘愈把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