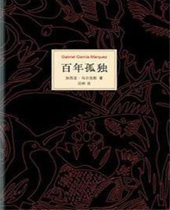饥饿百年-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用,便双双落下泪来。
何兴能说:“我们想抱养你一个孩子。”
这一下,轮到李高氏落泪了,她说:“我早就看出你们的心事。按理,我是舍不得把孩子抱养给人的,但你们是好人,对我们娘儿有恩,我答应你们。”
说罢她放声大哭,一遍一遍地呼喊我曾祖父李一五的名字。
何兴能和张氏安慰着李高氏,表示一定把孩子带好。
翌日,李高氏带着大儿子李田离开了何家坡。
李高氏何以要把自己最喜欢且寄予厚望的李地留下?是因为李地比哥哥聪明,凡事自有主张,留在别人家里,不会受欺负。
我父亲说,李高氏回到李家沟后,又挣了许多田产。但父亲也只是听说而已,事实上,李高氏和李田一离开何家坡,就音讯杳无,李地再没见到过母亲和哥哥。
李地改名为何地。那一年,他十二岁。
何兴能和张氏巴望李高氏从此消失,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全占有何地。何地是他们最宝贵的、没花多大代价就得来的财产。一度,他们禁止何地出去跟别的小孩子玩,生怕这件财宝受了损伤。可何地虽然形象斯文,童心却在,不仅想跟同龄人接近,还要跑到大山上去,掏鸟窝,寻野果,捡拾猎人的枪弹切割下的五光十色的羽毛。何兴能将他锁在家里,即便大冬天哭出痱子也不放他出去。何地要被关疯了,他说我不玩了,我念书去!何兴能颇感新鲜,念书?十几岁的娃娃,马上就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为我何家传宗接代,还念啥书?在何家坡,何华强算发财了吧,可从他高祖父算起,就没一个人读过书!何华强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却陆陆续续购置了上百挑田产,把土地侍弄得该长啥就长啥。这种比较让何兴能和张氏觉得读书是多么无聊。他们只需要有个儿子就行了,念不念书无关紧要。这个儿子不仅要为他们养老送终,还要去跟那狗日的何华强斗;眼下不能跟何华强斗,将来也要跟何华强的后人斗!……此外,他们不让何地念书,还有一层隐秘的担忧:传说清雍正年间,何家坡出过一个读书人,名叫何条元,此人才高八斗,狂放不羁,上京应试,竟把放在考官旁边的花翎先戴在头上再坐下答题。返乡途中,他买了一木船书籍,边读边扔,过目成诵。他中了进士,人未到家,榜已送达。谁知,他的木船刚进清溪河,突然腹痛难忍,暴死船中。何家坡人由此得出结论:此地只养罗大人那样的“武棒槌”,不养读书人——更何况,据说当年的何条元,就住在何兴能的屋基里!好不容易捡一个儿子,怎舍得让他半途夭折?
但何地不管这一套,威胁说,如果不让他念书,他马上就去找母亲和哥哥。
母亲遗传给他的坚定性格使他说一不二。
何兴能和张氏被迫只好同意他上学。
何地的聪明才智,从上学的第一天就展露出来,他不仅能背书,还能讲书,他的许多即兴发挥,让杨老先生一面大摇其瘦长的脖子,一面称赏不已。由于何地的超凡出众,使他很快就在同学中建立了威信,那些取笑他是外乡人并扬言要把他赶出何家坡的同学,不仅不敢再取笑他,还争先恐后巴结他。何地就在被巴结当中坏了德性。他让何家坡的同学做了一乘滑竿,上学的时候,一进入老林,就坐上滑竿,由同学把他抬到学堂附近,再将滑竿藏进林子;放学后,走到先生看不见的地方,就把滑竿拖出来,同学将他抬回何家坡,快出林子,他又下来,并将滑竿藏好。他这样逍遥了一年,突然得了“铁斑麻”,浑身长红疙瘩,连成一片,在当时的乡村,是绝症,可何地自采草药,捣碎之后,箍在身上,竟将铁斑麻“箍”好了!
此时,何家坡来了一个算命先生,说何地是文曲星下凡,是比曾中进士的何条元还大的一条鱼,何家坡山太雄,土太薄,养不活这条鱼,如果他再读书,不上二十岁就会戴顶子,戴上顶子不出三月,就会死于非命。何兴能和张氏惊闻此言,再不让何地走鞍子寺那条路了。
何地自己也被吓住,并不强求上学。
他不知道,那个算命先生是何兴能特意找来且按他的旨意说出那番话的。
儿子不再上学,张氏这才把心放到肚子里去,到处物色媒婆,要为儿子定亲结缘。
何地十六岁里定下亲,女方是何家坡后山——望鼓楼的人,姓许,单名一个莲字。她后来成了我的奶奶。父亲只用一句话来形容奶奶的长相:漂漂亮亮的。这一句过分抽象的话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许莲的美,至今被人传扬,那些跟父亲年岁相仿的老人不服气某个模样儿生得周正的新媳妇,往往就是一句:“赶许莲差他妈蛮天远!”某年,我从外地回到故乡县城,在朋友家无意中翻阅民国时期当地文人出版的一部笔记,在“人物门”中竟有这样的句子:“老君山多出美妇,望鼓楼许素和之女许莲,年未及笄即有闭月羞花之容,嘴角一痣,似能言语,星目流转,顾盼传情。”这样的一个美人胚子,之所以沦落为我的奶奶,一为家贫,不与豪门纨绔公子般配,二为山高,不被怜香惜玉者所识……
谁知,何地定亲不久,何兴能便一命归西,张氏也深感自己来日无多,就想给儿子完婚,无奈儿子守孝期未满,不能议定婚事。没想到仅过两月,张氏又死去了。张氏死得很奇,吃罢晚饭,她坐在火塘边打瞌睡,何地提了一桶猪食,泼泼洒洒地一边出门,一边说:“妈,瞌睡来了上铺里去困嘛。”张氏唔唔应声,还睁了眼说:“人老了没球得祥(福气),一坐下来就想挺瘟。”其间,三曾祖父何兴孝和妻严氏进来了,张氏招呼他们坐了,又继续打瞌睡。何兴孝把火塘掏了一下,加进一块烘焦了的青㭎柴,火便熊熊地旺了。严氏对张氏说:“这么大的火,坐那么拢,不怕把胯里的家私烤糊了?”张氏没回话。何地喂了猪回来,跟三爹三母打过话,又喊母亲到床上去睡,喊了数声,张氏没有反应。猛然间,何兴孝听到囫囵一声响,接着张氏的脖子搭了下去。何兴孝惊慌地吼叫:“娃娃,你妈怕不行了,我刚才听到她跨过奈何桥的脚步声呢!”言毕去探张氏鼻息,果然已经断气。
何地哭了一回,在何兴孝的帮助下,安埋了母亲,就锁了房门,上李家沟去寻他生母和哥哥。他打算把生母和哥哥接到何家坡来。这几年,由于有了何地的帮助,何兴能又买了几亩田,日子当然比李家沟好过。
何地到李家沟,根本没有生母和哥哥的踪影,以前的几亩田,早被别人占去。
他什么也没说,阴悄悄又回了何家坡。
听说何地要去接生母和哥哥,何家坡头号财主何华强情不自禁地摸了摸那根皮面溜光、头部沾了星星点点狗血和几根狗毛的打狗棒。这根打狗棒他已用了十年。如果李高氏敢来,何华强将以极端的方式把那家人赶走。后来,何地一个人回了何家坡,何华强便只是冷笑两声,把打狗棒藏了起来……
何兴孝对何地说:“娃娃,你爹妈都死了,那些旧规矩就不要了,依我看,赶快把婚结了是正经。”邻居都这样劝他。见过许莲的人说,那女子家里虽穷,可美若仙人,再拖延下去,说不定会拖出变故。何地完全没了主张,一切依照三爹三母的意志去办。
来年的春天,我爷爷何地还没满十七岁的时候,与老君山望鼓楼的许氏完了婚。
爷爷和奶奶婚后的生活,我父亲何大往往羞于谈论。
结婚那天,何地与许莲入室合卺之后,十余青壮男人就闯进新房,嚷着要喝新酒。何地捧出一口酒坛,请他们畅饮。这些男人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都已结婚,对男女之事也早已了然,却永远不失新鲜,一个说:“何地,你龟儿子今天晚上就莫想歇气哟。”何地不懂,殷勤地说:“你们耍,耍一晚上也无妨。”一阵大笑之后,众人说:“我们不想耍,我们想帮你干活哩!”何地说:“晚上干啥活呢,外面连个月亮也没得。”又是一阵大笑。许莲粉颈低垂,面颊早已红过耳根。见新娘如此,一帮浪荡子更加来了兴致,一个说:“何地呀,今晚你可耍不成,要打井哩。”另一个说:“别看是一眼现成的井,要打下来,非把你龟儿子累得七吼八吼不行。”何地依然没懂,痴痴傻傻望着他们憨笑。一个年纪稍长的说:“何地,你找不找得到那眼井在哪里?”众人附和:“他肯定找不到,我们都是好兄弟,帮他一把好啦!”说罢,一个满脸长着疙瘩的家伙竟在许莲身上动手动脚。许莲一边躲,一边向何地斜瞟,见何地还在憨笑,她便将头一扬,正色道:“要喝酒就喝酒,不喝酒就各自回家歇息。何地,时间不早了,把灯点上,送各位大哥回去,明天一早,我们还要到酸梨树坡薅草。”
许莲初来乍到,竟知道酸梨树坡是何地的土地,证明她早已从父母的口里对何地的家境知根知底了。
这些青年毕竟是农家子弟,本无坏心,经许莲这么一说,亦觉无趣,不要何地拿灯送,相继出门去了。
他们并没走远,出门又集合到一处,悄悄转到新郎新娘窗下,要听个究竟。
通常情况下,听房者要冻得、站得、累得,直到后半夜才会有收获的,可这群人刚一转到窗下,就紧张得大气也不敢出。
许莲对何地说:“你当真不晓得?”何地没有应声,许莲说:“在这里,你摸摸就晓得了。”接下来就全是许莲的声音:“……憨子,你发抖了?……噢……痛……没事的……”几分钟后,有了何地的喘息声。何地说:“还真有趣。”许莲哼哼唧唧一阵,屋子里才静下来。
窗外阴沟边拥拥挤挤的十几个人,发出一片声的气喘,好在并没被何地听出是人的喘息,他以为那是偏厦牛棚里的老牛在反刍,或者猪圈里的猪因为吃得过饱在放屁。差不多过了半个时辰,他们正打算离开,没想到许莲又说:“还来吗?”何地急切切地说:“还来。”一阵乱响。比第一次孟浪得多。那些年轻人忍耐不住,便一个接一个地回家去了。
那天晚上,有七八个人都打了自家婆娘,说她们无用。
许莲是一片丰饶的土地,让何地从未有过地滋润起来了。由于生在穷人家,许莲对什么农活都在行,里里外外也收拾得干净利索。何兴能和张氏离世的前两年,家里雇了短工,许莲嫁过来,就把短工辞退了,她认为两个人做几十挑田的活,是没有资格雇人的。奇怪的是,不管怎样劳累,许莲都嫩白如初。只是何地消瘦多了,同辈人——尤其是在何地与许莲的初夜听过房的人,就取笑他:“莫信你婆娘的话,还是雇个短工安逸点。”何地老老实实地说:“她干的活比我干的还多。”同辈人说:“傻子!她只是白天干,你晚上还要干嘛!”何地知道他们说孬话,满面羞红,那群人就把在窗下听到的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何地羞愤交加。回家后,他跟许莲赌气,许莲莫名其妙,取下挂在花篮口上的一根狗尾草,去撩丈夫的鼻孔。没想到平时说话斯斯文文从不发火的丈夫,竟然给了她一个耳光,还骂:“不要脸!”许莲摔倒在地,百般委屈涌上心头,但她并没流泪,艰难地爬了起来。她没有摔伤,可她的肚里已装上了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出生在青黄不接的农历二月。这似乎早已注定了他一生的苦命。在生育孩子方面,许莲有着远大的理想,何地本想给孩子取一个文雅些的名字,可许莲坚持己见,把第一个孩子取名何大。她想这样依次排下去,何大何二何三何四以至无穷。果然,仅仅一年零两个月后,我的二爹出生了。我二爹当然就叫何二。
春天里,金子般的油菜花漫山遍野地开放,整个何家坡弥漫着令人昏昏欲睡的药香。中午时分,许莲从坡上弄回一大花篮牛草,就坐在门槛上奶何二。她的头发已被汗湿,一绺一绺地粘贴在白皙如藕的脖颈上;当她把衣襟打开,奶膛里立时喷出一股热气。她挺实雪白的乳房上,也密布着鱼子样的汗珠。何二不管这些,咂着汗津津的奶头,两只手还把母亲的两只奶握住,生怕被别人抢了去似的。这当口,何地回来了,他也弄了半背牛草,牛草之上,坐着下巴尖尖的何大。我父亲说,在那年月,大人上坡干活,哪怕是六七岁的孩子,也用小衣捆在床上,唯许莲不捆孩子,何地要捆,被许莲坚决制止了:“成天扔在家里,太阳也照不到,娃儿咋长?手脚一捆,连个痒处也搔不到,舒服吗?娃儿再小也是人!”一旦上坡干活,就是何地带一个,许莲带一个,即便她挑八十斤一担的粪上山,也把孩子用布条绾在背上。
何地回来后,坐在街檐下的青石坎上抽了袋叶子烟,神经就有些不做主,好像有什么东西遗忘了,一时又想不起来,心里痒得难受。这时候,何大在石坎的缝隙里掏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