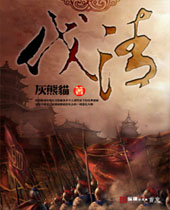逆流伐清-第35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红色小点在团团白烟还未消散时便撞入清军混乱的阵线,在山呼海啸的喊杀声中,锋利的刺刀对着清兵一轮轮的捅刺,收割着战场上廉价的人命,精神崩溃的清兵发出声嘶力竭的嚎叫,慌不择路的亡命奔逃。
突破。凿穿,在明军的猛攻下,清军的阵线如同被洪水冲毁的堤坝,一段段的垮塌,最后终于全线崩溃。广阔的战线上,逃命象可怕的传染病飞速传播。到处都是争先恐后逃命的溃兵,他们面色如土,惊慌喊叫,在明军的逼迫下四散奔逃。
精神崩溃的清兵互相践踏,在逃命中迸发着疯狂,骑兵砍杀着挡路的步兵,步兵则刺杀那些停顿的骑兵,只为争夺一匹坐骑,汉兵不再惧怕八旗。戈什哈们也不再护卫那些主子,人人都只为自己的性命争斗,溃兵互相砍杀,相互践踏,旷野上尸横遍野。
主攻部队向两翼席卷,突进兵团开始沿着凿穿的通路滚滚向前。先头部队则是两千骠骑兵,三千龙骑兵。从镇朔军调来的两千骠骑,以及五个军抽调的龙骑兵。几乎是正面明军所有的机动力量了。
庆阳王刘震纵驰战马,缨盔两侧响起了畅快的风声。冬季地面上腾不起太多烟尘。逃敌把背影和后脑展露在明军骑兵的面前。不是对冲,只是几乎没有危险的追杀。
追杀在最前面的是王辅臣,他率领着一飚骑兵狂猛追杀,手中的豹尾枪不断地向下滴着血,虎目圆睁、咬齿嚼唇,脸上的胡须也一根根地炸起。不断有清兵被击落下马。即便不是致命伤,也会被后面的明军骑兵砍杀,或者被马蹄踩死。
畅快的情绪感染着所有纵马奔驰的明军骑兵,所有的不痛快都随着这一下下的劈砍而被逐出体外。又有一个敌兵落马了,这个清兵拼命挥舞着双臂。没跑出几步,一把锋利的大刀斜着砍来,人头落地,血柱冲天。
嘿,刘震痛快地哼了一声,这是他的亲卫让着他,让他也有机会让自己的刀刃染血。
如果说到官爵,按照刘震的年纪,已经是非常令人惊叹了。但问题也出在这里,同李嗣兴一样,刘震希望用自己的功绩证明自己的爵位是实至名归,而不是承袭祖荫。
在陕西,骠骑兵也有过胜绩,毕竟镇朔军中是最早开始墙式冲锋,掌握这种战术最熟练的部队。但刘震却觉得远远不够,远远不够他这个郡王所要获得的功绩。所以,调令一下,他便主动请缨,要求带兵参加这场历史性的大战。
晋王李定国因为在陕西的推进缓慢,影响到了整个战局而心中歉疚,也为了证明镇朔军的实力,派出了精兵强将。赶来参战的骠骑兵不仅是精锐,更有王辅臣等猛将率领。
也正是因为明军的骑兵少,便愈发显得珍贵,使用也更加谨慎,也就使骑兵看起来威风,却少了很少建功的机会。此番作为突进兵团的先锋,刘震等人憋足了一口气,非要拿出象样的战功来证明自己。
在先锋骑兵之后,是大批的步兵和辎重车辆。沿着官道,汇成一道看不到边际的长龙,扭头摆尾地前进,前进!
…………
“胜利了。”魏王马宝投入了全部灭朔军,以加速摧垮清军的防线,在已经毫无变数的情况下,他长出了一口气,说出了自己的感悟,“这是银子堆起的胜利啊!”
银子堆起的胜利,是不是亵渎了英勇奋战的官兵,是不是忽略了千千万万为国战贡献力量的人们呢?
其实,马宝的这句话在表述上并不是十分准确,可也不算离谱。如果改成“战争打的就是后勤”,应该是更加贴切准确。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古代战争消耗的多是粮草,因为冷兵器作战对弹药的需求是很少的。但现在的明军之所以强大,却多是靠的武器装备。火炮,火枪,连带着消耗的弹药,以及粮草军饷,如果换算成银子的话,自然不能说马宝的感悟是错的。
投入是不断的,累积起来则是个惊人的数字。在庞大的投入之后,朱永兴打造出了足以称雄世界的陆军,随之而来的则是高于满清数倍不止的后勤供应。上千艘的江船海船在运输,十万以上的工人在制造修理,数百万的农民在耕种垦殖,到现在为止,累计投入的银子更达千万以上。
取得决战的胜利只用了两三个时辰,但支持胜利的准备却持续了数年之久。这是一个厚重的基础和保障,现在的明军固然可能打败仗,但只要基础和保障存在,几次失败也无法彻底击垮明军,也无法改变大局。
…………
第七十九章雪中送炭
运气,实在是个奇妙的东西。历史上,满清灭明,在很大程度上,在很多事件上,都表现出这个奇妙东西的作用。
真的有什么气数这个东西吗?朱永兴不明白,为何老天不长眼,为何要让文明被野蛮摧毁,为何要让神州沦于黑暗,为何要让中华从此走向愚昧和落后?
但现在,运气似乎被他夺了回来,中华的气运也逐渐掌握在他的手中。他更相信了那句话“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宗守义干得好。”朱永兴接到湄、河总督宗守义的奏报后,不禁脱口称赞,精神也为之一振。
尽管扶持傀儡、掌控他国的手段是朱永兴在安南所最先使用的,并且把这套思想进行了传授,特别是对维持开拓海外领地的宗守义,更是言传身教,书信不断。但此次宗守义策划并实施的行动,依然令朱永兴感到欣慰,感到振奋。
真腊(现柬埔寨全境,包括泰、寮、越三国之部份地区)之前夹在暹罗和南阮之间,成为两国争雄的舞台。南阮失败,王室流亡于明境,北郑取而代之;暹罗王室内讧,亦无力再施加军事压力。所以,现在的真腊,成为了明朝与北郑争夺的对象。
从总的实力来看,明朝的实力是强大的,但从局部比较,明朝在中南半岛的驻军数量则显得不足。特别是水师大部北调,滇省兵力又多集结于滇缅边境,在中南半岛便只能凭湄公、河仙两省的五六千人马,以及安南占领区的数千士兵。
虽然如此,面对明朝的强大,北郑依然是不敢轻易起衅的。但在真腊的争夺中却可以既扩大疆域,又可以尽量避免与明朝的冲突。毕竟真腊是个弱国,谁得到便是谁的,就看谁下手更快了。
基于这样的形势,宗守义在不放弃争夺真腊的前提下,隐忍并放缓了一举制服真腊的计划。在真腊再次爆发王位之争后。宗守义命令宜川伯高启隆调动大部兵力,并联合猛山克族央部的两千精壮勇士,悍然出兵。而北郑也不失时机地介入真腊内乱,希望扩大疆域。
果断而凶猛,明军的兵力虽然比北郑少,但在气势上却不落下风。因此,在这场趁内乱而出兵的干涉行动中,明军与北郑算是各有所得,以双方的默契瓜分而收场。
从此。真腊一分为二,明军拥立匿螉秋为王,北郑则拥立匿螉嫩为王,各自都得到了大片的土地和无数的百姓。
都很聪明,朱永兴越发对北郑的新进郑根刮目相看。立傀儡似乎比不上吞并更霸气,更强势,但却有自身的优势,那便是能尽量减少当地民众反抗的情绪。不需动用太多的兵力,耗费太多的时间才能够稳定秩序。
可见宗守义对现在的大形势有着很清醒、透彻的理解。不是那种贪图眼前功劳,却给主上惹下身后麻烦的官员。不必太多的投入,便取得了这样理想的成果,朱永兴自然十分地赞赏。
而郑根也扶持傀儡,则显示出了他的沉着和冷静。按照现在郑氏的实力,完全可以直接将真腊纳入版图。但后果便是要直接面对明国和暹罗。明国和暹罗也会认真对待这个威胁。保留真腊的名义,并且派驻的兵力不足以令明国和暹罗如芒刺在背,就象保留着占城国这个缓冲一样,北郑并不想引起明国的太大注意,更无意与明国刀兵相见。
恭顺奉上。隐忍待机?朱永兴判断北郑采取的是历史上大多数明朝的藩属国一样的策略。明国强盛时都乖得象孙子,以恭谨换取好处;一旦明国衰弱,便小动作不断,甚至有野心大爆发者。
但朱永兴仔细思索,又综合其他情报,觉得又不完全是这样。北郑与荷兰人早就有交往,第三次南征时使用了荷兰的火炮,并且有荷兰的战舰助阵,近阶段似乎更加密切了。显然,在隐忍恭顺的背后,北郑似乎还有借助西夷壮大自己的迹象。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南北恶斗中,北郑动员兵力最高达十万,而地广人稀的南阮常备兵力则只有两万人左右。但南阮大量购买西夷火器,并引进了葡萄牙的铸炮作坊。依靠着火器之利,南阮如果不是被明军和法国削弱,按照原来的历史,北郑应该不会轻易取得胜利的。
相信在南北战争中,北郑也意识到了火器的厉害,现在寻求与西夷的进一步交往与合作,要针对的目标也很明显,正是日渐强大且充满扩张**的明国。
虽然北郑的综合实力无法与明国相比,但却是明国在中南半岛扩张的唯一阻碍了。按照朱永兴的思维模式,北郑已经被列为首要攻打的对象。
其实,令朱永兴感到振奋的不仅仅是海外领地的扩张,而是钱粮的收获。不管国家是强是弱,不管民众是富是贫,在封建社会里,绝大多数的国王和王室都是富有的。流亡的南阮王室如此,被明军控制的水真腊也是如此。宗守义搜刮到的粮食和钱财,可算是解了朱永兴的燃眉之急。
虽然朱永兴殚精竭虑地想出了很多办法来解决财政问题,但却需要一段时间方能见效,而这笔意外钱粮的获取,无疑将使朝廷能挺过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按照比较传统的话来说,宗守义可谓是“深得朕心”。按照朱永兴的思维,需要的时候便会有,这不是运气又是什么?
“北地的百姓应该能熬过这个冬天了。”朱永兴慨然叹息,提笔在拔付赈济的文件上签字盖章。
财政缺口便是在如何安置北地百姓上,哪怕是至少不饿死、少冻死,也是朝廷的绝大善举。至于军需,户部已经计算过,是能够支撑到明年开春的。而随着各项举措的推行,见效前的困难期也就算是撑过去了。
宗守义不错,很不错。朱永兴已经是亿兆之君,按照封建传统,他富有四海,钱财对他来说已经算不上什么,但看着缴获清单,他依然在心中加重了宗守义的份量,给宗守义留的次辅位置也牢固起来。
…………
第八十章京师大乱
寒风在田野里一无阻挡地呼啸着,天空是灰色的,呈现着一种混沌沌的气象。太阳也好象成了穷人,吝啬地把光和热收敛起来。
就在这万物萧条,本应该是人迹罕见的时候,由北京通向北方的道路上却是喧嚣异常。无穷无尽的大小车辆,车上乱堆着家用的东西,在冰霜覆盖的硬地上咯吱咯吱地前进,扔在路旁的枕头、破布、马桶、扫帚、耙子等杂物随处可见;鸡在笼子里叫着,牛羊系成一串在后面走着,找不到主人的狗在乱钻乱叫着……
自从退回辽东的决议在朝堂上被通过,北去的路上便热闹起来,即便心中再留恋这繁华之地,即便万般不想回到那苦寒之地,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满人从王公贵族,到普通包衣,都无奈地收拾东西黯然踏上归北之路。
起初的时候,撤退还是不急不缓的,在很多满人看来,形势并未到了特别危急的时候,说不定能在京师过完年再走。而先走的满人,则贪婪地要把落到手边的一切东西都带走。侥幸心理,再加上所携的东西太多,准备的时间太长,导致了撤退行动的缓慢。
这种举族撤退,不同于军队的入寇劫掠,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拖沓延宕,比逃难还要慢上许多。
清廷做出了撤退的决定,却不想如同逃难般凄惶,他们还努力筹划着,希望能来一次有序的转进,尽量多地劫掠物资和人口退回辽东。但想达到这个目的,却是非常困难的。
明军集团的压力丝毫不放松,这使得河间防线的军队难以调动。为防万一,清廷又不得不把京师的禁旅八旗大部派出,一部驻通州。作为河间防线的双保险;一部分别驻于蓟门、遵化、山海关等地,以确保北退的通路。
这样一来,除去先前增援盛京的一部清军外,清廷能够调动的兵力已经所剩无几。无奈之下,只得再次命令各王公贵族把家丁奴才都抽出来,拼凑出了三千多杂牌军。开始组织大规模的运送物资行动。
时近隆冬,清廷也同样产生了侥幸心理,认为明军可能因为气候和水土的关系,发起进攻的可能性变小了。这样的话,兴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什么变数也说不定。
追根究底,满清对放弃关内、退回关外还是不甘心的,当初冷静的决定虽然获得通过,却无法改变心底的不舍和贪婪。从王公贵族。到普通包衣,都是这样的心理。
所以,形势的突然变化一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