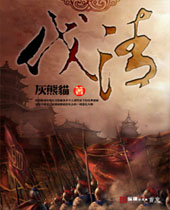逆流伐清-第30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从以上所述,人们不难读出其对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的切齿之恨。清初的“薙发令”以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暴政,更是激起了江南士民的强烈反抗。
而有明一代,明孝陵一直是祖宗根本之地,备受尊崇。每岁有固定三大祭、五小祭。凡遇国之大事。均需遣勋戚大臣祭告。对于清初那批数量庞大的明代遗民来说,明孝陵确实有着异乎寻常的象征意义。对孝陵的拜祭,其实就代表了对故国的追思。所以,自然会有那么的人前去“哭陵”。所谓“孤忠遗老,于社稷沦胥之后。既倮然亡奈何矣。独往往歌哭陵上,摅其志士之悲。”
“薄海哀思结,遗臣涕泪稠”,遗民谒陵时心境之悲凉,是后人难以真正体会的。“孤臣二十余年泪,忍到今秋洒孝陵”,孝陵已经成为那一代人寄托哀思和发泄情感的场所,也是已经灭亡的大明王朝的最后象征。
鲁王朱以海前来谒陵,为了避嫌,自然不会大张旗鼓,只是张煌言等数人相陪,到陵前大哭了一场。
若是从辈份来讲,朱以海是崇祯和永历的叔辈,朱永兴排字为雍,与燕府系的“由”字是一辈,要称永历为皇兄,称朱以海为皇叔。
虽然叫得有些别扭,朱永兴还是口称“皇叔”,安慰了哭陵回来的朱以海一番。
“召见可还顺利?”朱以海暂时收拾起还有些激荡的心情,开口询问道:“这些士绅啊,非是临危受命之辈,却擅锦上添花。”
“表面上却还恭顺。”朱永兴淡淡一笑,说道:“暗地里呢,我觉得做手脚的可能性很大。这些人哪,总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北伐之前还是不要过于触动他们,以免引起动乱为好。”朱以海委婉地劝道:“江南不比滇黔等地,士风最浓,缙绅势力最大,可缓而图之。”
朱永兴沉吟了一下,说道:“皇叔高估他们了。目前他们受满清盘剥榨取,势力正弱,且尚未渗透官场,即便是商业,也须从头开始。若是等他们坐大,盘根错节倒是更不好处置。”
朱以海轻轻点了点头,感慨道:“你有仁厚之心,亦有雷霆之威,他们若轻视小瞧,亦是咎由自取。嗯,且让闲杂人等退下,我与你有要事相商。”
朱永兴愣了一下,挥退了闲杂人等,而机要室的两位官员,还有张煌言,以及两名亲卫,却不属闲杂。
“圣子神孙,总为祖宗疆土。且汝当人心涣散之日,鸠集为劳,屡次临阵,出生入死,今光复神京,已是中兴一半根脚。”朱以海说出的话可谓震撼,但面色却颇平静,“有功者王,定论不磨。功之所在,谁当与争?”
朱永兴审视着朱以海,揣摸判断着他这番话的真诚程度。
“圣上巡狩,于缅甸形同囚禁,既不能召号中外,又于中兴并无尺寸之功,倒要使朝廷受制于蛮夷。”朱以海继续说道:“国不可一日无君,汝之才能胜今上百倍,可效英宗旧事,早正大号,已是有名。”
朱永兴早有计划。却没想到鲁王朱以海是首先劝进者,他沉吟了一下,说道:“国当大变,凡为高皇帝子孙,皆当同心戮力,共图兴复。吾原无利天下之意。且大敌犹在,而同姓先争,岂能成中兴之业?”
张煌言心中暗自叹息,作为鲁王朱以海的忠诚属下,他已经答应了朱以海,劝进,然后便可使朱以海布衣角巾,萧然物外,做个安生闲王。
“殿下。”张煌言拱手说道:“世治先嫡长。世乱先有功。殿下光复半壁河山,且欲提兵北伐,英明神武,可南拜正朔。若仍奉巡狩逃亡之天子,则军民之心难安,中兴又期何日?”
张煌言对永历是没有什么感情的,这番说辞一半是因为鲁王朱以海执意,一半也确实发自肺腑。朱永兴的一番作为。屡立奇功,确实已经凝聚了众多人中兴的愿望。而且。当着鲁王的面儿劝进,也是鲁王为他所做的铺垫。鲁王既要做个闲散王爷,便希望自己的旧人能有个好前程,如此表示,也算是解除张煌言身上鲁王系的烙印。
朱永兴知道张煌言的为人和品格,话既从他嘴里说出。可见并不是作伪。但现在他还得做出姿态,便笑着摇头道:“兹事体大,不可不慎。感谢皇叔,感谢张尚书,此事且放放。先图中兴为要。”
鲁王朱以海没有再继续劝说,他的态度已经表明,如何操作,便是朱永兴的事情了。劝进,那也是有规矩,有程序的,哪能一说便厚着脸皮答应。
历史上篡位之君每假“禅让”﹑“受禅”之名夺取政权。当让国“诏书”下达后,又故作逊让,使朝臣再三上表,劝其登基,然后即位。比如曹丕代汉。亦有外族入侵﹑皇统中断,大臣上表宗室劝其即位以继承皇统者。土木堡之变后,景帝登基,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便是一例。
鲁王朱以海等人走后,朱永兴沉思良久,对机要室主任查如龙问道:“诸事可安排妥当?”
“回殿下,俱已完备。”查如龙有点小兴奋,拥立之功啊,自己也算是开国功臣了。
“那便等各地的回信吧!”朱永兴如释重负地一笑,自己用奋斗积聚了人望,建立了功绩,收拢了文臣武将,终于到了百尺竿头再进一步的时候了。
而登基即位不仅是朱永兴个人事情,更能让手下的文官武将放下心来,不必顾虑永历哪一天回来,又会是新人换旧人的戏码。甚至平民百姓也会很安心,不会对现行的惠民政策有朝一日会因为永历回来加以废止而忧虑。
巡狩缅甸,永历已失中外之望。朱永兴则以努力奋斗打下了根基,到现在虽然还要弄出个名义,可也算是水到渠成,比较容易的事情了。
…………。
重庆。
匡国公皮熊已前往南京,水师一部溯江而至,成立重庆水师,暂归镇朔军调遣。在重庆周边地区的军屯开垦已经着手准备,很多湖广降兵被运来填充四川,重庆官员都予以妥善安置,以后他们的家眷也会被接来,从此成为扎根蜀地的四川人。
如果明军现在渡江北进,保宁被攻克的希望很大。但参谋总部和朱永兴都觉得此时攻取并不是最佳选择,蜀王刘文秀兵败保宁的教训还在,便是因为急于进取,厚重不足。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清军已被堵扼于保宁一隅之地,能守住保宁即已自庆,没有发动反攻的可能。明军暂缓直攻保宁,而在加强对该城清军戒备的同时,采取有力措施经营四川,设官安民,招集流亡,联络土司,加紧屯田,储备物资,并连通与成都的陆路联络,便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就军事而言,收复重庆之后镇朔军同讨朔军、伐朔军已经联成一片,可以动用的兵力大大增加,在适当时机协同作战,不仅收复保宁易如翻掌,继续北上陕西汉中亦是前景乐观。
说到底,这种稳妥的布置还是局限于粮草物资,对此李定国是清楚明白的。整个战场是一局棋,对四川的物资供应已经非常优厚了,他也不好再要求太多。只要一年,只要一年,重庆周边的屯垦,再加上成都的支援,镇朔军便会具有北上攻掠陕西的战略进攻能力,而不是只能攻取保宁。
就在李定国踌躇满志,期望着金戈铁马、纵横甘陕的时候,朱永兴的秘使已经来到了重庆,所携的密信立时令李定国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吾欲称帝,汝看如何?信中的意思很明确,措辞风格很象后世的竞选演说,自信而不狂妄,有实力却不盛气凌人。总之,就是说明“我能行”,“我比永历强”,“我会兴复华夏”,“我会让大家有好的前途和未来”……
第二百七十六章劝进风潮
朱永兴算是直言不讳了,连如何策划都坦承相告,这既表明了信任,又让李定国对永历的将来能够安心。
“遥奉今上为太上皇,以殿下的仁厚和自信,今上应不会有被锁南宫之事。”心腹幕僚高应雷虽没给出直接建议,但倾向性还是很强的。
景泰帝登基,第二年接回被瓦刺俘虏的英宗,并从此将英宗锁在南宫,整整七年。七年里,景泰帝不但将南宫大门上锁灌铅,甚至加派锦衣卫严密看管,连食物都只能通过小洞递入。
有时候,吃穿不足,导致太上皇的原配钱皇后不得不自己做些女红,托人带出去变卖,以补家用。为免有人联络被软禁的太上皇,景泰帝甚至把南宫附近的树木砍伐殆尽,让人无法藏匿。
景泰帝重用大臣于谦等人,治理国政,颇为有序,但他软禁兄长,甚至于景泰三年执意废掉皇太子朱见浚,换上自己的儿子朱见济,这种种作为,颇让后人诟病。
高应雷的意思很明显,朱永兴比景泰帝更强势,为人也更自信,凭永历的懦弱,他自不必担心其复辟,也就不会象景泰帝那样严加防范,甚至到了严苛的程度。
晋王李定国其实早就知道有这一天,大厦将倾时岷世子出缅入滇,收拾人心,聚拢残军,亲临战阵,屡番血战,才挽救了危局;其后更是纵横捭阖,伐安南,结暹罗,联英法等西夷,使大局逐渐扭转;今时更是宗室亲征,慑服吴三桂,一举光复了大江以南。攻克神京,立下不世奇功。凭功绩,凭英明神武,取永历而代之不可谓不是名望所至、大势所趋。
但永历对他的重恩,又使他不能轻易说出支持岷藩的话,以免有人物议。说他是忘恩负义,趋炎附势之辈。
高应雷看出了李定国的犹豫和忧虑,他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现在的形势看得更清晰、全面。
军队呢,不说将领们都加官晋爵,便说士兵,粮饷不缺,且死有恤,残有养。退役还有功田养家糊口;百姓呢,光复区生活安定,日子也在不断好转。国战虽然在打,可朱永兴并不过分盘剥百姓,且经常施恩,虽说很多是要在日后兑现,但对老百姓总是个盼头。
武将归心投效,文官也拥护朱永兴。从龙之功,拥立之功。谁不期待?等到朱永兴登基,讲武堂、书院出身的武将文臣岂不都成了天子门生?
也就是说,晋王李定国同不同意并没有多大关系,岷殿下只不过表示尊重之意。退一万步讲,晋王李定国真要武力相抗,别说庆阳王刘震、昌国公高文贵等将领不会同意。便是普通士兵,谁又肯为了那个远在缅甸的皇上丢弃光明的前程,而进行无谓的战斗。
再者,朱永兴也算是含蓄和厚道了。凭他现在的实力,便是直斥永历无德、无能。甚至无道,要取而代之,又能有多少反对的声音,多大的反对力量?
“大王,此种结果亦算是很好了。”高应雷苦笑了一下,说道:“岷藩即位,今上于缅人便如英宗在瓦刺人手中一样,既无法奇货可居,多半会礼送归国,以免激怒岷藩。如今半壁江山已光复,我军挟大胜之势,岂是缅人可敲诈,可抵挡的?大王就算不直言劝进,亦可委婉表示赞同之意。如此,岷藩即可安心即位,今上亦得安乐,大明得一中兴英主,军民百姓得一宽厚明君。为国,为民,大王一片赤心,又何必在意那些人言物议?”
“岷藩的才干和能力,吾是十分赞赏钦佩,且自愧不如的。”李定国脸色有些舒缓,苦笑着叹了口气,“按理说,他确实有这个资格和实力,但——”沉吟了半晌,他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大势所趋啊,岷藩不是靠阴谋诡计,不是靠虚言诈取,他若能登大宝,确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罢了,早知有今日,却还矫情什么?便按你说的意思,给殿下回信吧!”
………………
孝陵被用作正统地位转换的象征,早在明初即已有之,只不过那时还只是朱家内部轮换而已。建文四年六月,燕王朱棣攻陷南京,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诸王群臣纷纷上表劝进,朱棣在象征性的推辞两次后,于己巳日,“谒孝陵”,虽然“唏嘘感慕,悲不能止”。但当礼毕后,百官再次“备法驾,奉宝玺”劝进时,朱棣没有再做过多推辞,最终登上皇位。
劝进与推辞,与其说是事不过三,不如说是形式上所必需的登极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这其中祭拜孝陵,昭示自身的正统性,就是不可或缺的最后一环。所以,在后人撰修的《明史》中,对此事的记载相当简洁:“己巳谒孝陵,遂自立为皇帝。”由此可见,明孝陵在政权交替之际的重要性。
崇祯十七年三月,崇祯帝自缢景山。于是,在南京拥立新帝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一时间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涝以及周王、桂王均有即位的可能,各方势力纷纷登场。直至五月初一福王朱由崧祭拜孝陵,才最终平息了这场明争暗斗。祭陵后的第三天,福王监国,半月后正式登极。孝陵在这场即位之争中,再次成为了正统地位的象征。
原定三月初一祭拜孝陵,但朱永兴突然身体不适,将日期推迟至三月十五。时间向后延了,但各项准备工作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