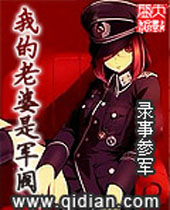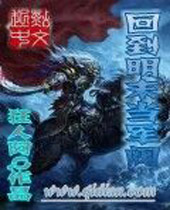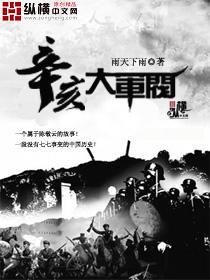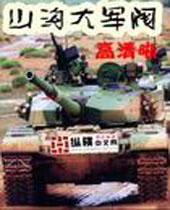爱国军阀-第8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税收,把持乡政,走私贩毒,同时交接官府,把持地方
罗裕民建始1896开中药铺,小有土地略识文字经商,办硫磺厂汉流大爷,县自卫大队长、县参议员、县党部执委各级民意机关。
王献谷恩施1893父、叔父均为前清廪生,县商会会长私塾经商、返运鸦片汉流首领、县商团副团长、商会主席等父辈为清末民初地方最大权绅,本人贩卖鸦片致富,先攀附军阀,后加入国民党。权势年限为20-40年代
傅卫凤恩施农民家庭小学毕业团丁出身团防队队长、团总、三县边防联防总指挥、辖区百里、为恩施“团阀”之一拥枪割据,在其势力范围内独断专行,但也为地方办过一些有益的事,如兴办学校、创办邮政等,权势年限为1925-1942年
冉作霖利川1890父为清末拔贡,公正士绅地主兼商人,承包税收团总、民团大队长、自卫大队长、是利川有名的“团阀”在利川称霸一方,其权势年限为1917-1941年
陈铸九巴东1894家境寒微略识文字,学过道士,当过苦力保董、区联防团首领、保卫团中队长、区长、县参议会副议长,为巴东“团阀”中首屈一霸用钱贿买保董职务起家,其后参与剿共而步步高升,权势年限为1923-1948年
谭孔耀巴东1886土财主不习文墨地主区保卫团团总、区联防团大队长、巴东“团阀”之一独霸一方,鱼肉百姓,于1936年被国民党军委会武汉行辕处决,其权势年限为1920-1930年
向卓安来凤1890祖辈务农目不识丁作土匪起家拥枪自雄,是来凤有名的“团阀”1933年一度被国民党湖北省政府通缉拿办,后以剿共有功,接受收编,被委为来凤县壮丁总队附,1940年被湖北省政府处决,其权势年限为1920-1940年
杨芝香咸丰1884家境清贫私塾设蒙馆教书,后办团练,御匪保民出任咸东联防主任、县长等职基本上属于地方自治型的“团阀”
侯唯一宣恩1891家境贫寒私塾跑江湖、玩汉流汉流大爷、县常备中队长地方小“团阀”,其权势年限为1923-1940年
资料来源:根据《鄂西文史资料》1987年第5期所载资料整理而成
上表所列民国时期鄂西7县12位地方权势人物,其出生年代为1884-1907年间,而其权势年代均在民国时期。12人中,父辈有功名者4人,无功名者8人,而本人均无协名。12人的教育程度,中学、小学及教会学校毕业者各1人,私塾4人,略识文字者2人,不应1人。很显然,这12人所赖以掌握地主社会支配权力的资源基础均非超人的教育和学识。
分析12人的发迹凭藉和途径,虽然具体的表现各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均靠的是有两种:军事的--武力;经济的--财力。12人中,靠武力发迹与靠财力发迹者,几乎相当。靠武力发迹者,大多出身家境清寒的平民家庭,其中不少是好勇斗狠的无赖、土棍,只有一人出身士绅家庭;靠财力发迹者,则是地主商人出身。
就时期而分,民国前期,亦即北洋军阀时期发迹者,其凭藉主要是武力,其权势资源为团练、帮会(汉流)。他们拥枪自雄,独霸一方,实际上是一地的“土皇帝”,时人称之为“团阀”,其势力范围,大者为一县或数县,小者为一区或数乡。“凡拥有枪枝数百杆者,即自称司令;仅募徒手数十人者,亦称官长,是以所谓司令者,到处皆是,彼此各据一方。凡地方财政赋税收入,截不解省。”他们之中虽然也有少数作过一些保护地方和对地方有利的公益事业,但大多数以掠夺和鱼肉百姓为生,在其势力范围内生杀予夺,独断专行,叱咤一方,劣迹累累。在清末以前,民团领袖60%以上为有正途功名的士绅,民国时期转移到由地痞恶霸组成的“团阀”之手。这个时期,随着地方社会军事化的进程,“团阀”们凭藉强大的武力资源,重新塑造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形成民国前期省一级军阀割据,县一级“团阀”割据的格局。“团阀”与军阀并无质的区分,悉视其军事实力而定。只要控扼部分军事资源,即可称霸一乡一区一县,成为叱咤一方的权势人物。这几乎成为当时边缘社会成员积累财源权势和谋求晋升之阶的捷径。影响所及,社会风尚和坐标观念亦为之丕变。民国年间,河南各地普遍流传着“要当官,去拉杆”的俗谚,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不为匪者,则“妻室恨其懦”,愿为匪者,则“父老其能”的怪象。这种怪象不独河南一省为然,当时全国各地由土匪首领摇身转化为地方“精英”者比比皆是。前表内所举来凤县‘团阀’向卓安即为作匪起家。事实上,民国时期,防御性的民团与掠夺性的盗匪团伙已互相渗透,地方当局剿匪不成,乃转而采取“以匪治匪”的办法,对一些拥有较强武力的股匪采取招抚政策,给以地方保安团队的名义授其匪首以官职。民团领袖的社会构成亦因之而改变。
在鄂西各县,当南京国民政府势力深入以后,“团阀”们的出路不一,有的见风转舵,主动投靠国民党,跻身于基层政权与省县参议员行列,继续拥有其权势资源;有的负隅顽抗,不服国家政令,企图继续割据称雄,其结果,多被国民党政府以“土豪劣绅”的罪名镇压或摄服。
从前表所举例证可以看出,民国后期,亦即国民党统治时期发迹者,其凭藉主要是财力,其权势资源多为参与地方自治、教育、商务、党团及民意机关和团体的活动。他们在地方颇具势力,并以地方民意代表自居,上焉者把持县政,挟制县长,下焉者垄断乡曲,把持乡政,并在地方买田置地,承包税收,富甲一方。他们与民国前期的“团阀‘有所不同的是,“团阀”完全以我行我素的“土皇帝”自居,抗拒国家权力的制约和渗透;而他们则大多希望在政治上寻求出路。由于他们的行为方式在某些方面承续了清末以前的绅士角色,故他们虽然不再拥有传统功名,而时人仍以“绅士”相指称。
但是,与清末以前的传统文人绅士相比,民国时期的“新绅士”在才德和威望方面均令人有今非昔比之感。他们所赖以支配基层社会的资源基础是强制性的武力和财力,而不是传统士绅所具有的对乡土社会的内在道义性权威、外在法理性权威和个人魅力权威。上述鄂西12位权势人物中,有的虽也在“保境安民”的口号下,抵御过外来匪患,或抵制过军阀官僚的苛索,或为地方做过一些修桥补路、兴校办学之类的公益事业,但与其劣迹恶行相比,前者多为后者所淹没。少数公正士绅反被这些有劣迹的“土豪劣绅”从地方自治领域排斥出去。“土豪劣绅”遂成为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的主要支配者。。。。
民国农村权力结构
五、国家政权的下沉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任何类型的组织建设,都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必须有一定的组织成本;二是必须有相应的组织队伍。在清代以前,中国社会具有一种独特的组织结构:一是正式领薪的官僚人数极少,据统计,19世纪末期,清朝中央政府官员2622人,地方官13007人,武官7464人,共计约23000人,而当时全国人口已突破4亿,平均每名正式官员需治理17000余人。如以地方行政官员而论,这一比例则更悬殊。有人指出,18世纪末,中国每一知县统治人数为30万人,而革命前的法国,每一地方行政官员统治的人口是3000人。二是非正式的吏役群体数量庞大。清代除中央和省道级衙门的吏员不计外,仅县级衙门,就有“千县30万吏”之说。三是县以下乡绅自治。据张仲礼研究,19世纪中国乡绅总数逾百万。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由数万名官员,数十万名吏役和百万乡绅组成的上中下有机衔接的整合体。这样一种独特的组织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成功地维系了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社会的整合。
与传统社会相比,国民党时期的官僚组织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为了应付“内忧外患‘的大变局,国民党既不能象传统王朝那样“无为而治”,而传统文人士绅的衰亡,县以下的乡村自治网已经破裂,在这种情势下,国民党如要实现社会各层次的整合和控制,唯有建立一个从中央直统到基层的金字塔式的巨型官僚机构。与历代王朝相比,国民党的确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据1948年统计,国民党中央和省级公务员共计余人,另有公役、技工、警兵人(见下表)。这个时期县级公务员的实际人数有多少,未见综合统计。以1939年推行“新县制”以后的县政府员额编制来推算,一个县政府直属机关公务员大约100人,附属机关公务员也大约100人,全国县级公务员总数当在60万人左右。若将中央、省、县公务员三者总计,则超过115万人,相当于清代文官总数的74倍有余。
表6-11948年国民党中央和省市级机关公务员人数统计
公务员公役技士、警兵合计
中央机关31113812388797831532856
省市机关246565103974371988722527
总计5577032278614698191255383
资料来源:(1)“中央机关实有员役人数”;(2)“各省市政府实有员役人数及其分析”,均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号6-4930。
但是,115万公务员尚只填充了国民党整个官僚机构的上层部分。随着国民党政权由县而区,由区而乡,层层向下深入时,其公务员人数以几何级数增长。在1939年“新县制”实施以前,县以下的正式官僚机构只到区一级,县区两级机构规模尚小,人员编制尚有限。自“新县制”推行后,官僚机构延伸到乡保,县以下基层公务员人数倍增。据1942年的粗略估计,区一级干部约需164612人,乡镇一级干部约需686721人,保甲干部约需12140908人,共计需要12992241人。
如此庞大的基层社会组织群体,其数量已是清代乡绅的十余倍。任何社会组织都必须有相应的经济系统为其提供物质资源。在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只需一定的农业税收即可供养数万名官员,而国民党时期,省以下政权的财政收入仍主要建立在传统农业税收的基础上,而同时期中国农业经济仍处于19世纪以前的发展水平。国家政权的财政需求剧增,显然与传统农业经济的承负能力不相适应。以湖北为例,据1942年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称,仅湖北一省实行“新县制”就需要52万干部,若每人每月薪俸十元,全省每年就要6000多万;若每人每月薪俸50元,全省每年就需要3亿元。而1942年湖北省的年财政收入仅1200万元,支付一省行政人员的薪俸尚不敷远甚。就全国而论,据当时的估计,近千万基层干部每月以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计,就需要40亿元。国民党政权在深入基层社会的过程中,面临着巨额的财政负担。据1946年底的统计,国民党中央的财政支出超过其收入的5倍。中央政府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一方面滥发纸币,同时对地方各级政府的经费预算大力削减,甚至停发。基层行政人员薪饷微薄,有的完全没有薪饷。政府实际上默许这些基层行政人员在与农民打交道中浮收摊派以维生。这等于政府每年从广大农民手中获取数以百亿的行政“暗税”。
除了组织成本外,国民党政权的深入,还必须有一支健全的组织队伍。蒋介石也一再强调,要行“新县制”,首在得人。国民党实行“新县制”需要上千万基层干部。人才从何而来?作为一个现代动员型政党,国民党本可大量从基层社会中吸收党员,然后通过其意识形态的严格薰陶和组织训练,将党员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基层干部。但国民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比其基层政权建设还远为滞后。战前国民党党员不仅人数有限,而且集中在城市和上层,农村党员如凤毛麟角。战时国民党党员人数虽有所增加,党的组织也向基层社会有所深入,但总体而言,基层党组织仍不过是基层政权的附庸和寄生体。党不是培养和派遣合格的党员去充当基层干部,而是不加甄别地将所有现职基层保甲长披上党员的外衣。其结果,不是将合格的党员转化为基层干部,而是将不合格的基层干部转化为党员。
国民党基层组织建设的另一条途径,是指望让“公正士绅”和新知识分子接受党的意识形态训练后转化为基层干部。但是,这个时期,中国县以下基层社会与19世纪以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前所述,自科举制度废除后,传统文人士绅逐渐衰亡,新知识分子城市化,乡村成了穷光蛋、地痞流氓和土豪劣绅的渊薮。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象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