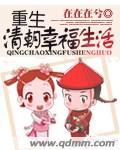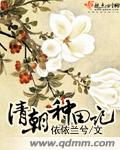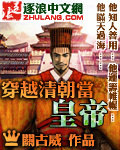细说清朝-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领托合齐等几个获罪的贪官潛通消息。(明珠在康熙四十七年已死,与太子此次被废的事并无关系。)
康熙叫胤礽仍旧住在咸安宫,但不许出去(禁锢),也不许与人往来。康熙说,“胤礽仪表、学问、才技俱有可观,而行为乖谬,不仁不孝,非狂易而何?”这分明是说胤礽已经成了疯子,但是康熙又接着说他不是得了神经病,而是交了坏朋友:“凡人幼时犹可教训,及长而诱于党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矣。”
三年以后,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胤礽不耐烦被“拘制”的生活,用矾水写隐形文字,托一个医生带出去,和那位被他打过的普奇通信。似乎是叫普奇运动朝中大臣,举他自己为大将军。结果,普奇又吃苦头。
过了三年(康熙五十七年),康熙任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驻扎(青海的)西宁,升四川巡抚年羹尧为四川总督,驻扎成都,以对付派兵侵入西藏的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
胤禵的行情,一天一天地涨,胤礽的行情,便一天一天地落下去。然而朝中仍有若干大臣,对胤礽不忘情,想劝康熙回心转意,三度立胤礽为太子。
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的时候,大学上王棪和陈嘉猷等八个御史,先后上书,请康熙早立一个太子,不敢提起胤礽的名字。他们的奏章,被康熙搁起,不予批答。
次年,翰林院检讨(“检讨”比编修低一级)朱天保鼓了勇气,说出胤礽的名字,请康熙考虑。康熙把朱天保杀掉,也杀掉与他同谋的副都统戴保。男三个同谋:朱天保的父亲(侍郎朱都讷),与副都统常赉、内阁学士金宝,枷首示众。还有一个同谋,“都统衔”齐世,交宗人府幽禁。
康熙六十年(1721年)三月,在万寿节(康熙生日)的一天,那位碰过软钉子的大学士王棪,又拼了老命,约同御史陶彝等十二人,请皇上立一个太子。康熙很生气,罚王棪与陶彝充军。王棪年纪大了,不能去;康熙叫他的一个儿子代去。
胤礽就这样永久被禁锢在咸安宫。
康熙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去世,继位的不是胤礽,也不是胤禩,而爆出了一个冷门:皇四子胤禛。
胤禛自己说,康熙在临终之时当面指定他继承帝位。别人说,康熙留下了一个条子,交给国舅隆科多,条子上面写的是“传位十四子”,这隆科多与胤禛勾结,把“十”字改成“于”字,变成了“传位于四子”。
胤禛即位以后,不释放胤礽,而封胤礽的儿子弘哲为“多罗”理郡王。他重用皇八子胤禩,封他为和硕廉亲王,叫他与皇十三子胤祥(封为和硕怡亲王)及大学士马齐,共同“总理事务”。
《细说清朝》四八、贤士在野
康熙在血统上,一半是满人,一半是汉人(母亲姓佟);在文化上,他只是一小半为满人,而一大半为汉人。四书他完全念过,五经与二十一史他也约略有所涉猎。朱熹及其弟子所撰的通鉴纲目,他批阅得相当仔细。朱熹的哲学,是他生平所最佩服的。
他颇以振兴朱学为己任,叫左右编印了朱子全书、性理大全;又在康熙五十一年下旨,把朱子的牌位放进孔庙,配祀孔子。从此全中国想做官的人,都把精力花在朱子的书上,套用朱子的话与朱子的思想,写他们的八股文。
真正而纯粹的朱学,在清朝反而几乎成为绝响。太子胤礽的两个辅佐詹事汤斌与少詹事耿介,是讲学于辉县夏峰的孙奇逢的弟子,孙奇逢算得上是一个儒者,但无所偏袒于朱熹与陆九渊之间。曾国藩与罗泽南、倭仁、李棠阶等少数人,在修养的功夫上,很得力于朱学;除了曾国藩等人以外,便根难找到实践朱子的教训的人了。
明朝几百年的学风,以王守仁(阳明先生)的一派为主流。王的思想与陆九渊相近,而创见甚多。王门的殿军刘宗周(戢山先生),生平着力子“慎独”二字。他是浙江绍兴人,万所二十九年的进士,在明熹宗朝中以刑部主事(科员)的地位,弹劾过魏忠贤与熹宗的乳母客氏;后来,在庄烈帝(崇祯)朝中,他又以工部左侍郎的地位,反对误国的大学士温体仁;庄烈帝革了他的职,不久又任命他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他主张杀另一个误国的大学士杨嗣昌,又主张释放姜埰与熊开元两个“言官”,被庄烈帝再度革职。福王在南京即位,召他复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他先后弹劾马士英与悍将高杰、刘泽清。等到阮大铖作了兵部侍郎,他看见势无可为,请假出京,住在杭州。杭州入于清兵之手。他绝食二十天而死。
在他的门人之中,以浙江余姚人黄宗羲(梨洲先生)的成就为最大。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也是王阳明一派的硕儒,于明熹宗时当过山东道御史,弹劾魏忠贤三次,其后与杨涟、左光斗一同被害,死在牢里。
黄宗羲在庄烈帝即位以后.到北京为父诉冤,恰好庄烈帝已经把魏忠贤明正典刑,黄宗羲便杀了当年在牢中害死父亲的两个狱卒,也用锥子锥伤崔应元等几个魏忠贤的余党,拔掉崔应元的胡须,拿回余姚,放在祠堂里的父亲牌位之前。
福王在南京即位,黄宗羲至南京有所建议。被阮大铖捉住,与顾杲关在一起。罪名是,他们两人在北京沦陷以前,曾经集合一百四十个书生,写了一个“留都(南京)防乱揭”,宣布阮大铖阿附魏忠贤,出卖“东林”的罪状。所谓“东林”,本是无锡一个讲学的书院,主讲的入是顾杲的父亲顾宪成。阮大铖也在该处听过讲。听讲的人极多,不免议论时政,魏忠贤恨他们,称他们为“东林党”,杀了他们中很多人。
南京被清军拿去以后,顾杲与黄宗羲从监狱里逃出。顾杲回无锡起兵抗清,被不认识他的乡下农民杀了。黄宗羲参加鲁王的阵营,以三千精兵经营海盐一带,又在宁波四明山扎过寨,而且到日本去乞过师。鲁王失败以后,他回余姚养母,著书授徒。
在他所著的书之中,以《明儒学案》与《明夷待访录》为最重要。《明儒学案)是一部明朝的儒家哲学史,其中有简单的传记,与各家语录的摘要。这书的体裁是他新创的。《明夷待访录》是他本人的哲学,包括若干篇论文,以“原君”与“原法”两篇为最精辟。
他是王派巨子刘宗周的学生,但思想超出了伦理部门,兼及于政治。这是由于他史学的造诣特别深。他留下不少关于南明的记载,也整理了整个明朝的史料。他的学生之一万斯同,成为一个大历史家。万斯同以后的全祖望与章学诚,均私淑于黄宗羲。万与全均是鄞县人,章是绍兴人。他们形成了历史学界中所谓浙东学派,而黄是此派的开山祖。
康熙有几次请黄出山,黄均坚辞。康熙只得命令当地的巡抚到黄的家里抄他的书,送进皇宫,以便拜读。黄也很有礼貌,让他的儿子黄百家进史局,帮助徐元文等人纂修明史。
另一位康熙想请去修明史的大学问家,是昆山的顾炎武(亭林先生)。他是明朝的一个秀才,在南京陷清以后,他参加本县县知事杨永言的义师,其后也追随鲁王,作了鲁王的兵部司务。鲁王失败,他遍游全国重要地区,图谋复国,在山东、山西、陕西,均建立下小规模的经济基础,可惜人心已不思明,他便终老于陕西华阴,以著述来开创中华民族的新运。
他留下给我们以《天下郡国利病书》《隐学五书》与《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可说是一部人文地理;《音学五书》是科学的中国音韵学;《日知录》是考据的杰作,
他认为明朝之所以亡,其最大原因为士大夫中了宋儒的毒。朱派、陆派均太注重言心、言性,把政治与经济搁起不谈,不研究。因此,他想纠正风气,大声疾呼,要读书人研究经学,说“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又说,“今之君子…。。。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
他提倡切于民生日用的经世之学,但这一种学问在清朝三百年间并未能发达,原因是文字之狱。不过,若干封疆大吏却留下了《皇朝经世文编》,其中充满了可供我们研究的资料。
他的治学方法,发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他不说空话,每说必有根据,而他所根据的决不是不值得根据的东西。第二,他不抄袭别人的话;即使是他自己所研究出来的,倘若在其后发现前人已经说过,他也即刻删去。第三,他颇能接受别人的意见,从善如流。因此之故,他成了清代“汉学”的开山之祖。
顾炎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比黄宗羲还要高。黄在思想上颇有独到之处,但规模、系统均不如顾。就治学方法而言,黄比顾更逊一筹。
与顾、黄二人同以隐逸自全,终身不事二姓的,还有很多。其中最有名的,除了前述的汤斌、耿介之师孙奇逢以外,有陕西墿厔人李颙(字中孚,号二曲),山西太原人傅山(字青主),与湖南衡阳人王夫之(船山先生)。
李颙注重苦行,曾经徒步到河南襄城,寻求父亲的遗骸。他父亲是一个对张献忠作战而阵亡的兵士。他也应邀到过江南,在无锡、江阴、靖江、宜兴等地讲学。康熙在康熙十七年开了所谓“博学鸿词科”,以网罗在野的“遗才”。有人荐举他,他称病不出。人家把他用病床抬到省城。他绝食,宁死也不肯入京。其后,康熙在康熙四十二年西巡,召见他,他派儿子李慎言去应召,将所著的《四书反身录》与《二曲集》带去,送给康熙。
傅山也是一个苦行的人。明亡以前,他曾经冒死援救一位被魏忠贤党羽(巡按张振孙)所陷害的忠臣袁继咸。南京陷清后,他在顺治十一年被捕,罪名是与河南的某一件案子有关。他抗辩不屈,继以绝食,结果被释放。到了康熙十七年,有人荐他应博学鸿词科,而且把他抬进北京城。他在看见“大清门”三个字的时候滚到地上,两泪直流,于是又被抬回家乡。康熙这时候,已经特免他考试,任命他为“中书舍人”。他回家以后,仍以“民”自称;凡是称他为“舍人”的,他一概不理。他写字、画画、作文都很好;也很懂医道。顾炎武和他颇谈得来。
王夫之是明朝的举人,参加过以永历皇帝为中心的抗清活动,其后隐居在衡阳的石船山,闭门著书,一直到死不肯剃发。在学术思想方面,他反对王守仁(阳明)及其若干支派,也不太赞成朱熹,而远宗北宋的张载。他说:“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就这一点而论,他可算是戴震(东原)的先驱。
他著有《张子正蒙注》《老子衍》《庄子解》。他的更重要的著作是《读通鉴论》与《宋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想见他读书之勤而认真。他的见解。虽则有时不免主观,但大体上均很值得重视。
除了这几个人以外,在言行上自成一家的,有颜元及其弟子李塨。他们把读书看成次要,认为实践才是学问的主体。他们除了躬耕自给以外,又天天射箭、练武。可见他们不仅是隐士而已,而是志在复国的有心人。
常熟有一位顾祖禹,是《大清一统志》的真正著者,而不居其名。他的《读史方舆纪要》,则不仅是历史地理学的一部好书,也是一部兵要地理。他认为山东在全国各省之中形势最为重要,希望后世的“欲有事于天下者”特别注意,言外之音,跃然纸上。
此外,有仅仅留给我们一部《广阳杂记》的刘继庄(字献廷)。他的著作,倘若完全被保存下来,其贡献当不存顾炎武与黄宗羲之下。他对于中外的语言文字,极有研究,也颇深入于数学、火器、农桑、地理、法律、医药等好多种有裨实用的学问。他是大兴(北京)人,祖籍吴江,他本人回到吴江住了几十年。生平行踪诡秘,很像是秘密社会中的人物。徐乾学曾请他帮忙关于《大清一统志》的事,但他十分看不起徐乾学。他所佩服的,只是金圣叹一人。
金圣叹,名人瑞,原姓张,名喟,是长洲(苏州)的一个秀才,批过《水浒传》与《西厢记》。他是一个群众运动家,在顺治年间聚了很多人向清朝政府抗缴钱粮,到孔子庙里哭,被抓去砍头。 当时,苏州有一位举人,姓徐名枋,是大书画家。明亡以后。他不见任何宾客。汤斌来看他,在客厅里坐了许久,他始终躲在书房内,不肯出来。他隐居到七十三岁而死;死前吩咐家里人说,“宋荦必定会送银子助葬,切勿接受。”其后,宋荦果然送了银子来,被徐枋的家里人拒绝。徐枋与汤斌、宋荦并无仇怨,所恨的是这两人作了清朝的官。
魏县(河北大名)有一个举人刘永锡,官居苏州府教谕,于明亡以后隐居在阳澄湖边,和一妻一了一女织席为生。他家中本属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