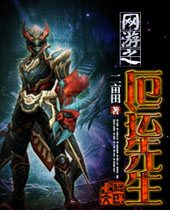��������-��1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Ը����ϵģ���ʦ���м�λ���ǻ������µ��١���������ȥ��Ҫ�϶���һ�������Խ������������һ�����Ҳ���϶��ˣ�����ǿ����˼����Ķ�������û�д��������Ѿ��ӼDz�����ٴεĸ������еó�һ�����ۣ���ϵļ��ֺ�Ӧ�����µļ��ֵõ���ʵ��Ч����һ���ġ�����ϵ������Լ�����˵��û�С�����˼����ӡ�����Ӧ�����µ������Լ�һͨ��������˵��û�С�����˼����İ��ණ�����������Բ������Խ��ˣ���ȻҲ������������˼���ʱ��������ɫ�IJ������ˡ���
��������ˮ�����壬ɨ�أ���ɨ�������洶��Ա��ʦ���ջ���ˣ�ϴ�����롣�����κ���Ҳ������˵����������������һ�仰ʱ���Ҿ�Ȼ�е�һ�����ң��ƺ��ҵ�����Ҳ����ˡ��ö���֮������ȫ�����ˡ����ɡ��ļȳ���ʵ���Լ�Ҳû��һ˿���İ��Լ����˿��ˡ���ȥ���е�ѧ������һ�������ɡ�������������һ�£������Ѿ����IJ����ˣ�����Ī������ضԺ��š����ɡ���ѧ��ЦһЦ���ֺ��Ƶ�ЦһЦ����
�������ҽӴ��������Ǵ���Ա��ʦ����������������ú����ϴ�����룬����Ϊ�˱�ʾ����ij���������е��Ķ�����£�ʱ��һ�����������ҵ��ɰ������Ա�ˡ������һ�������ͽ��ң������������ֵ���Ժ���ﺰ���������У��㹷�յ��굽�������ȥ���𣿻���ӝ�֣��������ǣ��������ɣ�ûˮ�֣��㲻��ˮ����ӝȥ���𣿡���һ�������ĺ�������ȥ�ջ𣬾�ȥ��̨�Ͻ�ˮ����Ҳ���գ�Ҳ��˵��������æ�������������������Ķ㵽������͵�У������������������¡�����ӝȥ�ˡ���
������Ҳ�ж��Һõ�ʱ����������������У����������ʱ�ͻ����ʮ�ֳϿң��������ڶ����ķ�����������ǰ��������˵�����ԣ����ײ��ԣ��㲻�ԣ�ָ���������Ǹ�����˵��ĺû������룡����ô��������ظɣ���ָ������������˵�û���ժñ�������룡�Ǹ�����û���˵��ĸΣ����Ĺ��Σ����������Ҳ�������������
��������ʱ������ʮ�ֶ��ӣ�����������������У�������ʱ�ͻ���ҵ����������۾������㹷�յ�һ��ĥĥ���ģ����úø��죬��������˾Ҳ���Ǹ��ù����˼���У��������ͬ��ͬѧ�����˼Ҷ�����ɶλλ�Ͼ��ţ��������ɶ���������ţ�������������Ĵ���ǣ���ҷ�������û��������������ϳ���һ�����ǡ�������
����Ȼ�������������û�ܵ�������������Ҳû�ܵ������ʱ�䣬����һ���������ţ�һ��б���۶���˵�����ҵĻ�����һ��������������̫��į����ʦ��һ�㲻м�ں����й���Ľ�����û�й�ͬ�����ԣ������ǾͰ��ҵ������ĵĶ��������У���˵��ı��ºܴ���֣���д�ܻ��������������Ǹ�ȫ���֣���˵���ܵ����������ѧ������֣���û�¸��ˣ�����ӝȥ���ô��Ҫ���쳤�������������µ��ã����������ʦ��λλ����������������¿����չ�����̺��˼ҡ���������������ܿ����̺�����������
��������ʱ���Գ������������ӣ�������һ�����С�����Ǹ�װģ�������������Ů���������ö������ģ���˵���������ʱ�������ˡ���һ��ˣ���˵ʵ�������������û�У����ǣ��������ۣ�ֻҪ����һ���̣�����Ҳֵ�ˣ�����
������Ҫ�Dz������ܶ������ߵ������ͻ��У�������¿�յ��������굽�Ĵ�ȥ�ˣ������������֣�������̡�������
���������Բ�˵����������������Ҷ�Ȩ���ǹ���ƨ�������ӻ�ģ���������У����ǰ���ҵĽҷ�����У������ͨ�����˽��ҵ����С����ӿڳ����Ҽ��������ǧ�����ԡ�ʱ��һ�����������ܶ������������ҵ�����ɵɵ��ЦЦ���ֺõ�ЦЦ����
�����ҵ����ӵı仯������Ϸ���ԡ���
��������������ٳ������ɣ���û�лؼ�ȥ�������¼����ף��¼������ĸ����ֵܣ������¼��ҵ���������Ҳ�֪����ô�죬���﷼�Ͼ��ˣ��Ҹ�Ը���������������������£��Ҿ������Ѵ����Ĺ�ϵ���������ɣ����������������ѵ�ʱ��ȥ�����պ��Ź��ɣ�����������Լ�̫�¼��ˣ�������ζ��Ҳû���ˡ���
�����������û��ȥ�ˣ�����ѧУ���ţ�������������������У����Ա����Ȼû���ң���������������һ�����ڶ�����ѧУ�ˡ����������ң������ݻ��ը�ɣ����ں����������ص����е�İ���ļ�������塣��
��������������Ž����ǽ���ϣ����ð�ˢд�Ĵ��������������á���������������彭ɽ���������ɽ��������Ҽ����ٲ��Ҷ�������������ͷ�����Լ�����¥����
������̤��Ժ�ӣ�����С�����ž��ž�յķ��������ҵ���������Լ�����Ų��죬��С���̽�����������ң�վֱ�����ӣ��ʣ�������˭������
������װ������ʶ���ˡ���Ҳ��֪����ô�Ը����־��棬�ܿ����Ķ���۹⣬��ֱ�����ߡ���
�������ޣ������������������������ĺö���ѽ�����Ɀ�˱��ۣ����ϲ����ˣ���������ſ��Ĵ����֣��Ĵ���ϥ�ǣ�����С̾��Ų����˵������˵������ˣ����������������ˣ�������ѽ����������¹��ˣ�����
�����ҵ������Ǹ�����һ�ӣ��۵ü�����Ϣ�ˡ����߽��Լ���ס����̱���Ƶص����������ϣ���������ľ�ˡ���
�������ָϽ����������ֲ������վ���ſڣ���Ū��Ʋ�ź����촽��������ôһ���˻����ˣ���İ�ëŮ�أ��Ǹ�Ұ�����أ�����
�������㡭�����ҵ�Ѫһ���ӳ嵽�Զ�������վ��ȭͷ���������ϣ������١�����˵һ�䣡������
������������ǰ�ף���ɶ���£������������£�����ͦͦ�������б�����ѧУ���ȥ������
�������뵽����ѧУ�����裬��Ȼ���ˣ�������������
������������ɣ�Ҳ�����Ҹ����ģ����Ҹ�ǰ��ɶѽ�����������ˣ�����ѹ�����ҳ�ʮ�꣬�������ҳ�ʮ�꣬�ҵ������������ʮ���ˣ����ˣ���������¸������ɣ��ܻ����Ѷ����ˣ�Ҫ�Dz������ɣ��㻹������Ұ�Ѷ���������������
�������ǡ�������˵������Ҳ�ò����������㲻Ը���ˣ�����ı㣡����
��������飡�������˵�������Ҹ�ũ����Ҳ���������˳�û�Ļ��������ܹ��ˣ��롭������
�������ã���Ȼ��飬�ٱ�˵�ˡ�����˵��������ȥ�����������߸��ġ�����
������˭����Ͳ��������ģ����������������Ӳ������ƣ��������ھ�ȥ�糤�Ƕ��������ţ�����
�������߳���ȥ�ˡ���
����������ܾ�����ĸ�ײ�֪��ɶȥ�ˣ�����û�ˣ���һ���������������ʼ��Թ���ף������������������ͷ����в�������ڴˣ��������𣬹�ȥ��������Ķ��ӣ��������ӵؿ��ң�����Ҳû�и���˵��һ���������������ǽ��ҡ������������Ϸ�����Ůһ�����������ط����ҡ����ڣ������һֻ��ĺڶ��ˣ������ų�����Ҫ������飬���ſ����Ž��ﺰ��ȥ�ˣ����룬�����ӣ�������˶�֪�����ǵļҳ��ˡ���
��������ĸ���߽�Ժ�ӣ���ɫ���֣������Һ������̵�ԭ��̾һ����Ҳ����˵˭��˭�ǣ�ֻ��ĸ���������֣�����ȥ��ȥ�������������������ڽֵ����У���ೡ�ϵ��˸�Ϸ̨��һ�������Ƕ������ˡ�������
����ֱ����ڣ�ĸ��Ҳû�ܰ��������������ڷೡ����˵�����Ҫ��飬��֮�ָϵ������μң���һ���Ӻ�һ���ӣ�˵Ҫ�������β��������������ţ����Ͳ��ؼҡ�����
�����������죬������������������μ�Ҫ�������š��ҵĸ����Ǹ�����Ƥ���ˣ��������������ˣ��跹������ĸ��ǰ�����ϱ��˵�û���Ȱ�⣬���ö����ˣ���Ȼ�����¡������˾�̾����ôҲ�벻��������������һգ�۱���߳ܲ��˵�ĸ�ϻ��ˡ���������
�������ֻ�����ҳ��棬ȥ��������˵������˵�˻������Ÿ������˽����š���
�����ڶ���һ�磬��ϴ����ͷ�����ҵ��ط�Ժȥ��飬����������ظ�������·����
�����߽��سǣ��߹�һ�ҷ��ݣ���˵�����������Ҷ��ˣ�����
�����Һ�Ȼ�е����ܣ������������ˡ������ҽ���ʮ���ˣ����ǵ�һ�ν����ݳԷ����Һ�Ȼ�����ҹ�ȥ����̫��������÷������˼���С��������õIJˣ��Ӵ���ȡ�������ŵ������ϡ���������������ѹ�����ȣ����ɵ�ɽ�������ԣ������Ҷ������ֶ����������DZ����Ƶس����ң���������һ���Ұɣ���
����������ȡ����������֧ʹ�ҡ���
�����Ҵ���һ��������ȡ���ε�������������
�����շ����������߳�ȥ�����ں�����š��ߵ��ذٻ���˾��ǰ�����߽�ȥ�ˣ�վ�ڹ�̨ǰ�����ۻ�Ա˵����ȡһ˫��Ь���������Դ�С��Ȼ�����˵������Ǯ��������æ���ۻ�Ա����Ǯ�����ﲻ�ɵ��������������ˣ������Ҹ������������һ�����ָ�����������
�������ߣ�����·���������������������ӣ������ϵ÷�Ժ��·������
�������ߵ���Ժ�ſڣ���ͷһ������������Ӱ�ӣ�����Լ�ǵ�һ�ν��سǣ��ò����ڴ�ʮ���ߴ�·�˰ɣ��һ�æȥ�ң��ܱ����سǵĶ������أ��������Ϲغͱ��أ�û��������Ӱ��������ҵ�����ҵ�����������ֻ�������ߡ��߹�ʮ��ƽ����·��һ��С�ӵ�ʱ��������ͷ�Ͽ��������÷��ϵ�������
�������㡭������վ������ǰ����������˵�����������㡭����ô�����������
������������վ������������������㡣����
�����ҿ���������ɫ���ã�˵��Ҳ�������ˣ�æ�ʣ����㲻��Ҫ�Ҹ��㵽��Ժ�𣿡���
����������Ժ��ɶ������װɵ��������
���������ѽ������˵����
��������飿�ҲŲ����Ǻ�ɵ�£�����˵������Ҫ�������˶�֪������Ҳ����飡�⼸����Ҫ������飬Ů���Ƕ����ۿ��ң�˵���˲�Ҫ���ˡ���ʱ����Ҳ��Ҫ�����ˣ���ʵ�����������ȥ�����������
������һ����̱���ںӱߵĿݲݵ��ϣ����ڴ��Ӵ�д��������μҴ���֣�ԭ����Ϊ��������Ŀ��������Ӱ�����
���������ˣ������ӿ������ᣬһ˦ͷ����̤����ľ���ɵĶ�ľ�š���
�����ҴӸɿݵIJݵ���վ���߹�ȥ��̤��С�š����ղҵ���Ϧ���ĺ�⣬����ɫ�ĺ�ˮ��Ͷ�µ�����Ѫ�졭��
�������������Ŀ�У��������ҳ
ǰҳ
Ŀ¼
��ҳ
ǰҳ
Ŀ¼
�ҵ��Ǽ�С����
����ţ����Сѧ������һ�������£���ǰ��һ��С�ӣ������������Ŵ��СС��ʮ����ׯ�����������ݺ�����ŵļ����������ء�������������һ��һ���ٵ��Ӳ�������ӡ���Щ�洦�ɼ��ĺ�ʯ�Ӷ�����î����һ���ļ�����¶�Ÿ���ĺ�ɫ�����˿������ܡ���ׯ��Χ��Щ���ݵ�������ˮ����ĵط���һ�������ӵĻ��ƣ���������ƶ����µش��ļ��������ɻ��õļ��ڣ��������д�ѩ��������ӣ������Ҳ����ֳ����ụ�õ����ǡ����벻���۵�����ĩ�����һ�����ճ־õĸɺ������µ��ϵIJ�ľ�����ˣ��ɿ��ˣ���ľ��������Ҷ�ӣ����������δ���ӧ�������Ͱε�ιţ�ˡ�����ɽ���ϣ�����ջ��ǹ�һ������ȥʹ�����ܡ���
����ֻ��ѧУ��ǰ�������Ӵ���һ���ļ��ﶼʹ���ܸ��ܵ�����Ȼ��������ζ����ʹ�ڸɺ��˿��ñ����ϵ���ð�����Ľ���ʱ�ڣ��Ӵ���Ҳ������Ȼ����
����һ���������������Ѻ�ˮ�������۵��������ء�������һ�ܼܻ�ţ���������ŵĶ����������ŵĽ��ʽˮ�����������ĵ���ˮ������������ո��Ժ�����ء���
�����ҳ����������ҵ�С����������ºͺӴ��ļ���ɫ����Ȼת������
����ѧУ������������ľ�ṹ�ķ��ᣬ��ľ�ڹ��������Ļ���Χǽ�ϣ�������С��С��ð���������������ɺ��������ȿ�����У���дִ���������������µ�����У��ÿһ�����䣬�������н�ʦ��������Ʒ������塣���ŷ��ᣬ���������֮����Ž�ʦ�����Ҽ�칫�ң���Ϊ����Ƿ�٣��������˻�����һ�ң�һ��һ�Ŵ���һ�Ű칫�����м�ֻ��һ���ߵ����롣�ƺ�û��˭��̫�����������ƣ�ֻ����ˡ�ֻ��У��������һ��һ�ң���Ϊ��һУ֮��������ijЩ���ܵĹ������ε���Ҫ�����Ҳû�����飬Ҳ������˵�����⻯����
����������ں��ŵ�һ�䷿�ӣ���Ϊ��Сѧ���꼶�İ����Σ�������Ϊ�Ŵ�������һ�ҡ����꼶����ʦ�Ϳ�����ʦ��һ�������˾۾ӡ��Դ��ҵ��������ԺͰ�����Ǹ�����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