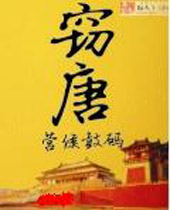Ѫ�ȵ�ʢ��-��93����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ش𣺡��������������������������ڱ��¹��У������DZ��µ����������������𣬲�����ʮ�꣬���˱ض��������£����Ὣ����������¾�����������������Ѿ��γ��ˣ���
���������һ�ֽ��������������������ֲ���δ����������������һ�����������ѿ��ɵ���ȫ��ɱ����������Σ���
��翴������˵��仰��ʱ��ͷ������Ŀ������һ�������ɭ�䡣
��������ˣ���������Υ���������˵��������ν���߲���������ѿ��ɵ���ȫ��ɱ����ֻ������ɱ��һЩ�����������ѡ����ߣ��ӽ�������ʮ�꣬������������ϣ����������м��ִ��ģ����������Ҳ����Сһ�㡣�������ڰѴ���ɱ�ˣ�����Ҳ������Dzһ������ʱ������׳�꣬һ��ʩչ���֣����±��µ�����һ��Ҳʣ�����ˣ���
�������Ĭ�ˡ�
��Ȼ��ˣ��Ǿ�����ȥ�ɡ�������������ε��룬Ҳ���������ж��︣����ʱ����Ȼ����������ʰ������µġ�Ů����������Ҳ�����������Σ�����������Ƶ�δ���������������ݵ���ô�ֲ���
����������ֲ�������Ԥ���������ŵ���һ�꣬����۶�ʮ���꣨��Ԫ648�꣩��
��ʱ�˿̣������������ǧ����֮�У���һ��������õ���òŮ�ӣ�����һ����������㯵�Ŀ��������Ҵͥ������һ�����ɫ����ա�
������ӡ���У���Ƭ��պ�����Զ�����ɫ�ġ�
ʮ���ˣ��Ѿ�����ʮ���ˣ�
�����ʮ���꣨��Ԫ638�꣩�빬�����ڣ���������������ʮ��ʱ���Ѿ�������ָ�졢ü�䡢���ޡ������������ߣ�����ֻ����Զ����Ҵͥ������շ�����
���Ů���ں�Ʒ���Dz��ˣ�λ������Ⱥ�ĵ���Ʒ��
��ʮ�����빬����һ���������Ѿ��Dz����ˡ���ʱ�����գ���������һ�����ϲ��¡����̲����IJ��ˣ�
�����빬�ڶ����ij��ҹ����һ����ͥ���������ӻ��������ҹ����������������������
�����껪�����ȥ������Զ�ǵ���һҹ�ʵ������������´��صĴ�Ϣ����Ȼ��һ�ж����������⧲����������������������˸������������ܺ�������ͻ���������Ҹ���
Ҳ���������ĸոշ���һ���Ҹ���������̫�ڻʵ۵Ĵ��־��������ʲݵػ������ļ�����Ȼ����һ�ּģ����������Դֱ��ķ�ʽ��������һ��Ů�������һ��Ů�ˡ�
���ˣ��ʵ�����ʱ���������������������ã���������һ�����֡������
�ǵģ������������
������������Ȼ�ǵ�ʮ��ǰ���Ǹ��糿���Ǹ����ı������˵��糿��
��Ԫ638�꣬�����ʮ���ꡣ
���ա�������
һ����ѩ�������糿����ɫ��ڤ����������ȸ���������ϡ�٣�ż����һ��ֻ�䵥�İ�ͷ�̴ӿ��е͵��ӹ������¼����¶�����������У��漴�����ų������ɽ�����ȥ��һ�����Իʹ��ĺ����������ź��Ļ�ѩ�ڷ����ꤶ��У����ͣ���ѹʾ��ݶ�����Ӧ������ʿ����լۡǰ��
���Թ��е�ʹ�߾�ֱ�߽�Ӧ���������������˻ʵ۵�گ�顣��ʿ�������ס�Ӧ���������ϴ��ż��˹�ؽ�ּ��������ʹ�����нӹ�گ�����һ˲�䣬��������������ض��������
��һ�����ڻ������ˡ�
��������ǰ�Ѿ��ӵ����и��ͣ�˵����Ҫ����ʮ����Ĵ�Ů�ٽ�������Ϊ���ˣ���������һ�ٸ����Լ������ǻʵ۶�����һ�ŵĶ��裬Ҳ��Ů������ע���ĸ��֣������µ���ͷ��һ�����еĸ��˺Ͳ��ỹ��ǿ�ҵ�˺�����������顣
����һ�����ƺ���Ů��һ��̤����ݻʼҳ����������㼫�п��ܲ����������Ȼ����������������ڽ�������һ����ǽ������������ĺ�ǽȴ��ͬ��ǵ������������ĸŮ������롢������ġ�����һ�뵽Ů����һȥ�����������������ס���絶�ʡ��������¡�
Ȼ�������ӵ�گ���Dz���Υ���ġ�
����Ů����һȥ�Ǹ��ǻ������϶�ֻ��������һ����һ��ص����ϲԣ�ǧ��Ҫ��Ů������������ͷ��Ů���������ˡ���һ���ò������ӳ��ң�ֻ����ǧ��������Ҵͥ�����ж��Կ�ή��������עĿ���һ����ĬĬ��ȥ��
���ϲ���������Ů���ܹ�����ǧ�谮��һ�����������������г�һ���ܹ�ĸ�����£���ֻ��������������Ů��һ��ƽ�����������һ��Ů��Ӧ�е��Ҹ���
���˶��ѡ�
�ɼ���ֻ��������룬������Ȼ��������һ����ʵ�ֵ�������
���в�֪��ʱ��Ʈ���˴�ѩ����ɫԽ���ް���
��ʹ�ߵ�һ�ٴߴ��£��������ڻ���������Ů�������Ǹ�������á���ü��Ŀ��Ů�������߳���������ʮ����Ĺ뷿���߳���Ӧ�����ľ������Ⱥ�����ͥԺ���߳�������֮ǰ�����һ�������������������̽�Ļʼҳ����ԣ�������ݳ�����δ֪���˵������ԡ�
��˵���ѿ����˺���ǧ�������ɵ�����ʹ�ߵ�һ�ۿ������Ů��ʱ�����ﻹ�Dz�Լ��ͬ���ӹ���һ����֮�С�
�����Ǹе����IJ�������Ů������ò�������������ڲ�ͬ�����ʺ����顣
����һ������ӳ����һ��°�������һ�����������һ�����ˡ�
���Ϻ�һ��Ů��վ�ڸ���ǰ��̨���ϣ�Ŀ����Ů������̨�ס�������Ȼ������ֹ������Ů�첻ס�ص���Ȱο������Ȼ��ֹ�������ĸ��˺ͱ������������ϳ�����һ˲�䣬Ů����Ȼת����������ĸ������ʩ��һ��˵����������ӹ֪�Ǹ����ζ�Ů�����������������顤������ʺ���
�����Ӻγ�����һ�ָ��֣��α���С��Ůһ��������
ֱ���ܶ����Ժ����Թ��е�ʹ����Ȼ�����ǵ�������ڲ�ͬ��Ů��˵��������������Ļ���������˽�µij��ϣ�����ʼ�����ơ�������ӭ���빬����һ�죬���Ǿ��ѿ������Ů�����Ƿ��ˣ��պ����һ�����춯�ص��컯��
Ů��˵��仰ʱ����һ���������������飬���������ؿ����Լ���Ů������Ȼֹס�˿�����
��һ�̣�����Ŀ�������Ǵ�㵡�
��ΪŮ�������е���һ��İ����
��ݻʼ������ܿ����Զ�ˣ��ڰ�ãã�����֮��������һ�������䶯��С�ڵ㡣
�����صĹ��Ŵ�������Ȼ���ϣ������ڵ�Ů��֪�����Լ��������Ѿ����س����Σ�һ���ӽ��˵���֮�ң�һ���׳��˹�ǽ֮�⡣
ѩһֱ�£��ԲԕF���ͣ���£��������ظ�����Ӧ������̫����������·�ϡ�
��һ���·���ԶҲ�²����ѩ�������������Ů����עٲ��ϵļ����оþ�������
�����¡����ϳ����빬
��һ��ľ�����˵Ļ���ת����
����������Ƶ۹�����պ�Ȼ�����������������£�����ǧ����һ��������ͳ�εĽ�ɽ��Ȼ����֬��������ף�Ů����ļ���������Ȼ���˴��ܳ����̸��������Ż��⡣�ܶ��˶�֪����Ů������Dz�����ˮ�ˣ��丸��ʿ�����Ƴ��Ŀ��������������������顢���ݶ�������Ӧ��������ν������ԡ�λ��Ȩ�أ�Ȼ���ƺ����������ἰ����Ů��֮����ʿ��������ʵ��һ����λ���µ�ľ�����ˡ�
���й��Ŵ�������λ�����������ǣ�ʿ��ũ�������̡����˾����ĵȹ������ĩ����������������ᡢ����һ�������ڵ�Ȩ����ǰ��ʲô�����ǣ�������ũ���ֵܵ����˶�����ͦ�ñ���ֱ����Ϊ����������һ����Զ���ŵ�����֮�ס���ν����Ϊ�����ɡ�ĺ�������á�������˵ũ���������ֻҪ�ϸ���Ŭ��������������п���һ����������ҫ�棬�������Ļ�������ȴû�У���Ϊ�ƾٿ����Ĵ�����Զ����ͭ���������Ĺ��̴�ҵ�߹رա�����˵��������һ��������ҵ�Ĺٱ�λ����У��ƴ���δ�ؾ������֡�
����ʱ������ʿ���о��Լ�����һ�㶼�ֲ���������˵������쾵۴�����ľ��Ӫ������֮������һ�ʺ�ƣ�����������ģ���������Щ���մ�Ȩ����ָ��ʹ�Ĺ���ү��ǰ�����Բ��ݵ�ľ��������ʿ��Ҳֻ�е�����������ͷ�����ķ֡�
����Ľ�Ҳ��������ʿ���������̴���������֮һ��
��������˶����ڽ���Ӧ�꣬��һ����ʿ����Ȼ�������⡣��֮�����ܿ����¸���ԭ����������˵�ʱ��͢�ġ��Ĺ�֮һ�����������ۣ������۵ĵܾܵ������ܶ���Ӫ�����̵ĸ�ʹ�������ԣ����ࣩ������������Ǻ���Ů����������Ȼ����ʱ�����ʿ������֪��ʮ������Լ���Ȣ����Ů��Ϊ���ҡ���
��ʿ����Ȼͨ�������ֵܵĹ�ϵ������Ӫ�������д���ƣ�������һ����Ҫ������ȴû�м�ʱ�ͽᣨҲ�������ֶβ���Ӳ��û�ͽ��ϣ�������˾��Ƕ���Ӫ�����̵���ʹ�����������һ���ࣩ���ء���ʿ���������صľ���ԭ��ʷ�����أ�������һ����Կ϶������ض���������ľ�ķ��ӷdz���ˬ�����ԣ�����ʿ������ر����ڲ����ֳ��붫���ٳ�֮�䣬��Ƹ�Ҳ���Űεض�����������ڶ��ڽڿ���֮ʱ�����ؾ��Ѿ��ڰ��и���ʿ����֯��һЩ������һ��Ҫ���������ء�
Σ��ʱ�̣���ʿ����ǰ�����Ȩ������ɡ�����˹ؼ����ã�����Ȩ�����۵��˻�������Ӫ�����������������ⳡɱ��֮����
�������һ���������Ů��������Լ��ĸ��׳�����ڶ�����������һ����飬��������һ������������������ܵ��ξ��١�����������˵ʲô����Ϊ�����ҡ����峯֮�������ش��������ƣ��������˶����ó�����Ů����ô������������ԩ��ԩ���г𱨳�
��Ȩ����ǰһ��Ϳ�ص���ʿ��һ�����ӻ��˲����ϼҡ����긦��֮�࣬��ʿ��������δ���е�һƬãȻ�����Լ�������Ȼ�DZ�ס�ˣ����Ǿ�Ӫ���������֮��Ҳ�����ˡ��������·����ô�ߣ�
��ʿ��֪���Լ��������ְҵת�ͣ�����ȴ��֪����������ת��
���ҵ���꣨��Ԫ612�꣩��Ⱥ�۷������´��ң��ݾӼ������ʿ����Ȼ��ʶ������һ������ϴ�ƵĻ��ᣬҲ���Լ���̥���ǵľ���ʱ��������Ϊ˼��֮���漴���������������ش��һ�ξ������̴��֡�
��ϣ���������н���������������������������磬���װ��ѵ�λ���µ����˽�ɫ��
��ʿ����Ǯ����һ����ӥ�︮�������ĵͼ���ְ���Ӵ��������˻�֮;��
�����������������Ƕ��������ꡪ����ʿ��������̫ԭ������Ԩ�����˷����˵Ĵ��Ӵ����㷭��������ҡ��һ�����̫ԭ����Ԫѫ�����ƿ������������������һ�����˺�ͨ������ֱ�ϣ������������Ƶ۹���Ȩ���߲㣬�dz��ɹ��������������������Ҫ��һ�λ���ת����
���ǣ���ʿ��������ʱ��ֻ�����Ǹ�СС�ġ������������¾���������ʮ���ˣ���̫ԭ������Ԩ��������һ���ķ⽮��������������쾵����ı��֣�˫�������ݵ�λ������⣬��ʿ������������������֦���أ�
��ij��������˵����ʿ���ķ���ʷ��֮�˰ٶ���ǰ�ĺ���������Τ�Լ�һǧ�����ĺ춥���˺�ѩ�ң�������Щ����ͬ��֮�
�������Ͼ�������һЩ��ͬ�㡪����ҵ�ϵijɹ����������ǻ����˾�Ƹ����������������dz�������Ĵ��������;�����ʵ�ľ�Ӫ���ܡ����⣬��Ϊ��Ҫ��һ���ǣ�����ҵ������ȡ�õľ����������һ˫�������µĻ��ۣ�Ҳ��������һ�ָ߶�ǰհ�ķ���Ͷ����ʶ���Ӷ�ʹ�����ܹ���ǧǧ��������һ�۾������Ǹ����Ը����Ǵ�������ر��ġ�����������Ҵ�ʹ���Ǻ�����ԥ�س��֡���ϧ���۵�Ͷ�ʣ�
��������Τ���ԣ��ع����������˾�����ֵ�������������������ʿ��������̫ԭ������Ԩͬ���Dz��ɶ�õ������
���ڴ�ҵʮ���꣨��Ԫ616�꣩����Ԩ����̫ԭ��������ʹ���������ֵ��ر��������о�;��·����ʿ���ļң��ܵ�������ͼ����ٵ�����������ʱ��ʿ��һ������Ԩ�����϶������۽ܼ��ף��������䣬�˿ɴ����ӡ�����ȫ���顷�����ľš�����̨�����������������ѳ���Ѻ����Ԩ���ϣ��������պ��ȡ������λر�������ʱ����Ԩ���������������Ĵ��㣬һֱ�ڰ��л��������������ķ����ܣ���ȻҲ����ύ����ʿ�����־���ǿ�ɶ��Ҽҵ���ʵ�����
���μ��棬˫���Ա˴˵ĵ�һӡ�ܺã�����˵��һ�ļ��ϡ�������������Ե��˵ڶ�����Ԩ��ʽ����̫ԭ�����������Ѹ��о�Ӫ�Ÿɵ���ʿ�����Ϊ�о�˾�����༴���ܺ���װ���ľ�е������Ҳ����֪�����Σ�������������ʿ����ʶ���Լ������ҵ���һ�����Ա���Ĵ��������Ǹ��Ӳ��������ط�ӭ�ʸ�����ԨҲ�ܸ����ӣ�ʱ��������լ���ͣ�����ʿ�����������ޣ��������ء���
��ҵʮ���꣨��Ԫ617�꣩���峯���·ֱ����������˶�֪�������i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