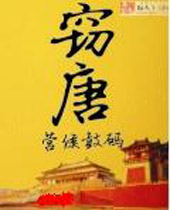血腥的盛唐-第4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世民派来的秘使订下了盟约。
突厥军队绝对没有料到,唐军会在这个大雨滂沱之夜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军营上下顿时一片慌乱。颉利可汗本来想要迎战,可一想到他的侄子突利和李世民之间很可能有什么阴谋,心里马上敲起了退堂鼓。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颉利终于决定退兵。
因为他绝不希望在与唐军交战的时候,让这个居心不良的侄子从背后捅他一刀。
尽管此刻退兵让颉利很不甘心,可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派遣突利和另一个亲王阿史那思摩到唐军大营,与李世民议和。而突利则借此机会,正式和李世民结下了香火之盟。
此后突厥退兵,这场有惊无险的五陇阪之战终于落下帷幕。李世民以他超乎寻常的胆识和谋略,演绎了一出经典的“孤胆英雄记”,不但兵不血刃地逼退突厥大军,而且成功地缔结了一个政治盟友,可以说在他辉煌的军事生涯中又增添了精彩绝伦的一笔。
也许正因为李世民的表现太过精彩了,所以历来很多人认为五陇阪之战精彩得有些过头。除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外,似乎还有严重低估突厥人智商的嫌疑。对此胡如雷先生也曾提出如下疑问:首先,突厥倾国而来,意在一决,怎么会以优势兵力而慑于世民的诱说,竟轻易讲和退兵呢?世民的个人作用似乎夸大得太不近情理了。其次,世民施反间计是肯定的,但内容究竟是什么呢?最后,世民对待二可汗的态度有显着差别,可以概括为拉突利打颉利,采取这样的策略有什么根据和条件呢?
对此,胡如雷先生以陈寅恪先生的考证为依据,证实“大约在克长安前,世民曾遵突厥风俗,与突利可汗约为‘香火兄弟’”(这可能只是一次非正式的口头约定)。因此,李世民在五陇阪不战而胜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是他在突厥上层中实行分化政策的反映,正因为世民在过去早已在二可汗中预布了棋子,才能在这次事件中收‘叔侄内离’之效,取得戏剧性的结果。”(胡如雷《李世民传》)
至于李世民派密使向突利施行反间计的具体内容,史书没有记载,胡如雷先生也没有提出他的看法,但是我们站在突利小可汗的立场上,完全可以推测出李世民向他传达了怎样的信息。
据《旧唐书·突厥传》,突利可汗在“幽州以北”统领着数十个小部落,但由于“征税无度”,导致“诸部多怨之”。由此可见,作为颉利长兄始毕可汗的嫡子,突利不但因年龄关系未能继承大可汗的宝座,而且现在连小可汗的位子也坐得不太稳当,日子显然并不好过。在此情况下,李世民很可能会向突利做出承诺:只要他与李唐交好,密切配合李唐对突厥的一切军事和外交行动,那么李世民就能保证作为突利的强力外援,尽可能维护他的利益,帮助他巩固地位,甚至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还可以帮他夺回大可汗之位。
为了自己的利益,突利可汗当然没有理由拒绝李世民。
不管李世民采用了什么手段,总之“五陇阪之战”确实是不战而胜了。
毫无疑问,五陇阪的精彩表现,使得李世民在那条通往权力顶峰的高空悬索上又往前迈进了一步。
我们不知道,当秦王李世民再次凯旋回朝时,齐王李元吉和太子李建成会用一种什么样的眼神看他。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眼中那嫉妒和愤怒的火焰,一定燃烧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灼热。
而此刻的高祖李渊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
他首先当然是感到欣慰,因为穷凶极恶的突厥人终于走了,京师长安总算化险为夷了。但是除了欣慰外,李渊肯定也会感到更深的无奈和不安,因为秦王头上的光环更加璀璨了,他对太子的威胁当然也就更大了。
然而,李渊又能怎么办呢?
除了尽其所能对秦王进行制约和防范之外,老皇帝还能做什么呢?毕竟秦王是帝国独一无二的军事王牌,如今边患频仍,只要突厥人的威胁一日不除,秦王就一日不可或缺。虽然李唐王朝并不缺将才,可问题是把兵权交给任何一个异姓将领,李渊都会一百个不放心。退一步说,即便秦王不是帝国的中流砥柱,他也是自己的儿子——掌心是肉,掌背也是肉。只要他没有公然做出夺嫡篡位的举动,李渊就只能苦心孤诣地保持现状,维持平衡。他一方面必须遵循“立嫡以长”的原则,始终维护李建成的太子之位,防止李世民越过雷池;另一方面也要念在秦王长年征战、劳苦功高的分上,给予他应有的荣誉和地位,不赞成太子和齐王采取过激的手段对付他。
总而言之,李渊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尽量把一碗水端平。
但是武德七年夏秋之交,我们却赫然发现,老皇帝手上的这碗水正在儿子们日渐升级的政治PK中剧烈颤动……
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突然倾覆。
第三章 玄武门之变
【突厥又来了】
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夏末秋初,大唐帝国的边境线上再次燃起烽火。
东突厥的颉利可汗自从去年秋天倾巢南侵、无功而返后,顿觉颜面尽失,大为不甘。经过将近一年的养精蓄锐,颉利便再度挥师南下。
这一次,颉利改变了战略。他并不打算再干上次那种看上去气势汹汹、到头来却劳而无功的蠢事,而是在西起凉州(今甘肃武威市)、东至幽州(今北京)的数千里战线上,采用“多点进攻、袭扰为主”的战略,专搞打砸抢,捞一把就走,不问仗打得漂不漂亮,只求有没有捞到实惠。这样的战争虽然不像去年那样直接威胁唐朝中枢,但覆盖面广、持续时间长,也着实让唐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东奔西跑、疲于应付,大伤了一回脑筋。
从六月末颉利亲率大军攻击灵州(今宁夏灵武市)开始,这场长达一年多的断断续续的骚扰战就拉开了序幕。
七月十二日,李渊对负责起草诏书的侍臣宣布:“突厥人贪得无厌,朕将与其全面开战,从今往后,给突厥人去函不能再以平等的‘国书’形式,而要一律改用‘诏书’和‘敕令’!”
相对于突厥的战略转变,李唐朝廷这次的军事任命也有了微妙的变化。李渊先后把右卫大将军张瑾、安州大都督李靖、行军总管任瑰等人调到前线御敌,而李世民则只是作为后备力量被派驻蒲州(今山西永济市),防守关中门户。
李世民之所以没有像往常那样被推上第一线,主要原因当然是突厥的这一波入侵并未对唐帝国构成太大的威胁,但同时也表明了李渊的用心,那就是尽可能抑制李世民的锋芒,不让他再出风头。
在前线看不到李世民的身影,这对颉利来讲绝对是一大利好。八月初,颉利亲率十万大军劫掠朔州(今山西朔州市)。张瑾等人急忙北上御敌,于十一日在太谷(今山西太谷县)与颉利会战。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仗张瑾全军覆没,出任行军长史的中书侍郎温彦博被俘,张瑾仅以身免,狼狈投奔李靖。
此仗突厥完胜,颉利发现自己有了讨价还价的筹码,便在八月末派人与唐帝国“和解”。可想而知,这种打完胜仗后主动提出的所谓“和解”事实上就是要挟,无非是想挟新胜之威狠狠敲一次竹杠。史书没有记载李渊对此做何反应,但从颉利随后便引兵北还的结果来看,李唐朝廷很可能又是违心地给了颉利可汗一笔数目可观的贿赂。
颉利这次之所以见好就收,一来当然是贯彻他“捞一把就走”的战略思想,二来估计也是担心继续向纵深推进迟早会碰上李世民。
突厥人的主力虽然撤了,但是其他各路偏师却依然在唐帝国广袤的北部边境袭扰不止。这场旷日持久、令人不胜厌烦的骚扰战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打到了武德九年(公元626年)。
在这一年的六月份之前,除了边境线上这种小打小闹的骚扰之外,唐帝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四月二十日这天,李靖在灵州境内的硖石与突厥军队狠狠干了一仗。据说这一仗打得极为惨烈,唐军从是日清晨一直血战到黄昏,最后终于将突厥人击退。大约也在同一天,朝中的太史令傅奕上了一道奏疏,内容是请求皇帝禁止佛教。李渊基本上采纳了傅奕的奏议,随后颁下一道诏书,对全国范围内的寺庙和道观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理整顿。
除了这两件事,这些日子总体而言相对平静。在这种表面的平静之下,时间走到了武德九年的六月初一。
这个盛夏的早晨,大唐帝国的一切看上去都与往日并无不同。
阳光依旧明媚而灿烂,天空依旧澄澈而蔚蓝。
然而仔细一看,这个早晨的天空却有些异样。
因为天上多出了一个东西。
那不是UFO。那是一颗星星——一颗大白天跑出来闲逛的星星。
武德九年六月初一的早晨,耀眼的太白金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从大唐帝国的天空上划了过去。
按古人的说法,这叫“太白经天”,是一种奇异而重大的天象。
那么,这种天象意味着什么?
史书说:“太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汉书·天文志》)金星白昼划过长空,天下将发生变革,人民将拥有一个新的君王。
此刻的李世民并不知道,两个月后,他就将成为这个新的君王。
尽管冥冥中一直怀有天命在我的自信,尽管对自己在政治上、军事上以及其他各方面所拥有的绝世才华从来不曾怀疑,但是眼下,李世民却只是一个受困于现实的藩王。
是的,起码到目前为止,他仍然只是不断遭人排挤、生存空间日益狭小的一介藩王。
从懂事的时候起,李世民就感到自己体内奔流着一种无以名状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显得如此完美、强烈而又如此自然,以至于李世民相信它绝对是上天的赐予。随着这种与生俱来的能量在生命各个阶段的流淌、奔腾和外溢,它便具有了诸多的表现形式,并被赋予了各种名称——
在少年时代,它表现为“幼聪睿”(《旧唐书·太宗本纪》)、“好弓矢”(《贞观政要》卷一)、“尚威武”(《全唐文》卷九);稍长,它表现为“玄鉴深远、临机果断”(《旧唐书·太宗本纪》)、“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后来,它在战场上表现为一种无坚不摧的惊人意志、一种藐视对手的傲然气概、一种冲锋陷阵横扫千军的骁勇和无畏;再后来,这种能量逐渐转化为一种掌控外部世界的欲望,一种睥睨世间万物的雄心,一种经天纬地、济世安民的抱负;到了最后,这种能量终于不可遏止地演变成一种问鼎皇权、君临天下的政治野心。
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
巨大的潜能促使李世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着生命的自我实现。他似乎始终坚信,上天既然赋予他这种潜能,必是要让他完成某种神圣的使命。
不可否认,这是一种强烈的自我期许。
说白了,这就叫自我暗示。武德四年李世民刻意去找道士王远知,也许正是为了加强这种心理暗示。所谓“眷言风范,无忘寤寐”(《旧唐书·王远知传》),正是他不断进行自我暗示的生动写照。
不过,我们有必要知道,这样的自我暗示恰恰是一个伟人最宝贵的品质之一、恰恰是伟人区别于凡人的重要标志——“它标示出我们,似乎我们注定要从事伟大的事业!这是一种我们不知不觉自我赋予的价值。正是靠这种品质,我们赢得了其他人的尊敬,也正是它,常常使我们高出那些门第出身、高官显爵和功勋本身。”(拉罗什福科《道德箴言录》)
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不断地进行自我激励,这一切共同构成了李世民精神力量的源泉。毋庸置疑,这种精神力量要远远大于门第、官爵和功勋这些外部事物所提供的价值。换言之,只有始终如一地告诉自己“注定要从事伟大的事业”,只有持续不断地让这种自我激励的精神之光投射到外部事物上面,通往伟大的道路才能被真正照亮。
美国精神之父爱默生说:“一心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会为他让路。”
然而,如果说在武德前期整个世界确实都在为李世民让路的话,那么到了武德中后期,这个世界却在他面前筑起了一道无形的高墙。
与此同时,李世民发现自己汪洋恣肆的巨大能量也被悄然纳入了一个无形的容器中。
这个容器是高祖李渊亲自为他量身定制的——不但划定了尺度,而且打造了边框。
李世民试图冲破它,可无论他往哪个方向奔突,到头来所有努力均告失败。
最后一次努力就是武德七年六月的杨文干事件。
从这个事件之后,无论是李世民还是李建成,肯定都会不约而同地意识到——用常规的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剩下的办法只有一个:武力。
只有挥起手中的剑,才可能结束这一切。
就像亚历山大曾经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