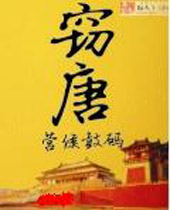血腥的盛唐-第30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十年后,元稹卒于鄂州刺史任上,终年五十三岁。
【敬宗登基】
长庆二年,宰相们在朝堂上斗得不可开交,而在地方上,藩镇叛乱更是此起彼伏。这一年三月,也就是河北战乱刚刚平息不久,武宁镇又传来了兵变的消息。
武宁镇的治所在徐州,地处江淮,历来是帝国的财赋重镇。这个地方出了乱子,对朝廷显然是一个沉重打击。消息称,发动兵变的人是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他在三月中旬驱逐了节度使崔群,夺取了军政大权,然后纵兵劫掠了中央盐铁专卖署在甬桥(今安徽宿州市)的转运院,抢走大量财帛,同时洗劫了各道停泊在汴水(连接黄河与淮河的运河)的进奉船,甚至连过往商旅的货物也强行搜刮了三分之二。
面对如此恶劣的反叛行径,穆宗李恒很头疼。
河北乱了,还可以依靠江淮的财赋发动一场平叛战争,如今江淮也跟着乱了,朝廷要拿什么来打仗?
最后,穆宗只好再度采用他那屡试不爽的“平叛”法宝——妥协。
三月二十八日,亦即兵变爆发仅仅十多天后,穆宗就忙不迭地授予了王智兴武宁节度使之职。
在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藩镇面前,与其说李唐朝廷的底线是被一次次突破了,还不如说此时的朝廷已经没有任何底线可言。
既然朝廷没有底线,那么造反也就成了一件低风险、高收益的事情了。这种好事,当然是人人抢着干。这一年七月,宣武(治所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又爆发兵变,将领李介驱逐了节度使李愿,自立为留后。
眼看藩镇叛乱已经从河北蔓延到了江淮和中原,再这么乱下去,帝国迟早会分崩离析。穆宗意识到事态严重,不敢再轻易让步了,连忙召集宰执大臣们商讨对策。
大臣们分成了两派。
一派以宰相杜元颖和财政大臣(度支)张平叔为首,他们认为,既然已经承认了河北三镇,宣武也未尝不可援用前例。
另一派以李逢吉为首,他坚决反对说:“河北的事情是迫不得已,现在如果连宣武也抛弃,那么江淮以南就都不再是国家的土地了。”
虽然李逢吉在权力斗争方面是个不折不扣的野心家,但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他的立场还是值得称道的。可碌碌无为的杜元颖向来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对李逢吉的强硬立场很不认同。他对李逢吉说:“李大人,难道你宁肯顾惜这几尺长的旌节,也不顾惜一方百姓的生命吗?”
这样的理由听上去似乎是冠冕堂皇的,让人很难反驳。
可事实上,杜元颖是在偷换概念。因为,李逢吉拒绝承认李介,绝不是出于对那“几尺长旌节”的爱惜,而是在维护朝廷废弛已久的纲纪,重拾屡屡被突破的底线。试想,假如李唐朝廷对所有叛乱藩镇始终采取妥协纵容的态度,那么天下藩镇必然会以河北、江淮和宣武为榜样,动不动就拥兵割据,与朝廷分庭抗礼。到那个时候,损失的就不是“几尺长的旌节”,而是帝国的秩序和天下的安宁。所以,与其说杜元颖等人的绥靖政策是在“顾惜百姓的生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在以苍生社稷的福祉为代价,换取虚假而脆弱的表面上的和平。
说白了,这就叫饮鸩止渴、苟且偷安。
李逢吉当然不会听杜元颖等人扯淡,所以坚持原议。双方争执不下,穆宗无所适从,这次御前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不久,宣武下辖的宋、亳、颖三州因不服李介,遂相继上表,请求朝廷另行任命节度使。穆宗大喜,这才感到李逢吉的意见是正确的。李逢吉随即向穆宗献计:“征召李介入朝担任禁军将领,然后命义成节度使韩充转镇宣武。如果李介抗命不遵,就命武宁镇与忠武镇东西夹攻,再由义成军从北面攻击,韩充一定可以顺利赴任。”
穆宗依计而行。
李介果然拒不从命。
七月底,穆宗下诏讨伐,命忠武节度使李光颜等部对宣武发起进攻。李介发兵抵御,却屡战屡败。到了八月中旬,李介在忧惧中一病不起,只好把军政大权交给兵马使李质。李质历来倾向于朝廷,于是再度发动兵变杀掉了李介,并将其麾下所有反叛将领全部诛杀,最后把李介的四个儿子逮捕,一起押赴京师。
随后,韩充顺利赴任,并驱逐了一千多名参与李介叛乱的士兵,迅速稳定了宣武镇的形势,一场祸及中原的叛乱终于得以平息。
长庆二年下半年,各地又陆续爆发了一些小规模的兵变,所幸都被及时扑灭,没有酿成大的祸乱。然而,到了这一年冬天,一个突如其来的不幸事件,却让整个长安城的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穆宗李恒中风了。
天子的病是因一场马球赛而引发的。十一月的一天,穆宗和宦官们在宫中打马球,一个宦官不慎从马背上跌下,穆宗受了惊吓,随后就中风瘫痪、卧床不起了。
天子卧病在床,一连数日不能上朝,满朝文武都不知道具体情况,不免忧心忡忡。此外,更让朝野上下惶惶不安的是,帝国还没有储君。
无论天子的病情能否好转,都必须早立太子。这是人们的一致想法。于是宰相们屡屡上疏,请求入宫朝见,但都没有得到答复。
这种时候,人们自然想起了裴度。裴度年初虽被罢相,但仍以右仆射的身份留在朝中。如今,恐怕也只有像他这种功高勋着的元老重臣,才有资格见上皇帝一面了。
经朝臣们请求,裴度连上三疏,要求册立太子,并请皇帝接见大臣。十二月初五,穆宗终于被宦官用“大绳床”抬了出来,在紫宸殿接见了宰执大臣。
虽然天子的脸色异常憔悴,行动能力也尚未恢复,但是看见他的神志仍然清醒,众人总算稍感安心。
不过,太子是无论如何要赶紧册立的。
裴度和李逢吉不约而同地向穆宗提起了此事。当然,两个人的出发点截然不同。裴度考虑的是皇权的平稳过渡和社稷的安危,而李逢吉则是想趁此机会抢一个定策之功。所以,两人的劝谏之辞也有着微妙而重大的差异。
裴度说的是:“请速下诏,负天下望。”
李逢吉不仅极力劝请,还提出了具体人选:“景王已长,请立为太子。”
景王就是穆宗的长子李湛,此时年仅十四岁。
尽管宰辅重臣请立太子的要求非常强烈,可在整个接见过程中,穆宗李恒却始终不置可否,一言不发。
此时此刻,穆宗的心情无疑是很悲哀的。因为他现在才二十八岁,正值青春年华,可宰相们劝他册立太子时那种急不可耐的神情,好像他是一个马上就要死掉的七八十岁的老头。
不过,这也怪不得宰相们。因为李恒知道自己已经废了,更何况他也知道——死神在拜访一个人的时候,绝不会事先询问他的年龄。
所以,不管多么不情愿,他都只能认命。
随后的几天,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请立太子的奏疏,又像雪片般飞进了宫中。穆宗怔怔地看着那堆奏疏,知道自己已经别无选择。
十二月初七,一道诏书颁下,景王李湛被立为太子。
接下来的整个长庆三年(公元823年),朝野上下都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帝国貌似一片平静。河北三镇虽然再次脱离了中央,所幸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并且自从朝廷平定宣武之后,各地藩镇似乎也收敛了一些,叛乱势头暂时得到了遏制。
这方面总算让朝廷暗暗松了一口气。可相形之下,朝廷内部的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朝堂上,李逢吉独揽朝政,极力排斥异己,于这一年八月把裴度逐出了朝廷,贬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而在内廷,宦官王守澄本来就因担任枢密使一职而手握大权,此次更是趁穆宗病重之际而彻底成为了天子的代言人。
李逢吉和王守澄就这样互为表里,联手控制了整个帝国朝政。
穆宗的病情在这一年没有进一步恶化,让满朝文武稍感安心。然而,天子随后便又染上了一样新的毛病,不禁让人们的心头再次蒙上了一层阴影。
天子喜欢上了长生之术,开始频频服用金石之药,就跟当年的宪宗一模一样。
遗传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
人们对三年前发生在宪宗皇帝身上的那一幕记忆犹新——宪宗之所以英年早逝,正是不顾一切追求长生的结果。如今,天子李恒再次走上父亲的这条老路,其下场可想而知。
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正月初一,穆宗在含元殿举行朝会,准备恢复因病中辍的例行早朝。
然而,李恒绝对没想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坐在金銮殿上。
正月二十日,穆宗旧病复发;短短两天后,病情迅速恶化,只好紧急下令太子监国。当天傍晚,刚届而立之年的穆宗李恒就驾崩了。
二十三日,李逢吉自命为“摄冢宰”,即摄政大臣。
二十六日,年仅十六岁的太子李湛在太极殿即位,是为唐敬宗。
穆宗朝的短暂历史就这样浮皮潦草地翻过去了。面对高高坐在金銮殿上这个尚未成年的新君,满朝文武未免都有些忐忑不安。因为大唐开国二百余年来,还从没出现过如此年轻的皇帝。
说白了,李湛还是个孩子。
饱经沧桑的大唐帝国,将在这个孩子手中变成什么样子?
人们不敢预料。
【一人独大的朝堂】
自从裴度和元稹罢相,李逢吉便在朝中一人独大,其地位已无人可以撼动。于是,朝臣中的识时务者纷纷投靠,很快就在李大人周围结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死党。
这个死党以李逢吉的侄子李仲言为首,麾下有张又新、李续之、张权舆等人,号称“八关十六子”。所谓“八关”,是说李仲言等八人是这个死党的核心层,若有人想求李逢吉办事,必须先贿赂他们,相当于八道关卡;李仲言等八人另外还有八个手下,所以统称“十六子”。
面对权势熏天的李逢吉一党,多数朝臣都不敢招惹,只求洁身自好。但是,总有那么一两个刚直不阿的人,始终不买李逢吉的账。
比如翰林学士李绅。
自中唐以后,翰林学士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很多宰相都是从这个位子提拔上来的,所以中晚唐的翰林学士常有“内相”之称,最典型的就是德宗时代的贤相陆贽。
当初穆宗在位时,李绅就深受天子信任,每逢穆宗跟他讨论朝政,他都会不失时机地贬抑李逢吉。此外,凡是李逢吉有奏表递进宫中,只要让李绅看到了,通常都会利用自己的“内相”职权,不动声色地将其否决掉。
对于这样一个处处跟自己叫板的人,李逢吉自然是恨得牙痒。所以早在去年冬,他就曾精心做了一个局,要把李绅扳倒。
那是长庆三年九月,御史中丞一职出缺,穆宗让李逢吉推荐人选。李逢吉二话不说就推荐了李绅。他的理由是,李绅秉性正直,为官清廉,正是肃清政风、维护朝廷纲纪的不二人选。
穆宗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当即批准。
此时的穆宗当然不会想到,李逢吉这是在给李绅下套。他把李绅支到御史台,目的就是要看一场好戏。
当时,御史台的一把手是韩愈。而韩愈跟李绅是同一种人,性情刚直,眼里从不揉沙子。很多人都知道,宪宗末年,韩愈曾因那篇着名的《谏迎佛骨表》差点被宪宗砍掉脑袋,多亏裴度和崔群力谏,才救了他一命。长庆三年六月,韩愈从吏部侍郎调任京兆尹。在他之前,禁军一贯在京师作威作福,过去的京兆尹都不敢惹,可韩愈一来,禁军一下就变乖了,纷纷在私下里相互告诫:“这姓韩的连佛骨都敢烧,咱千万别犯在他手上!”
韩愈当时除了京兆尹,还兼任御史大夫。按规定,有此兼职的京兆尹不仅要在本衙门办公,还要在某些规定时间到御史台去坐班,称为“台参”。
李逢吉就打算在这里做手脚,让李绅和韩愈去死磕。
李绅刚到御史台上任,李逢吉马上通知韩愈不必台参。李绅不知此事,一连几天发现顶头上司都不来上班,便给韩愈发了道公函。韩愈有宰相特许,当然有理由不去。于是两人便在来回往返的公文中打起了口水仗,双方措辞都很强硬,最后闹得沸沸扬扬,满朝皆知。
李逢吉随即上奏穆宗,说李绅和韩愈身为大臣,竟然为了如此芝麻小事就撕破脸面,实在不堪为群臣表率,理应贬谪。
穆宗也觉得李、韩二人太不识大体,遂贬韩愈为兵部侍郎,贬李绅为江西观察使。
到了这一步,李绅和韩愈才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他们被李逢吉下套了。随后,两人便以辞谢君上为名入宫觐见。穆宗也依稀感觉事有蹊跷,就让他们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仔细讲了一遍。
事情摊开后,傻瓜也明白问题出在哪了。
穆宗当即收回成命,改任韩愈为吏部侍郎,李绅为户部侍郎。
精心布下的局就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李逢吉大为不甘。
长庆四年正月,穆宗驾崩,敬宗即位,李逢吉一边庆幸李绅的靠山倒了,可一边却不免担心新君会再度重用李绅。
为了彻底摆平这个死对头,李逢吉召集党羽,日夜密谋,最后终于想出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