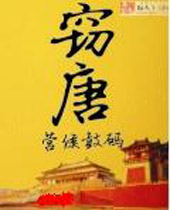血腥的盛唐-第20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柳骨”。
在音乐和歌舞方面,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个造诣精深的艺术家。大明宫太液池东边有一座梨花盛开的庭园,称为“梨园”,唐玄宗就在这里创建了皇家艺术中心,亲自遴选数百名具有艺术禀赋的乐工和宫人,共同进行教学、创作和演出,称为“梨园弟子”,其中以李龟年最为知名,后人称其为“歌圣”。玄宗本人精晓音律,善击羯鼓,尤其擅长作曲,中国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霓裳羽衣曲》,就是由李隆基亲手谱写,由杨贵妃编舞并演出的。
除了文化艺术以外,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科技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僧一行。
一行俗名张遂,自幼博览经史,精通天文历法,唐玄宗时受命主持历法修订,编成了《大衍历》,其体例结构一直为后代沿用。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了恒星移动现象的人,比英国人哈雷发现恒星移动早了一千年。同时,他又倡议测量子午线的长度,虽然测量结果并不很准确,但却是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的记录。此外,他还与另一位科学家梁令瓒合作,制成了观察日月运动的“黄道游仪”,以及观察天象的“浑天铜仪”。后者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用机械转动的天文钟。
……
这就是盛唐。
这就是锦天绣地、流光溢彩的盛唐。
这就是令无数后人心驰神往、魂牵梦绕的盛唐。
然而,到了公元八世纪中叶(天宝末年),当大唐帝国走过一百三十多年的辉煌与沧桑,在企及鼎盛与巅峰的同时,也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浮华、堕落与衰乱。
从一千多年后回头去看,透过岁月的尘烟与时光的帷幔,人们能否看清,哪一刻才是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是不是从开元十三年泰山封禅的那一刻起,当玄宗李隆基以千古一帝的姿态伫立在人间绝顶的时候,一种器满则盈、盛极而衰的历史宿命就已经悄然埋下了伏笔?
是不是从开元末年李林甫独揽朝纲的那一刻起,当玄宗李隆基越来越耽于享乐、怠于朝政的时候,大唐帝国的马车就已经开始了盲目的奔驰、并日渐暴露出倾覆的危险?
又或者是从天宝初年安禄山强势崛起的那一刻起,当玄宗李隆基毫无原则地给予他越来越大的权力和荣宠时,一场极具颠覆性和毁灭性的历史悲剧就已经拉开了序幕?
再或者是从天宝末年杨国忠擅权乱政的那一刻起,当玄宗李隆基宁愿把自己埋在盛世迷梦中不愿醒转的时候,曾经繁荣强大的帝国就已经滑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也许,上述每个时刻都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节点,只要唐玄宗李隆基能够在当时的每个节点上保持清醒,在“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问题面前正确选择,那么他到最后就不会被迫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极端命题,更不会在马嵬驿陷入那个“要江山还是要美人”的人生困境……
不过,对于天宝十四年春天的李隆基来说,上面这些问题都是不存在的。
因为在他看来,“安禄山造反”是个不值一哂的伪命题。他绝不愿为此花费脑筋,让自己徒增烦恼。此时此刻,他正怀着跟年轻人一样的激情,在热烈拥抱自己生命中的第七十一个春天。
人生七十古来稀。既然上苍如此慷慨,赐给了他太平江山,赐给了他绝代佳人,又赐给了他享受这一切的长寿人生,那他有什么理由不好好享受呢?!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白居易《长恨歌》)〗
这样的春天,只宜享受纯净的艺术和无暇的爱情;这样的春天,只适合在恍如天籁的《霓裳羽衣曲》中,让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比翼双飞、翩跹共舞,不能让世间一切俗务来搅扰,更不能让政治来插足、大臣来聒噪。
简言之,李隆基生命中的第七十一个春天,只属于他的爱人杨玉环,不属于他的帝国和臣民……
然而,让李隆基感到无奈的是——他毕竟是一国之君,而一国之君就不可能真正地摆脱政治。比如早春二月的某个早晨,朝廷又接到了安禄山的奏请,要求用三十二名蕃将替代汉人将领。李隆基懒得去操那份心,立刻下诏让有关部门颁发任命状。诏书一下,杨国忠和新任宰相韦见素立刻入宫,极言安禄山反迹已露,绝不可同意他的奏请。
李隆基大为不悦。
安禄山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你们这些人总是放不下对他的嫉恨和猜疑呢?
狼来了,狼来了……就会说这一句!你们就不能来点新鲜的?
李隆基不顾宰相的劝阻,仍旧把三十二份任命状颁给了安禄山。杨国忠和韦见素深感不安,最后只好想了一个明升暗降的办法,建议玄宗让安禄山入朝为相,然后将范阳、平卢、河东三个节度副使升任正使,借此解除安禄山的兵权,从根本上削弱他的势力。
李隆基拗不过两个宰相的力谏,只好勉强同意。可诏书草拟好后,玄宗却留着不发,而是悄悄派了心腹宦官辅璆琳去范阳,让他刺探安禄山的虚实。辅璆琳去范阳走了一趟,收受了安禄山的重金贿赂,回来后就极力向玄宗鼓吹,说安禄山“竭忠奉国,无有二心”。
李隆基笑了。他对杨国忠和韦见素说:“禄山,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东北二虏,籍其镇遏。朕自保之,卿等勿忧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朕对安禄山推心置腹,料他必不会心生异志。东北的奚和契丹,全是靠他镇守遏制的。朕可以当他的保人,你们无须担忧!
天子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杨国忠和韦见素还有什么好说的?
于是,征召安禄山入朝的计划就此不了了之。
在李隆基看来,安禄山势力再大,也是自己的赤胆忠臣;安禄山能量再强,也是帮自己镇守国门的一条看门狗。所以,安禄山绝不会是杨国忠臆想中的那头狼!
朕自保之,卿等勿忧!
这是多么掷地有声的话语、多么乐观自信的态度啊!
然而,事实很快就将证明——李隆基错了。
这个严重的错误不仅将彻底葬送锦天绣地、歌舞升平的盛唐,而且将开启一个长达一百四十二年的乱世——一个充满了流血、杀戮、黑暗、纷争和死亡的乱世。
第五章 安史之乱爆发
【狼真的来了!】
从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的夏天起,安禄山对朝廷的态度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本来安禄山还想再摆一下迷魂阵,没打算这么早动手,因为他觉得玄宗待他不薄,想等玄宗死后再起兵,可如今杨国忠天天喊说他要造反,终于把安禄山给彻底惹毛了。
这一年四月,玄宗派给事中裴士淹去“宣慰”河北,主要目的是去安抚安禄山,同时当然也想再摸摸安禄山的底牌。裴士淹抵达范阳后,安禄山声称身体不适,不但不出面迎接,还把这位钦差大臣晾在了宾馆里,而且一晾就是二十多天。
后来,安禄山虽然接见了裴士淹,但却故意把所有亲兵都召集起来,让他们全副武装进行警戒,摆出了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
一见这阵仗,裴士淹吓得魂都没了。
这是在接见天子使臣吗?这分明是在向朝廷示威啊!
裴士淹匆匆宣完圣旨,赶紧一溜烟跑回长安,向玄宗禀报了事情的经过,说安禄山包藏祸心,“无复人臣礼”。(《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对于裴士淹的汇报,玄宗却不以为意。因为前不久心腹宦官辅璆琳刚从范阳回来,还信誓旦旦地说安禄山“竭忠奉国,无有二心”,时隔不过两个月,安禄山怎么可能就包藏祸心了呢?
在玄宗看来,裴士淹纯粹是夸大其词,危言耸听。
玄宗不把裴士淹的汇报当一回事,可有个人却如获至宝。
他就是杨国忠。
这些日子以来,杨国忠正“日夜求禄山反状”,如今听说安禄山怠慢朝廷使臣,总算抓住了把柄,立刻下令京兆尹出兵包围了安禄山在京师的宅邸,逮捕了安禄山的门客李超等人,并把他们扔进御史台监狱,连夜突击审讯。
可御史台审来审去,也没审出个子丑寅卯,杨国忠大怒,便命御史台把李超等人全部秘密处死。
如此一来,朝廷与安禄山的矛盾便进一步激化了。
当时,安禄山的长子安庆宗和宗室的荣义郡主订了婚,住在京师。他眼见杨国忠动了杀机,大为恐惧,赶紧派人密报安禄山。
得知门客被杀的消息,安禄山又惊又怒,遂下定起兵的决心。
六月,安庆宗与荣义郡主的婚礼举行在即,玄宗亲自下诏,召安禄山入朝参加婚礼,可安禄山却推说生病,拒不入朝。
实际上,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安禄山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了。
玄宗当然不至于看不出这一点。然而,他还是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不愿意相信安禄山真的会造反。
七月,安禄山向朝廷上表,说要献上北地良马三千匹,每匹马配备两名马夫,并由二十二名蕃将率部护送马匹入京。
在这个节骨眼上献马,还兴师动众地派军队护送,安禄山的心思不言自明。河南尹达奚珣赶紧上奏玄宗,说:“请皇上诏令安禄山,若要献马,可由沿途各地官府供应差役,无须另派军队护送。”
安禄山这马献得实在是蹊跷,玄宗心里不禁犯起了嘀咕。恰在此时,宦官辅璆琳受安禄山贿赂之事又突然被人告发(很可能是杨国忠所为),玄宗才猛然有所醒悟,觉得自己是被辅璆琳和安禄山给结结实实地忽悠了一把。他勃然大怒,马上找了个借口杀了辅璆琳,然后又派另一个心腹宦官冯神威前往范阳,给安禄山带去了一道手诏,告诉他说献马可以,但没必要派军队护送;同时,玄宗还在手诏中情深意切地对安禄山说:“朕最近专门命人为你新凿了一个温泉池,十月份在华清宫等你。”(《资治通鉴》卷二一七:“朕新为卿作一汤,十月于华清宫待卿。”)
如果说玄宗此前对安禄山的宠幸确实是出于真心的话,那么这一次,玄宗显然是在给安禄山灌迷魂汤了。
可是,安禄山会上钩吗?到了这个时候,他还会稀罕玄宗给他新作的这一“汤”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冯神威抵达范阳后,得到的待遇并不比裴士淹好到哪里去。他在宣读玄宗圣旨的时候,安禄山居然不跪拜接旨,而是一脸傲慢地踞坐床榻,只微微欠了欠身,淡淡地说了一句:“圣人安好。”等冯神威宣完圣旨,安禄山又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马不献也可以;你回去转告圣上,到了十月,我会昂首挺胸、精神抖擞地到京师去见他。”(“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
话说到这份上,已经是赤裸裸的威胁了。
安禄山随即安排冯神威住进了宾馆,之后就再也没有露面。心惊胆战的冯神威在宾馆里寝食难安,度日如年。几天后,冯神威终于接到了安禄山的逐客令,却没有接到照例应该呈上的谢恩表。
可此时的冯神威也顾不上什么谢恩表了,一接到逐客令便马不停蹄地跑回长安,一见到玄宗就哭哭啼啼地说:“臣差一点就见不着皇上了!”
从冯神威离开范阳的那一天起,亦即天宝十四年八月开始,安禄山就把起兵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防止泄密,安禄山只和心腹幕僚严庄、高尚和将军阿史那承庆加紧密谋,其他文武将吏一概被蒙在鼓里。
众人只是觉得奇怪,自从入秋以来,安禄山便频频犒赏士卒,并且三天两头搞军事演练,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直到这一年冬天,当有奏事的官员从长安返回范阳,安禄山才借机伪造了一道天子密诏,然后召集众将说:“有密旨,命我举兵入朝讨伐杨国忠,诸君应全部随我出征。”
众将官相顾愕然。直到此刻,他们才终于明白——原来这几个月的好酒好肉都不是白吃的,比平时多好几倍的饷银也不是白给的,是通通要让他们拿命去抵的!
说白了,这世上本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阵杀敌也是他们分内的事情,这本来没什么好说的,可让他们感到郁闷的是——这一次并不是跟敌人拼命,而是掉转枪口跟朝廷拼命!
然而,不管众将佐中有多少是仍旧忠于李唐、不愿追随安禄山造反的,现在都已经是身不由己了。除了硬着头皮跟安禄山登上贼船,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集结了麾下的所有部队,并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共计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正式在范阳起兵。
次日清晨,安禄山在蓟城(范阳治所)城南誓师,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宣布即日南征,同时告谕三军将士:“胆敢反对起兵、扰乱军心者,一律屠灭三族!”
是日,安禄山命节度副使贾循留守范阳,然后亲率十五万铁骑从蓟城出发,大举南下,兵锋直指东京洛阳。
“安史之乱”就此爆发。
一场彻底改写唐朝历史,并将深刻影响整个中国历史的战乱就此拉开序幕。
《资治通鉴》称:“禄山乘铁舆(防箭的铁轿),步骑精锐,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