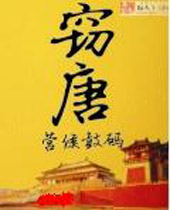血腥的盛唐-第17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和刘幽求同病相怜的,还有很早就靠边站的钟绍京。唐隆政变后,钟绍京只当了几天的中书令就被罢为户部尚书,不久又贬为蜀州刺史。玄宗即位后,他回朝复任户部尚书,但是随后又被贬为太子詹事,和刘幽求一样坐了冷板凳。面对如此际遇,钟绍京当然也是牢骚满腹,所以时常和刘幽求一起慨叹时运不济。
刘、钟二人的怨言很快就传进了一个人的耳朵。
他就是新任宰相姚崇。
姚崇很清楚,虽然他和刘幽求他们一样,都是李隆基的心腹股肱,但是单纯从拥立李隆基为帝的角度来说,刘幽求等人的功劳是远远大过他的。所以姚崇觉得,如果不将刘幽求等人彻底排挤出朝,他的宰相之位就不可能牢固,更难以放手施政。
为此,姚崇毫不犹豫地告发了刘幽求和钟绍京。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闰二月,玄宗命姚崇对刘幽求和钟绍京立案审查,准备治罪。刘、钟二人不服,不断上疏抗辩。
其实,无论是玄宗还是姚崇,他们的目的一样,只是想把刘幽求等人逐出朝廷而已,并不希望事态扩大。所以,当刘、钟二人极力抗辩,事情一度陷入僵局的时候,姚崇便又恰到好处地站出来打了一个圆场。他与另两个新任宰相卢怀慎、薛讷联名,向玄宗奏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闲职,微有沮丧,人情或然。功业既大,荣宠亦深,一朝下狱,虑惊远听。”(《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刘幽求等人都是功臣,忽然转任闲散职务,心情难免沮丧,此乃人之常情。功劳既大,所受的荣宠也深,一旦逮捕下狱,恐怕会惊动朝野舆论。
姚崇的言下之意,就是暗示玄宗见好就收,不宜把事情做得太绝。
玄宗心领神会,当即贬刘幽求为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刺史,并把他的七百户封邑削掉了六百户,同时贬钟绍京为果州(今四川南充市)刺史。
不久,在姚崇的积极配合下,玄宗又把王琚、魏知古、崔日用等人也先后贬出了朝廷。
至此,昔日辅佐李隆基君临天下的政变功臣基本上已被贬黜殆尽。
这就叫飞鸟尽,良弓藏。
此乃政治角斗场上的游戏规则,自古皆然。更何况,为了彻底改变自神龙革命以来政变频仍,皇权危弱的局面,李隆基也只能这么做。
《新唐书》称:“幽求之谋,绍京之果,日用之智,琚之辩,皆足济危纾难,方多故时,必资以成功者也。然雄迈之才,不用其奇则厌然不满,诚不可与共治平哉!姚崇劝不用功臣,宜矣。”这“不可与共治平”一语,道破了玄宗罢黜功臣的个中原委。
从历史上看,这“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一幕,几乎也是每个强势帝王为了巩固皇权,开创大业而必修的一课。尤其对李隆基这种非嫡长子出身,并且靠政变上台的皇帝而言,这更是他亲政之初的势在必行之举。
作为睿宗庶出的第三子,相对卑微的出身始终是李隆基的一块心病。所以,如果想要坐稳皇位,他就必须在摆平功臣的同时——再摆平宗室。
当时,能够对李隆基构成潜在威胁的宗室亲王,就是他的四个兄弟和一个堂兄(豳王李守礼)。一开始,李隆基对五王采取的主要是怀柔手段,“专以衣食声色蓄养娱乐之,不任以职事”,让他们在富贵温柔乡中当逍遥王爷。
每当政务之余,李隆基总是陪五王一起寻欢作乐,彼此间不以君臣相称,而以家人之礼游处,有时候一起到郊外击球、游猎,有时候召他们入宫一同宴饮、斗鸡、下棋、吟诗作赋、演奏乐器,待酒足饭饱,笙歌散尽之后,就用特制的“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据说,要是诸王偶染微恙,李隆基便会为之“终日不食,终夜不寝”。有一次薛王李业生病,李隆基甚至亲自为其熬药,以致胡须不小心被火烧着了,左右大惊失色,连忙扑火,李隆基却说:“但使王饮此药而愈,须何足惜!”由此,朝野上下都交口称赞天子李隆基“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继感情笼络之后,李隆基又在制度上采取了防范措施。开元二年六七月间,在宰相姚崇等人的建议下,玄宗把五个兄弟都外放到了地方上担任刺史,并且规定:五王到任后不负责具体政务,一切州务都交由僚佐处理。到了开元八年左右,玄宗的皇权已经相当巩固了,才让五王陆续回到了长安,授予了他们司空、司徒等荣誉衔,同时严禁他们“与群臣相结”。
就这样,在玄宗的情感安抚和制度约束之下,这些亲王都学会了夹起尾巴做人,在余生中始终表现得临深履薄,谦恭谨慎,让一些野心家即便想利用他们搞阴谋也无从下手。有些侥幸之徒想要轻举妄动,到头来也只能自遗其咎,招致祸败。比如开元八年,有几个朝臣就跟岐王李范、薛王李业走得很近,企图背着玄宗搞一些小动作,最后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贬谪流放的下场。
事后,李范和李业惶恐不安,主动向玄宗请罪,李隆基还安慰他们说:“我们兄弟亲密无间,都是一些趋炎附势之徒强相托附,我不会责怪自己的兄弟。”最后,为了表明自己对兄弟的真情,李隆基甚至赌咒发誓说:“倘若我有心猜忌兄弟,就让我天诛地灭!”
就这样,李隆基以他的高明手腕巧妙地摆平了功臣和宗室,消除了所有潜在威胁与后顾之忧,牢牢握住了他的帝王权杖。
不可否认,在处理功臣和宗室的问题上,李隆基的做法具有浓厚的权谋色彩。但是,和历史上那些为了巩固皇权而翦除功臣,诛杀兄弟的皇帝比起来,李隆基采取的手段还是相对比较温和的。他充其量只是做到了“飞鸟尽,良弓藏”,而没有发展到“狡兔死,走狗烹”的地步。
换而言之,李隆基身上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人情味。用一句经典台词来说:“没有人情味的政治是短命的。”唐玄宗李隆基之所以能在皇帝的位子上一坐就是四十五年,而且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也许就在于他的人情味,在于他执政手段的温和。
【姚崇:为盛世奠基(上)】
在李隆基摆平功臣和宗室的过程中,宰相姚崇一直与他默契配合,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令人奇怪的是,同样作为玄宗昔日的亲信,姚崇为何没有遭遇“兔死狗烹”的命运,反而能得到玄宗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倚重,从而位极人臣,独揽朝纲呢?
究其原因,应该有以下三点。
首先,姚崇虽然和郭元振、刘幽求等人一样,都是玄宗政变的支持者,但他并没有直接参与,因此也就无所谓什么“功高震主”“尾大不掉”,对玄宗的皇权当然也就构不成威胁。其次,姚崇是三朝宰相,素以“吏事明敏”,精明强干着称,玄宗要追求天下大治,自然需要这种富有执政经验的大臣辅佐。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姚崇忠于人主,深明君臣大义。
有一则故事很能表明姚崇的这种节操。
那是在神龙政变成功后,女皇武曌被软禁上阳宫,姚崇作为武曌一手提拔起来的宰相,虽然追随张柬之等人参与了政变,但得知女皇被软禁之后,还是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感的泪水。别人都兴高采烈,惟独他一个人“呜咽流涕”。张柬之见状大为不满,警告他说:“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始。”
姚崇说:“事则天岁久,乍此辞违,情发于衷,非忍所得。昨预公诛凶逆者,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缘此获罪,实所甘心。”(《旧唐书·姚崇传》)随后,姚崇果然被逐出了朝廷,贬为亳州刺史。
像这样一个忠于旧主,性情坚贞,绝不与时俯仰的臣子,有哪一个皇帝不喜欢呢?又有什么理由让李隆基不放心呢?
当然没有。
因此,姚崇必然会成为辅佐玄宗开创盛世的不二人选。
姚崇没有让李隆基失望。
据说,姚崇于先天二年十月奉密诏赴骊山觐见玄宗时,一见面就提出了十个条件,相当于跟皇帝“约法十章”,声称若是玄宗不答应,他便拒绝出任宰相之职。(《新唐书·姚崇传》)
居然会有如此牛逼的臣子,皇帝让他当宰相,他还和皇帝讲条件。
是的,姚崇就是如此牛逼,否则他就不是姚崇了。
当然,姚崇之所以敢跟玄宗讲条件,是基于两个判断:一、玄宗为人豁达大度,有容人之量;二、玄宗锐意求治,亟需一套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
果然不出姚崇所料,虽然他的倨傲态度让玄宗颇有些诧异,但玄宗还是流露出了浓厚的兴趣,表示很想听听他所谓的“十事”。
姚崇随即侃侃而谈,向玄宗提出了他的十条政治建议:一、施政以仁义为先;二、不谋求对外扩张;三、执法从亲近之人始;四、宦官不得干预政事;五、对百姓除租赋之外不得苛取;六、皇亲国戚不得担任台省要职;七、对臣下接之以礼;八、鼓励犯颜直谏;九、停止建造各种佛寺道观;十、杜绝外戚干政。
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十事要说”。
此“十事”,与其说是宰相跟皇帝的十条约法,不如说是姚崇的十大施政纲领。当时玄宗求治心切,此“十事”又皆为切中时弊之言,所以玄宗欣然接受,全盘采纳。
从玄宗朝廷日后出台的种种政治举措来看,基本上都是以这十大纲领作为指导思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姚崇所言的“十事”,实际上就是一整套针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治国方略。正是这一套方略的推行实施,玄宗朝廷才会呈现出一派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清正廉洁、抑奢求俭的政治新气象,从而使得“贞观之风,一朝复振”。(《旧唐书·玄宗本纪》)
玄宗深知,姚崇是一个栋梁之才,只因这些年来政局紊乱,仕途颠沛,所以他一直没有机会施展才干,如今所有的障碍既已清除,自然要给他提供一个广阔的舞台,好让他放手大干一场。史称开元之初,“上初即位(实际应为“初亲政”),励精为治,每事访于元之,元之应答如响,同僚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资治通鉴》卷二一○)
然而,玄宗固然敢于“专委”放权,姚崇复相之初还是有些放不开手脚。就算是任命一些低级官吏,姚崇也要一一禀报,不敢自专。有一次,玄宗听完他的奏报,忽然仰头望着房梁,一句话也不说。姚崇再三言之,玄宗却始终沉默。姚崇又惊又疑,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只好怏怏告退。
姚崇退下后,玄宗的心腹宦官高力士忍不住问:“陛下刚开始治理大政,宰相奏事,可与不可都当面议,陛下为何一言不发?”
玄宗面露不悦之色,说:“朕把政务交给姚崇,有大事理当奏闻,可像这种任命郎吏的小事,他自己完全可以定夺,又何必事事来烦朕?”
高力士恍然大悟,随后便把皇帝的这个指示精神透露给了姚崇。姚崇闻言,所有的忧愁和顾虑一扫而光,从此大胆秉政,“独当重任”,于大小政务“断割不滞”。当时的另一个宰相卢怀慎自知才干不及姚崇,于是“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旧唐书·卢怀慎传》)
有一次,姚崇家中办丧事,请了十多天假,朝堂中政务公文堆积如山,卢怀慎不敢决断,只好向玄宗请罪,没想到玄宗却说:“朕把天下事交给姚崇,卿等坐观其成就可以了。”
姚崇假满归来,没几天就把积压的政务全部处理掉了。众人大为叹服,姚崇亦颇为自得,忍不住问中书舍人齐澣:“我当宰相,比起管仲、晏子如何?”
齐澣略微沉吟,答:“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世,至少用其一生。而公所订之法,随时变更,似乎不及二人。”
姚崇又问:“那么你对我作何评价?”
齐澣道:“公可谓‘救时宰相’。”
姚崇大笑,把手中毛笔一掷,说:“救时宰相,也殊为难得了!”
姚崇理政,善于权变,因事制宜,从不墨守陈规,且办事雷厉风行,注重实效,所以“救时宰相”之誉,亦可谓恰如其分,实至名归。姚崇的上述执政风格,在随后展开的灭蝗斗争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开元三四年间,黄河中下游地区连续爆发了大规模蝗灾。蝗虫过处,千里赤地,颗粒无收。在古代农业社会,蝗灾所造成的损失无疑是各种自然灾害中最为严重的,如果对治不当,不仅国家的粮食储备会出现问题,还会造成大量的灾民和流民,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动摇统治根基。
所以,如何对付这场前所未有的蝗灾,就成了姚崇最后一任宰相生涯中最严峻的挑战。
蝗灾始发于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夏。古代人笃信天人感应之说,认为蝗灾是一种天谴,人力不可违抗,因而面对铺天盖地、漫山遍野的蝗虫,各地的官员和百姓都不敢捕杀,而是一味焚香祭拜,修德禳灾,希望以此感动上苍,使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