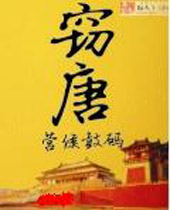血腥的盛唐-第1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时至今日,我们阅读的比较权威的《后汉书》版本,仍然是李贤的这个注本。
看着李贤得意扬扬地捧出他的《后汉书注》,武后当时的愤怒可想而知。
她断然没有想到——眼下的李贤居然会比当初的李弘走得更远,对她的挑衅和攻击也更为有力、更加明目张胆!
这是武后绝对无法容忍的。
既然李贤可以无视她的鞭子,她当然只能动用铁锤和匕首了。
仪凤元年,新太子李贤以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姿态,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和武后抗争并决裂的道路。
很显然,这是在步李弘之后尘。
很显然,这是一条不归路。
正当武后与太子的冲突日渐升级之际,一则耸人听闻的流言又在宫中不胫而走。流言说太子李贤并不是天后的亲生儿子,而是天后的姐姐韩国夫人所生。
没有人知道这则流言的出处,只知道它一下子就在朝野上下传得沸沸扬扬,并且使得武后和李贤原已异常紧张的母子关系变得雪上加霜。
面对这则杀伤力极强的流言,一贯自信而倔强的李贤也不得不产生了深深的疑惧。
他知道,尽管这种居心叵测的流言蜚语从来不值得深究,更不值得让人牵肠挂肚,可他还是不无痛苦地发现——这则流言并非空穴来风!
原因很简单,只要算一下武后几个子女的出生日期,李贤的身世自然就显得疑窦丛生了:李弘生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的下半年,而李贤生于永徽五年(公元654年)的十二月,其间相隔二年。这本来很正常,但是问题在于,在弘和贤之间,还有一个在襁褓中便已夭折的安定公主!
这就是说,如果李贤真的是武后所生,那武后就必须在两年之间连续怀孕并产下三个子女,这可能吗?
显然不太可能。
既然如此,那李贤会不会真的如流言所说,是韩国夫人所生的呢?
可能性很大。
因为武后当时正以昭仪的身份得宠于高宗,她的姐姐就有可能以这层关系得以自由出入禁中,并因此被高宗宠幸,产下李贤。可韩国夫人根本没有任何名分,所以,如果高宗想要留下这个孩子,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让武后认养。而当时武后正与王皇后激烈较量,就算她对高宗和韩国夫人的暧昧关系心生不爽,也只能以大局为重,暂时忍耐。所以我们认为,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形势下,由武后出面认下姐姐的这个“未婚先有子”,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在这个世上无忧无虑地活了二十几年,有一天却猛然发现,自己的身世原来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谜团!这样的发现无论对谁来讲,都是一个异常强烈的打击。
李贤当然也不会例外。面对这个巨大的谜团,他感到愤怒,也感到悲哀。可他却不知道要如何消解自己的愤怒和悲哀。他既不可能去问武后——我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儿子?也不可能去问高宗——当年您和韩国夫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他只能咬紧牙关,对一切保持沉默。
用沉默来对抗这则居心叵测、甚嚣尘上的流言,用沉默来对抗那个身份暧昧、性格冷酷的“母亲”!
接下来的日子,大明宫中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关太子身世的流言还没有消停,又有一些让人不快的政治谣言开始在李贤的耳边嘤嘤嗡嗡地飞舞。
此前的流言来历不明,让人想发泄都找不到对象。可这次却不同,所有的谣言都有一个明确的制造者和传播者。
这个人就是明崇俨。
明崇俨是一个术士,在江湖上名声很响,据说很早就跟师傅学了一手绝活——役使鬼神。除此之外,他还擅长画符、厌胜、医术等,总之是旁门左道中的顶尖高手。乾封初年(公元666年),明崇俨在某地当县丞,当地刺史的女儿得了绝症,眼看就要没救了,明崇俨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副偏方,竟然药到病除、妙手回春,把上司女儿的一条命硬是从鬼门关外拉了回来。
从此,明崇俨名声大噪,连天子李治都被他惊动了,很快就把他召进宫中,对他甚为赏识。明崇俨入宫后,屡经升迁,于仪凤二年(公元677年)被任命为正谏大夫,并得到天子特许,入阁侍奉。从此明崇俨就成了高宗和天后身边的红人。
如果是一般的江湖术士,混到这分上绝对应该知足了。
可明崇俨显然不是一般人。
他对政治似乎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兴趣。史称高宗每次召见他时,明崇俨都会做出一副神秘兮兮并且忧国忧民的样子,“假以神道,颇陈时政得失”。借着鬼神说政治,这自然要比朝臣们千篇一律的奏议新鲜得多,所以高宗每回都被他说得频频点头,“深加允纳”(《旧唐书·明崇俨传》)。
明崇俨对政治的强烈兴趣引起了武后的关注。后来的日子,武后就经常密召明崇俨,让他暗中搞一些厌胜之术,俨然把他视为心腹。很快,明崇俨就成了武后手中的一枚棋子,被摆上了与太子对弈的棋盘。
能得到天后宠信,明崇俨深感三生有幸,自然愿意替天后效犬马之劳。
可他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棋局。他贸然入局的结果,最终不仅为他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而且由此引发了高宗末年性质最严重、规模最大的一起政治案件。
在武后的授意下,明崇俨开始刻意制造对太子李贤不利的政治言论。比如说什么“太子庸劣无德,不堪继承大统,只有英王(李显)相貌最似太宗”,又说“看来看去,还是相王(李旦)的相貌最为尊贵”云云,总之是一意挑拨太子与兄弟之间的关系,借此蛊惑人心,制造矛盾。
明崇俨在宫廷内外肆意散播这些言论,当然引起了太子李贤极大的愤怒。
一个靠旁门左道上位的江湖术士,居然敢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攻击当朝太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李贤知道,明崇俨之所以如此嚣张,无非是因为背后有天后撑腰。
一想起自己的身世之谜,再加上明崇俨的恶意攻击和公然挑衅,李贤的气真的是不打一处来——明崇俨,你别以为仗着天后撑腰就可以有恃无恐!老子明里是拿你没辙,可暗里还收拾不了你吗?
调露元年(公元679年)五月,东都洛阳爆发了轰动一时的“明崇俨被刺案”,深受高宗和天后宠信的术士明崇俨遇刺身亡。
当时,二圣与太子均在东都。武后对此案异常重视,立刻命人缉查凶手,几乎把洛阳翻了个底朝天,可最后还是一无所获。朝廷只好含糊其词地宣布明崇俨“为盗所杀”,然后追赠他为侍中,连带着赏给他儿子一个秘书郎的官职。
其实对于这个案件,武后心里是有数的。她知道,刺杀明崇俨的幕后真凶并不是什么江洋大盗,而很可能就是太子李贤!
可是,武后没有证据。
所以她只能等待。
她的铁锤和匕首早已准备好了。
她等待的,就是太子李贤自己露一个破绽——露一个致命的破绽!
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八月,武后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
此前不久,东宫的谏官、司议郎韦承庆上书劝谏太子,劝他不要过度纵情声色、嬉戏宴游,应该“博览经书以广其德,屏退声色以抑其情”(《旧唐书·韦思谦传》)。
可令人遗憾的是,太子李贤却对此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
说起李贤的私生活,本来也没什么大问题。唐代享乐之风盛行,王公贵族的生活更是惯以飞鹰走马、嬉戏宴游为主题。李贤不是李弘,他从小并没有受到严格的储君教育,私生活自然要比太子放纵一些,这其实也无可厚非。更何况,李贤也并非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他的才学修养在王公贵族中还是属于上乘的,否则也不会受到高宗的一再褒扬,更不可能拿出《后汉书注》这样的学术着作。
然而,尽管李贤的私生活基本没什么问题,可还是在某方面让人抓了小辫子。
那就是李贤的性取向。
虽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可李贤的性取向依然是男女通吃,极度宠爱一个叫赵道生的户奴,时常与他同床共寝、出双入对,而且赏赐极厚。谏官韦承庆所批评的“纵情声色”,主要就是针对此事。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古代贵族男子经常有这种断袖之风、龙阳之好,所以就算李贤有双性恋的倾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问题在于——现在的李贤不是普通贵族,而是堂堂帝国储君!既然是这样的身份,他当然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比别人更为检点。
贞观年间的太子李承乾就是因为宠幸娈童称心,才被矢志夺嫡的魏王泰抓住了把柄,一状告到了太宗那里,最终被废黜。可见有唐一朝,对这方面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如今李贤当上了太子,还一如既往地把亲密爱人赵道生带在身边,这不啻于给自己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尤其是他现在正处于和天后激烈交锋的非常时期,就更应该爱惜自己的羽毛。
可李贤毕竟太年轻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在你死我亡的政治角斗场上,任何一个细微的破绽最终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
如今他既然露出了这么大一个破绽,精明过人的武后当然不会轻易放过。
于是,武后不失时机地出手了。
李贤的末日就此降临。
抓住了李贤“纵情声色”的把柄后,武后立刻命人对太子发出指控,旋即立案审查。武后亲自点名,命不久前刚刚升任宰相的中书侍郎薛元超、黄门侍郎裴炎,会同御史大夫高智周,组成三司合议庭,开始了对李贤的审查。
按照唐制,只有性质特别严重的大案要案,才需要由中书、门下两省长官会同御史大夫共同审理,现在武后搞出这么一个豪华阵容,摆明了就是要把这个普通的“风化案”整成大案,就像当初的长孙无忌硬是把一起“性骚扰案”弄成了震惊朝野的谋反案一样!
而此次的两位主审官——薛元超和裴炎,又恰恰是武后一手提拔上来的。这几年来,原本铁板一块的宰相班子已经有数人因病去世,武后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于是破格提拔了几个低品级官员,总算在帝国的权力核心中楔入了自己的政治势力。
薛元超是初唐的着名文人,文品甚佳,但人品不怎么样,曾先后依附李义府和上官仪,但两次遭贬,属于比较典型的墙头草,如今得到武后的信任和器重,自然是感恩戴德、决意报效。还有裴炎,在拜相之前官秩仅为四品,能够青云直上也全拜武后所赐,这次主审太子案,正是他扬名立万、捞取政治资本的良机,所以他必然也要全力以赴。
由武后这两个一心想创造政绩的亲信来审案,李贤当然是在劫难逃了。
薛元超和裴炎首先从李贤的情人赵道生身上打开了突破口。有司把赵道生逮捕归案后,还没有动用大刑,赵道生就一五一十全招了,声称太子李贤唆使他刺杀了明崇俨。赵道生一招供,案件的性质突然就严重了,从毫不起眼的“风化案”变成了富有政治色彩的“教唆杀人案”。但是据此还不足以彻底整垮太子,于是主审官们再接再厉,又从东宫的马坊中搜出了几百副崭新锃亮的盔甲。至此,案件再度升级,从教唆杀人案又变成了谋反案。武后非常满意,马上为此案定调,宣称太子谋逆,其罪当诛!
武后已经把绞索套上了李贤的脖子,长年躲在深宫中养病的高宗才如梦初醒。他慌忙要求武后手下留情,宽宥太子的过失。然而一切已经来不及了。武后严词拒绝了天子的请求,说:“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资治通鉴》卷二○二)
武后声色俱厉,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而高宗则只能低声下气,苦苦请求。最后的处理结果相对折中:太子贤免于一死,但废为庶人,押往长安幽禁;那几百副惹来滔天大祸的盔甲在洛水桥当众焚毁。一年后,李贤又被流放到了离京师两千多里的巴州(今四川巴中市),在那个边瘴之地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春秋。
李贤被废后,武后趁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几位支持太子的宰相先后被罢黜,其他一些与太子友善的宗室亲王和朝臣也遭受株连,或贬谪或流放,被驱逐殆尽。而在此案中立下大功的两位主审官则在一年后再次荣升:裴炎升为侍中,薛元超升为中书令。
至此,一度与武后分庭抗礼、激烈争锋的太子贤被彻底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他在朝中的势力也被全部肃清。武后以她的心机和铁腕,又一次铲除了权力之路上的障碍,在天下人面前牢不可破地树立起了她的无上权威!
调露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亦即李贤被废的第二天,高宗和武后的第三子——英王李哲(原名李显)被立为太子,朝廷改元永隆,大赦天下。
有唐一朝,民间长期流传着一首政治歌谣,名为《黄瓜台辞》,相传为李贤所作: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如今,武后这个种瓜人已经亲手摘下了两条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