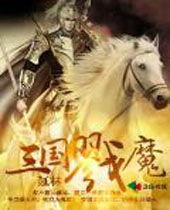慢船去中国-第7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只是提醒你。不希望这样的情形再次发生。你也看到了,我们的工作环境是这样的,这里不是美国。”毕卡迪先生态度非常诚恳地说。
“毕卡迪先生绝对是经验之谈,简妮。”Tim说。他将手搭在毕卡迪先生的肩膀上,对简妮说,“你们的家族经历有点相似呢,毕卡迪先生的家族也是印度最早的买办,为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工作的。你们都来自于世代与西方合作的商人家族。”
简妮看着毕卡迪先生,在格林教授书中长达几十页的附录里,她看到过对东印度公司的介绍,那是最早将鸦片卖到东方,开拓东西商路的英国公司。在中国,它因为鸦片战争的关系而臭名昭著,在英国,却被称为开拓东方市场的先锋。那么说,他们两个人的祖先不光都是prador,而且是贩卖过鸦片的那种prador。现在,他们又都为西方的海外公司工作。
毕卡迪先生也看看简妮,他再次将自己黛黑的手伸出来,与简妮握了握,“幸会。”他说。
也许,他们的祖先,在一次鸦片交接的过程中也见过面,也握过手呢。简妮握住他柔软的手,心想。她的手上,马上沾满了毕卡迪先生的香水气味。格林教授的书里说,当年美国公司也从东印度公司批发鸦片到中国。东方的买办们用的都是同样一种洋径邦英语沟通,一般会英文的人听不懂他们的话。一般人也不会去学,甚至接触不到这样的语言。自己祖先的那口洋径邦英文是从穆炳元那里学来的,那,他祖先的洋径邦英文又是从谁那里学来呢?如今,他们的后代再次相会,不再说那种从东方发展出来的特殊英文。他有口音,带着伦敦风格,她也有口音,带着美国东部风格,他们的英文如今已经无可挑剔。
“幸会。”简妮说,“真的是幸会。”
他们互相打量对方,简妮还是在他满面真正的笑容里找到了暧昧,那种不能常常正正的表情象米饭里的小沙子一样。她想,等自己若干年以后,象毕卡迪先生现在这样,做到了海外公司的高级雇员,不管经历多少事,都一定不要粘上他这样的表情。她暗中在裙子上擦着自己手上的香水气味。
“你会习惯的,也会做得好,要是你心里还真的流动着你祖先勇敢的血。”毕卡迪先生微微摇动着脑袋,简妮想起来,总是在学校餐厅的柜台里勤工俭学的印度同学,在赞美什么的时候,也总这样微微摇晃自己的脑袋,她想,这一定是印度人的习惯。
他将自己祖先的血称为“勇敢的血”,简妮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赞美,这个词让她一震。格林教授书本里,王家那是非纷纭的历史从她心里流水似地淌过去,祖先留在最早的照片上魔术般的面容,那种她开始认为是强悍的神情,如今被这个印度人点破,简妮认识到,也许那就是一种无耻的,或者是无畏的勇敢。格林教授在书上对东方买办们有一个总结,他说:“他们先得使自己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他们不为民族工作,而是为先进的文明工作。然后,他们才能成为坚强的买办,在封闭而骄傲的东方文明中生存,并发家致富,而且推动古老的国家走向西方世界。”也许,这种勇敢,是一个世界主义者的勇敢。简妮想,经历过独立运动的毕卡迪先生的家族,和经历过解放运动的王家一样,都有难以启齿的往事。毕卡迪先生一定也经历过煎熬,在煎熬里,他体会到了祖先的勇敢,也体会到了自己身上对祖先的那份勇敢的继承。他的话打动了简妮,使她暂时放弃对他的讨厌。
“你是勇敢的吗?”简妮问。
毕卡迪先生用力摇晃着他的头:“我吗?我有令人厌恶的勇敢。”
简妮不好意思地笑了,他象蛇一样,聪明到令人恐惧。
回到办公室,简妮学着劳拉的利落,处理手里的工作。心里却一直在琢磨毕卡迪先生说的话。格林教授在书里说过,东方的买办们,在东西方的沟通中,就象一道在从高处向低处的大河上的水闸,控制着高处的西方文明向低处的东方流动的速度。没有他们,西方就无法走向东方。他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他们处于中间地带,起着控制,选择,帮助和抵制的作用,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种族和政治的禁忌,只谋求商业上的发展与成功。简妮想,也许就是因为他们谁也不属于,孤独无傍总是免不了的,所以,血液里得有特别的勇敢。简妮想起在美国时对自己身上商人天赋觉醒的飘飘欲仙,这时,她才意识到,事情远没有这么单纯。她并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真的也有毕卡迪先生说的那种勇敢。Tim曾说过,有他们这样家族背景和经验的人,就是海外公司的宝贝。这是简妮听到过的最受鼓舞的话。她适时地提到格林教授的书,答应将那本书带来给他们看。
第十章:买办王(13)
她看到克利斯朵夫拿了文件,将他裹在牛仔裤里硕长的腿伸直了,穿了耐克球鞋的大脚轻轻一钩,身下的椅子便轻盈地向电脑台滑去。简妮想,他是不会体会到自己面临的这种复杂局面的,他的血太单一了。
察觉到简妮的目光,克利斯朵夫冷冷地看了她一眼。他不喜欢她,就象不喜欢劳拉一样。劳拉常常表达出对大陆人的嫉恨,让他想起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宿怨。劳拉到了共产党的地盘上,仗着是总经理秘书,一味地挑三拣四,象《红楼梦》里面的小老婆们,他气不过。简妮明明是前几年才出国的上海人,却做出一副美国人的样子,轻易不多讲一句中文,要是说中文,也只说上海话,一副洋奴样子,更让他厌恶。他自己学英文出身,自认为并不老土,也不古板,甚至在私心里,他也是个喜欢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人,当时他也是尼娜说的那些因为广告而投靠这家公司的大学生之一,他也希望自己能在一个国际化的地方开始自己的人生,他也是那些肯用自己几个月的工资买一双全进口的新式耐克球鞋的青年,可他就是见不得劳拉和简妮那种狭洋自重的样子。也许,与劳拉相比,他更讨厌简妮,她身上还有上海女孩的那种离心离德的劲,“IWasChinese。”那是什么屁话。
王建卫听说有一个上海女孩来顶替劳拉时,还打算统战一下,在美国人那里安一个眼线。一听到她和劳拉象说暗号似的说英文,克利斯朵夫就知道没戏。他打电话告诉王建卫说:“走了一个蒋介石,来了一个李鸿章。”
克利斯朵夫没想到,中国人民都已经站起来几十年了,还有简妮这种人。他想起自己很小的时候,看过一个动画片,里面有句话,实在很合适简妮:“阶级敌人就象屋檐下的洋葱,根焦叶烂心不死。”
他其实也很想工作一两年以后,去美国深造,但他想,自己有一天在美国学有所成,当钱学森,当詹天佑,哪怕当容闳,也决不当她王简妮,在会议桌上,他就看出来,她以当买办为荣,她的是非观与美国人一致,她也觉得香水和花露水之争,是市场之争,而不是民族之争。克利斯朵夫不觉得自己是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洗了脑的人,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而简妮则是没有中国人尊严的人。比起真正的美国人来,他更讨厌简妮这样的假洋鬼子。那厌恶里带着鄙视,那是一种类似嫉妒的恨意。但克利斯朵夫绝不承认那是嫉妒,他怎么可能嫉妒她,他鄙视她。为她的立场悻悻然。
他决定,下次要找个机会,将鲁迅的小说集借给简妮看。
在他冷冷的眼色里,简妮提醒自己,要尽量防止劳拉的故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她突然想,格林教授的书里,对王筱亭只身来往在义和团出没的地方,建立内地的经销点和仓库那个时期,只有短短的一句:“他成功地沿着河道,建立了经销鸦片,收集茶叶,桐油和蚕丝的货栈,甚至自己的钱庄,保证能够按时向洋行交回货款。”简妮想,这绝不是容易的事。也许如今只能找到,他是怎样的成功,却找不到他经历了怎样的困难。
住在上海让简妮痛苦。她对四周有不可思议的抗拒。她是带着理想来到上海的,她以为经过美国大学,她已被训练成一个新人,一个接受过国际市场学训练的,野心勃勃的美国青年,来上海掘她的第一桶金。但上海却象流满了黑色石油的阿拉伯海滩,将她紧紧粘住,举步维艰。在海湾战争的时候,被倾泻到海水里的石油曾经污染了许多海滩。不得不停在海滩上的海鸟,一落地,就被粘住,很快就奄奄一息。电视新闻里,那些变成黑色的海鸟在遍布油污的海边满跚而行,徒劳地在黏着的黑油里拔自己的爪子,扑打已经不能用了的翅膀。简妮一直记得那令人绝望的情形,那时她正被不断地拒签,身心具焚,她觉得,自己就是那些黑色的海鸟中的一只。
但如今她回到上海,心里却再次涌出了阿拉伯海鸟的感觉。她不想被公司里任何人提醒自己是个中国人,Tim,或者是毕卡迪先生,还有洋铁皮的标语牌和克利斯朵夫,他们大家象印地安螃蟹一样,在她将要逃脱的时候,合力将她拉回到原来那个可怕的位置上,并死死地压着她,让她不得不接受。她永远都记得,Tim在听说她说“IwasaChinese”时,脸突然往下一挂的样子,还有公司里的中国同事耸着鼻子冷眼看她的样子,她风闻他们叫她“买办王”,用毕卡迪先生带着印度口音的语气,用英文的结构,将她的姓放在后面,嘲讽和憎恶地。
她也不想被家里的任何人提醒自己是个上海人,成长的过程中处处充满美国消毒药水的气味,背景里充满了象海滩上的石油那样又黑又重又粘稠的苦难。她控制不住地恨家里人,恨爸爸妈妈的脸和声音,恨爷爷,恨那间小客厅里的陈设。上海就是她的泻满石油的海滩,到处都是痛苦。那天她已经走到人民公园门口了,透过修剪得象墙一样的冬青树,她又看到那里的林荫道,还有路边的绿色木条长椅,简妮以为自己会感慨,但她心里涌出的,却是强烈的抗拒。她不想回想起自己在寒冷的空气中站在英语角与人搭讪的情形,还有那一次次被拒签后一片死寂的心。这个上海,到处散落着细小的绳索,一不小心,就拉出一段让简妮痛苦的往事,或者事实,瓦解她从美国带回来的美梦。
第十章:买办王(14)
感到自己在美国建立起来的认同在被上海瓦解,简妮心里非常恐惧。她没想到,范妮在美国遇到的事,她回到中国来时遇到了。她们是那么不同,但她们却横竖就是当不成一个朝气蓬勃,欣欣向荣,自由自在的美国人。简妮每天的每个时刻都不高兴,她虽然坚持从家里搬到公司为她租的公寓里,但爸爸妈妈几乎每天都给她打电话,在她的答录机里留言,每天晚上回家,答录机上的小红灯都令她咬牙切齿地闪着。在上班的路上,她讨厌被人碰到身体,讨厌看到26路公交车,到了公司,她走进办公室之前,心蹦蹦地跳,害怕遇到迎头一棒。她常常想起第一次进办公室,看到劳拉的情形,她从自己现在用的灰色写字桌后慢慢站起来,她怕自己将要变成劳拉第二。和美国同事在一起时,她常常不高兴,要是有人向她学一句上海话,或者问起,为什么上海的男人穿睡衣在街上走。和中国同事在一起时,她也常常不高兴,因为她不得不说上海话,和他们一样的语言。和中国同事与美国同事一起时,她为中国人的不修边幅更不高兴,他们没有每天洗头,他们喝汤时发出响声,他们站着的时候不挺拔,他们坐下的时候拧着腰身,他们嘴里有香烟气味,女同事的袜子不合身,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心里为他们那么羞耻,那种不忍目睹的羞耻简直远远超过了憎恨。有一次,简妮陪Tim请日本人在希尔顿吃川菜,席间,也有日本人喝汤霍霍地响,但简妮觉得,自己和那声音一点也没关系。
在上海,简妮觉得自己就象生活在地狱里。
简妮决定自救。
她不敢,也不能在办公室里做什么,所以,她从家里开刀。
劳拉走后,简妮就搬到劳拉在龙柏的小公寓里,离开了那条灰色的弄堂,和父母。她借口说,合资公司要求她住到前任秘书的公寓里去,外事部门不愿意美方雇员住在上海人中间。这是个光彩的理由,爸爸当时说:“中国人将你当成美国人管了,你小心秘密警察。”但他的神情,很有点得意。听说简妮住在龙柏的外国人公寓里,爸爸妈妈很有点孩子成龙成凤的骄傲。他们不知道,那里只是在上海的外国公司低阶雇员的公寓,高级雇员都住在虹桥和波特曼右边的外国人公寓里。简妮的房子,不过是一间卧室加一个小客厅,小客厅里只有一张沙发,一个茶几,还有一只空的玻璃花瓶,卧室里也不过一个大衣柜,一张床,一张桌子而已。与家里的房间相比,这里充满三星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