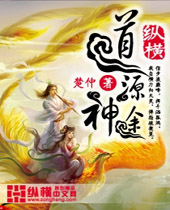流血的仕途-第5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赵士程乃皇家后裔,自然非仕途落魄的陆游所能比。红酥手,黄藤酒,眉梢眼角诉风流,可叹对面非陆游,悔青个肠!该,该,该。沈园相见一年之后,唐婉香消玉碎,承认吧陆游,这个噩耗让你feelmuchbetter。
第一百八十五部分
蒙恬虽为将门之后,却自幼嗜读经书,喜好文学,李斯一篇《谏逐客书》,看得他荡气回肠。在回咸阳的路上,蒙恬由衷赞道:“先生之笔,有如天半游龙,非人间所有。此谏书必可流传久远,为后世垂范。”
听完蒙恬的夸奖,李斯面色依然严峻。对李斯来说,把《谏逐客书》写好并不难,他一不小心就把《谏逐客书》写成了千古名作。难的是,要让《谏逐客书》达成它的使命——改变嬴政的决定,挽救他的命运,也挽救那些外客们的命运。作不到这一点,《谏逐客书》就只能是一堆华丽的文字垃圾。李斯才不在乎后世会有多少人来读他的《谏逐客书》,有多少学者为《谏逐客书》正义注疏,有多少学子对《谏逐客书》逐字解读。他眼中的读者只有一个——嬴政。
所谓工夫在诗外。别看李斯写《谏逐客书》之时,援笔立就,一气呵成,但他在文本之外下的工夫,蒙恬却并不能知道。也许,在李斯预感到宗室将对外客不利之时,他就已经开始构思这篇文章了。当他象布卢姆一样,在咸阳街头踌躇徘徊时,脑海里盘旋的还是这篇文章;在放逐的路上,他也没有停止过这篇文章的酝酿。用如此长时间来构思,李斯显然不是在斟酌词句,而是别有考虑。
首先,他要摸准嬴政的想法,站在嬴政的角度考虑问题,分析他的处境,判断他的立场,然后对症下药,务求斯人不言,言必有中。《谏逐客书》不出则已,一出便要正中嬴政的下怀,而不是下阴。
其次,同样重要的是,李斯要确立自己的写作姿态,给自己定位。在他面前有两个失败的先例,足以令他汲取教训。说起来,这两个失败先例的主人公,还都是李斯有些渊源:一是同为楚人的屈原,一是师兄韩非。
屈原见逐,作离骚。韩非不用,写孤愤。虽说屈原是怨而哀,韩非是怨而愤,但终究都是在怨。李斯也是有资格怨的,他无辜遭到驱逐,的确是受了委屈,而且委屈还不小。屈原是贵族,可以怨而哀;韩非是公子,可以怨而愤;李斯身份虽不比这两人,但至少也可以怨而悲嘛。而如果照这个定位写下去,我们不难想见,《谏逐客书》就将是另外一副面目:我李斯是怎样的劳苦功高,和大王共度过多少君臣和睦的甜蜜时光,如今受到宗室的陷害,命运如何的不公,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放逐的路上多少辛酸,同行的外客多么凄惨,再加入几个老人和小孩的行状特写……诸如此类,这般等等。
没有人说这样写不行,但从屈原和韩非的遭遇可以看出,哀怨的姿态并不能解决问题。通常来说,怨妇甚至比泼妇更加可怕。泼妇是不会讲理,怨妇是不肯讲理。没有人愿意做出怨气的筒,更别说是高高在上的君王了。再者,嬴政并非普通的君王,他能干出囊扑两弟、囚禁母后这样的事来,显见绝非可以动之以情之人。对付嬴政,必须晓之以理。于是我们看到,在《谏逐客书》里,李斯跳出了个人情绪的小格局,也跳出了围观他写字的外客们集体营造的悲伤气场,始终保持着冷静和克制,站在旁观公允的角度书写谏议,只字不提个人的冤屈、外客的凄凉。在他的文章里,只有血,没有泪。
很快就要面见嬴政,李斯有必要先提前了解一下嬴政对《谏逐客书》的反应,于是问蒙恬道:“大王读谏书时,你可曾陪侍在大王之侧?”
蒙恬点点头,道:“先生之书,大王击节赞叹,不能释卷。其中有几句,大王更是念出声来,吟叹再三,深有会意之色。”
听到嬴政的反应,李斯兴致好了许多,又问蒙恬道:“吾书你能背诵否?”
蒙恬有着照相机般的记忆力,当下将《谏逐客书》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李斯面露嘉许,道:“大王念出声来的那几句,汝可还记得?”
蒙恬道:“记得的。是……”
李斯打断蒙恬,道:“可是以下三句?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每说一句,蒙恬脸上的惊异之色便加重一分。李斯三句说完,蒙恬惊叹道:“先生真神人也。大王吟叹良久的,正是这三句。蒙恬费解,先生何以能未卜先知?莫非这三句话中藏有什么玄机不成?”
李斯大笑,道:“你不懂,大王却是懂的。”李斯知道,嬴政看出了他文章中的潜台词,所以才召他面见。李斯加鞭策马,回咸阳的路还很漫长,而在路的终点,他将站在嬴政面前,把文章中的潜台词一一揭晓。
想到这里,李斯止住了笑容,重新陷入思索。现在还没到笑的时候,对他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第一百八十六部分
李斯回到咸阳,顾不上旅途的疲劳,直奔咸阳宫而去。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已经破产,他和十年前刚到咸阳时一样,手中唯一的筹码就是一根三寸不烂之舌。李斯站在熟悉的宫门前,抬头仰望,竟有恍如隔世之感。他终于重新回到了赌桌,虽然筹码少得可怜,他也必须赌下去,如果不赌,便永无翻本的可能。
郎中令王绾远远见到李斯,忙迎上去,道:“客卿大人一路辛苦,大王已等候多时。”王绾乃是嬴政身边亲信之人,嗅觉最为灵敏,对嬴政的心思也吃得最准。王绾依然称呼他为客卿大人,应该不仅是出于私交,而是传达了一种信息——嬴政的立场已经出现松动的迹象。
李斯心下稍安,随王绾入宫,嬴政降阶相迎。李斯见到嬴政,心中一阵激动,跪拜道:“待罪之臣李斯,不意能再见大王,感与惭并。”嬴政赶紧扶起,亲执李斯之手,引其就座。
嬴政道:“先生身处放逐,犹不忘寡人,惠书赐教,实寡人之幸。先生当知,逐客之令,牵连甚广,非寡人之独断也。”
李斯道:“臣也知此。尽逐外客,谁能得利?宗室和六国也。六国不能为此,则必宗室之意也。”李斯轻飘飘一句话,便将矛盾化大为小,化繁为简,将逐客令体现的国家意志转变为宗室的公报私仇。
嬴政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展开李斯的谏逐客书,道:“先生之书,寡人读之再三。其末有云,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又云,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再云,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先生似乎有未尽之意,隐约别有所指,不知是否?此殿中惟你我而已,愿闻先生之见,望先生畅所欲言。”
嬴政的语气,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在怂恿。李斯心想,事已至此,也只能撕破脸皮,正面攻击宗室了,毕竟是他们先把他逼上绝路,他必须反击。况且,李斯对宗室是曾有过大恩德在先的。想当年,宗室站在成峤一边,联手对抗嬴政。嬴政一怒之下,本欲对宗室痛下杀手,多亏了李斯的进谏,宗室不光得以保全,而且在成峤败亡之后,更受到嬴政的重用。而宗室居然要驱逐他,把他赶出秦国,这种以仇报恩、以怨报德的行径,让李斯齿冷和记恨。李斯对宗室的厌弃心结,从此产生,并为日后一个左右历史格局、改变历史进程的极重大事件埋下了伏笔。
李斯于是道:“古训有云,疏不间亲,贱不议贵。今蒙大王恩准,臣敢不昧死直言,惟大王采听。大王当不难想象,臣所将言者,非臣一己之见,实乃无数无辜遭逐外客之共欲言者。他们曾经为秦国效忠,并愿能继续为秦国效忠。”
嬴政道:“说下去。”
(中)
李斯道:“宗室所以驱逐外客,其争有三。其争之一,贵贱之争。宗室,贵族也,外客,多庶民也。轻贱布衣,贵族之惯习。宗室与外客同殿为臣,为外客所屈,内心未尝不引为耻,必愿逐之而后快也。然而,宗室之所愿,不能为大王之所欲。夫贵者,大王之臣也,庶民,亦大王之臣也。大王志在天下,当以德怀天下,如阳光雨露,遍施万物,无所偏颇。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即谓此也。
其争之二,公私之争。宗室,以社稷为私物,外客,愿社稷为公器。宗室以社稷为私物,故而必欲独享,恶与人共。然而,宗室之所愿,不能为大王之所欲。大王志在天下,当与天下大同,独私一家,非天子之道也。五帝三王,皆以天下为公,非一己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天下无敌也,即谓此也。
其争之三,宾主之争。宗室,以主人自居,视外客为宾,以为召之可来,挥之即去。然而,宗室之所愿,不能为大王之所欲。臣窃为秦危之,再为大王危之。何故也?今逐外客,外客归六国,一旦用事,必与秦为敌,六国皆怨而伐秦,秦危也。外客即去,宗室见重,用事莫非宗室,则大王仰赖宗室,非复宗室仰赖大王也。势柄倒移,尾大不掉,大王危也。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即谓此也。”
嬴政何等聪明之人,一点就通。秦国的政局变化,再没有比他更清楚的了。成峤谋反之后,宗室开始走上前台,掌握权力。当斯时也,嬴政也确实需要借助宗室的力量,对抗嫪毐和吕不韦。如今,嫪毐伏诛,吕不韦遣归河南,宗室再无对手,在朝中一枝独大。宗室的强大,自然也让嬴政深为忧虑。逐客令原非他的本意,而是迫于宗室的压力。
既然要攻击宗室,索性便恶人作到底。李斯又道:“宗室与外客,为臣之道迥异。臣请为大王言之。”
嬴政道:“先生请讲。”
李斯道:“宗室得与大王同根同祖,非大王所赐,天赐之也。即便换个秦王,他们还是宗室。故而宗室只忠嬴氏,不忠大王也。大王赏之,宗室以为份在应得,不能感恩。宗室血统,与生而来,夺之不去,大王罚之,不足为惧。大王利在有能而任官,宗室却可无能而得事;大王利在有劳而爵禄,宗室却可无功而富贵。宗室与大王,利害相去不啻千万里。而外客来秦,为大王而来,惟大王是从。大王于外客,赏之则喜,罚之则惧,令行禁止,莫敢不从。大王于宗室,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宗室与外客,为臣之道迥异,侍主之道迥异。大王不可不察。”
李斯一番激烈尖刻的言论,让嬴政闭目沉思。嬴政忘不了宗室在他面前的桀骜无状。他们更多地是将他看做是嬴氏家族的一员,年轻而稚嫩的一员,应该教诲,而不是听从,应该训勉,而不是尊敬。在宗室面前,他体会不到王的尊严和体面。
李斯不安地望着嬴政,不知是祸是福。良久,嬴政睁开眼睛,道:“逐客之令,虽为宗室提议,而定夺在寡人。宗室之臣,素有大功,寡人不忍责之。寡人将除逐客令,尽归外客,使其咸复故位,一如从前。先生也请官复原职。”
李斯知道,嬴政不是不忍削减宗室权力,而是风险太大,有所忌惮,时机也未成熟。宗室势力根深蒂固,不容小觑。废除逐客令对宗室已经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如果急着采取进一步行动,难保他们不强力反弹。
嬴政允许李斯官复原职,标志着在这次赌博中,李斯已经成功翻本。李斯却并不叩拜谢恩,而是说道:“吾王圣明。除逐客令,诚外客之幸也,亦社稷之福也。臣斗胆,请辞客卿。”
嬴政大感意外,道:“为何?”
李斯道:“宗室知道因臣之谏,大王乃除逐客令,必然不快,乃至暗暗怀愤。臣请辞客卿,一则示以所谏无关私心,只为秦国也,或有安抚宗室之效。二则事因臣而止,臣即去,也给宗室一个平衡。苟有利于大王,臣虽离无恨也。”说着说着,李斯仿佛也被自己感动。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何等的境界,何等的飘逸。在这一刻,即便嬴政并不挽留,任他离去,李斯也自觉可以神圣地无悔。
李斯感动了自己,却未能感动嬴政。嬴政只是平静地问道:“先生辞去客卿,何人可继先生之后?”
李斯答道:“客卿之位,何须再设,废之可以。一个客字,终有隔膜区分之意,示天下以宾主有分、内外有别也。今外客虽归,心中难免存疑不信,受怕担惊。大王宜安其心,固其志。自今日起,再无外客之说,皆一视秦人也。”
嬴政叹道:“先生识见高远,顾虑周全。寡人谨受教,敢不从命。”嬴政召入尚书令,吩咐拟诏。嬴政口述道:李斯来秦,九年有余;辅佐朕躬,尽智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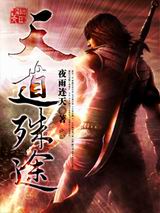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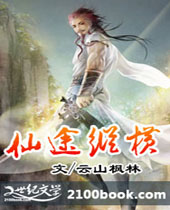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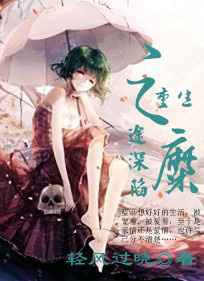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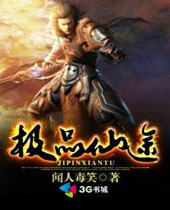
![逆袭之一品仙途[重生]封面](http://www.nstxt.com/cover/1/133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