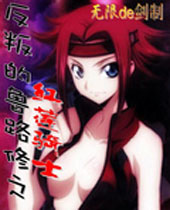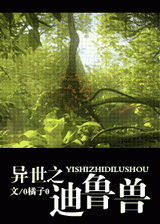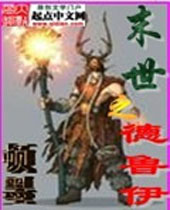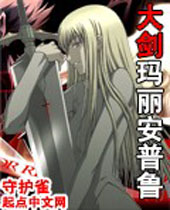花边文学_鲁迅-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飞”里,也没有“一片一片”的意思,这不过特地弄得累坠,掉着要大众语丢脸的枪花。
白话并非文言的直译,大众语也并非文言或白话的直译。在江浙,倘要说出“大雪纷飞”的意思来,是并不用“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的,大抵用“凶”,“猛”或“厉害”,来形容这下雪的样子。倘要“对证古本”,则《水浒传》里的一句“那雪正下得紧”,就是接近现代的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
一个人从学校跳到社会的上层,思想和言语,都一步一步的和大众离开,那当然是“势所不免”的事。不过他倘不是从小就是公子哥儿,曾经多少和“下等人”有些相关,那么,回心一想,一定可以记得他们有许多赛过文言文或白话文的好话。如果自造一点丑恶,来证明他的敌对的不行,那只是他从隐蔽之处挖出来的自己的丑恶,不能使大众羞,只能使大众笑。大众虽然智识没有读书人的高,但他们对于胡说的人们,却有一个谥法:绣花枕头。这意义,也许只有乡下人能懂的了,因为穷人塞在枕头里面的,不是鸭绒:是稻草。
八月二十二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华日报·动向》。
(2)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孤桐,湖南长沙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任北洋军阀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一九三一年起,他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曾为陈独秀、彭述之等案担任辩护。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申报》刊载他的《国民党与国家》一文,谈及保障“民权”问题。关于“二桃杀三士”,见他的《评新文化运动》(原载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上海《新闻报》,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北京《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曾重载)一文:“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按“二桃杀三士”的典故出自《晏子春秋》,这里“士”应作武士讲,章士钊误解为读书人。鲁迅曾先后发表《“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载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北京《晨报副刊》)、《再来一次》(载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两篇文章,指出他的错误。
(3)李焰生当时反动刊物《新垒》月刊的主编。他提出所谓“国民语”以反对大众语,这里所引的话见他发表于《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八月)的《由大众语文文学到国民语文文学》一文。他所说的静珍的文章,指《新垒》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四年七月)刊载的《文言白话及其繁简》一文,其中说:“文言文往往只有几个字而包涵很多意思,……譬如文言文的‘大雪纷飞’,这已经简化到一种成语了,见到这四个字马上会起一种严寒中凛然的感觉,而译作白话文‘大雪纷纷的下着’,那一种严寒中凛然的感觉无形中就淡漠了许多。”
“京派”与“海派”
栾廷石
自从北平某先生在某报上有扬“京派”而抑“海派”之言,颇引起了一番议论。最先是上海某先生在某杂志上的不平,且引别一某先生的陈言,以为作者的籍贯,与作品并无关系,要给北平某先生一个打击。(2)其实,这是不足以服北平某先生之心的。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兰芳(3)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4),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稳”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5)之感。“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6),前年大难临头,北平的学者们所想援以掩护自己的是古文化,而惟一大事,则是古物的南迁,(7)这不是自己彻底的说明了北平所有的是什么了吗?
但北平究竟还有古物,且有古书,且有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我希望着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文艺上的大著作。
一月三十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申报·自由谈》。(2)北平某先生指沈从文,湖南凤凰人,作家。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八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九期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一些文人对文学创作缺乏“认真严肃”的作风,说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元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上海某先生,指苏汶(杜衡)。他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上海《现代》月刊第四卷第二期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为上海文人进行辩解,对“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表示不满,文中还提到:“仿佛记得鲁迅先生说过,连个人的极偶然而且往往不由自主的姓名和籍贯,都似乎也可以构成罪状而被人所讥笑,嘲讽。”此后,沈从文又发表《论“海派”》等文,曹聚仁等也参加这一争论。
(3)梅兰芳(1894—1961)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表演艺术家。一九三○年梅兰芳在美国演出时,美国波摩那大学及南加州大学曾授与他文学博士的荣誉学位。
(4)“居移气,养移体”语见《孟子·尽心》。(5)“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语出宋代庄季裕《鸡肋编》:“建炎后俚语,有见当时之事者:如……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
(6)“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参看本卷第13页注(5)。
(7)关于北平学者以古文化掩护自己和古物南迁,参看本卷第13页注(6)、(2)。
“莎士比亚
苗挺
严复提起过“狭斯丕尔”(2),一提便完;梁启超(3)说过“莎士比亚”,也不见有人注意;田汉(4)译了这人的一点作品,现在似乎不大流行了。到今年,可又有些“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起来,不但杜衡先生由他的作品证明了群众的盲目(5),连拜服约翰生博士的教授也来译马克斯“牛克斯”的断片(6)。为什么呢?将何为呢?
而且听说,连苏俄也要排演原本“莎士比亚”剧了。
不演还可,一要演,却就给施蛰存先生看出了“丑态”——
“……苏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亚’,后来是‘改编莎士比亚’,现在呢,不是要在戏剧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亚’了吗?(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这种以政治方策运用之于文学的丑态,岂不令人齿冷!”
(《现代》五卷五期,施蛰存《我与文言文》。)
苏俄太远,演剧季的情形我还不了然,齿的冷暖,暂且听便罢。但梅兰芳和一个记者的谈话,登在《大晚报》的《火炬》上,却没有说要去演《贵妃醉酒》。
施先生自己说:“我自有生以来三十年,除幼稚无知的时代以外,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贯的。……”(同前)这当然非常之好。不过他所“言”的别人的“行”,却未必一致,或者是偶然也会不一致的,如《贵妃醉酒》,便是目前的好例。
其实梅兰芳还没有动身,施蛰存先生却已经指定他要在“无产阶级”面前赤膊洗澡。这么一来,他们岂但“逐渐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余毒’”(7)而已呢,也要沾染中国的国粹了。他们的文学青年,将来要描写宫殿的时候,会在“《文选》与《庄子》”里寻“词汇”(8)也未可料的。
但是,做《贵妃醉酒》固然使施先生“齿冷”,不做一下来凑趣,也使豫言家倒霉。两面都要不舒服,所以施先生又自己说:“在文艺上,我一向是个孤独的人,我何敢多撄众怒?”(同前)
末一句是客气话,赞成施先生的其实并不少,要不然,能堂而皇之的在杂志上发表吗?——这“孤独”是很有价值的。九月二十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2)“狭斯丕尔”即莎士比亚。严复《天演论·导言十六·进微》:“词人狭斯丕尔之所写生,方今之人,不仅声音笑貌同也,凡相攻相感不相得之情,又无以异。”
(3)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学者,清末维新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著有《饮冰室文集》。他在《小说零简·新罗马传奇·楔子》中说:“因此老夫想著拉了两位忘年朋友,一个系英国的索士比亚,一个便是法国的福禄特尔,同去瞧听一回。”(4)田汉(1898—1968)字寿昌,湖南长沙人,戏剧家,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人之一。他翻译的莎士比亚的《哈孟雷待》,《柔密欧与朱丽叶》两剧,分别于一九二二年、一九二四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5)见杜衡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六月)发表的《莎剧凯撒传中所表现的群众》。参看本书《又是“莎士比亚”》。(6)拜服约翰生博士的教授指梁实秋,当时任青岛大学教授。他曾在北京《学文》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四年五月)发表译文《莎士比亚论金钱》,是根据英国《Adelphi》杂志一九三三年十月号登载的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货币》一段翻译的。约翰生(S.Johnson,1709—1784),英国作家、文学批评家。梁实秋曾著《约翰生》一书(一九三四年一月出版),并多次推崇约翰生,如在《文艺批评论》一书中说他是“有眼光的哲学家”、“伟大的批评家”。马克斯“牛克斯”,是国民党政客吴稚晖谩骂马克思主义的话。
(7)施蛰存在《我与文言文》中说:“五年计划逐渐成功,革命时代的狂气逐渐消散,无产阶级逐渐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余毒’,再回头来读读旧时代的文学作品,才知道它们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意思的东西。于是,为了文饰以前的愚蠢的谬误起见,巧妙地想出了‘文学的遗产’这个名词来作为承认旧时代文学的‘理论的根据’。”(8)“《文选》与《庄子》”里寻“词汇”参看本卷第450页注(6)。
“小童挡驾
宓子章
近五六年来的外国电影,是先给我们看了一通洋侠客的勇敢,于是而野蛮人的陋劣,又于是而洋小姐的曲线美。但是,眼界是要大起来的,终于几条腿不够了,于是一大丛;又不够了,于是赤条条。这就是“裸体运动大写真”(2),虽然是正正堂堂的“人体美与健康美的表现”,然而又是“小童挡驾”的,他们不配看这些“美”。
为什么呢?宣传上有这样的文字——“一个绝顶聪明的孩子说:她们怎不回过身子儿来呢?”“一位十足严正的爸爸说:怪不得戏院对孩子们要挡驾了!”
这当然只是文学家虚拟的妙文,因为这影片是一开始就标榜着“小童挡驾”的,他们无从看见。但假使真给他们去看了,他们就会这样的质问吗?我想,也许会的。然而这质问的意思,恐怕和张生(3)唱的“咍,怎不回过脸儿来”完全两样,其实倒在电影中人的态度的不自然,使他觉得奇怪。中国的儿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