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一个 文章合集_韩寒-第4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惜老马家的门锁着,除了他自己,也没人有钥匙。
老马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发朋友圈,写道:一个人装起来的跑步机,我只能说是碉堡了'酷' '酷' '酷'
销售部的刘美丽又是秒赞,老马甚至怀疑此人除了睡觉和洗澡以外都在刷朋友圈。一大堆的评论大都是表扬和吐槽,最后一条来自老马妈妈:又浪费钱。
那个下午,精疲力尽的老马赤裸着上身,斜靠在沙发上睡着了,呼噜声好像风铃,做了一个不寂寞的梦。
梦里老马喝醉了,酒醒后躺在温暖的被窝里,穿着崭新的睡衣。
老马急忙跑去窗边,看见车完好无损地停在楼下的路边。老马又跑去厕所,看见马桶白得像雪。老马又跑去阳台,干净的衬衫飘在空中,有柠檬的香味。再回头,老马看见一杯温水,喝下去甜得发腻。
然后老马出门了,却不用锁门。
老马开着车,身体里流动着一种他一辈子都不曾感受过的温暖。然后他像儿时骑车一样高兴的放开了双手,大声喊道:晚上喝粥吧!我去买米!
轰隆!老马的车迎风飞起,撞上一对正在接吻的海鸥,落进大海。
老马在海里像鱼一样吐出来一个气泡,又跟着那个气泡飘上了天空。
那个气泡越来越远,他用尽了吃奶的力气终于靠近,伸出了手指。
“啵”的一声,气泡爆了,老马奋力吸了一口气。
“原来老子他妈的没有口臭!哈哈哈哈哈哈!”
老马就这样狂笑着飞向太阳,最终化为灰烬。
然后他听见有人哭了,哭得很动听。
虽然在梦里死了,但老马觉得很值得。
可惜,醒来以后老马依然赤裸着上身,依然斜靠在熟悉的沙发上,他感到身体发热,似乎是着了凉。
老马忽然挂念起“因寂寞而等你的猛男”,有些后悔把他拉黑,老马默默地想着,也不知道这小子现在怎么样了。
平安夜,公司聚餐吃饭,老马很是激动,把自己拾掇得跟要结婚一样,绑上h字头的皮带,还喷了香水。
老马人模狗样的好衣服不少,却常常找不到穿它们的理由。
席间,老马第一次很仔细地观察销售部的刘美丽,发现姑娘虽然和微信头像差距很大,但笑起来也还挺好看,老马想搭个话,谁知道刘美丽先惊叫起来:老马你这皮带不错啊!爱马仕啊!
老马心里得意,假装尴尬地摸了摸镶钻的h字母,笑着说:见笑见笑,什么爱马仕啊,海尔的!
刘美丽咯吱咯吱地笑了起来。
刘美丽刚刚进公司的时候就觉得老马是个很搞笑的人,那时大家一起吃火锅,问老马的香油碟里为什么不放蒜泥,这家伙竟然义正词严地回答:因为单身的缘故。
熊德启,电视台导演。微博id:熊德启
WWW。xiAosHuoTXT。
VOL。480 异团圆
t…xt小说天堂
作者淡豹
在与我一起成长的众多小伙伴中,味蕾最大胆好客。它和我共同冒险,去我幼年时未曾闻其名的奇异之地,迎接辣的芒果和带有大西洋北角寒冷清冽海水咸中淡甜滋味的生蚝。它感受敏锐,激发我的想象,它对新事物的兴趣和接纳能力一次次令我惊讶。
但味蕾也最可靠、老派、诚实。我能用大脑说服视觉,把不够可爱的景色看出几分赏心悦目,就像我在密歇根湖畔度过几年后,也能对自己说此地似乎宜于居住。可是我骗不了味蕾。
味蕾迅捷地依赖直觉判断,总领先理智。它反应快,执拗,铭铸的记忆深且持久,使我想起家乡沈阳时首先想念五岁时第一次独自出门,去院子拐角处杂货店买到的一种叫蜜桃精的果粉。
橡皮大小的一塑料包粉紫色粉末香甜强烈,比真正的桃子还要迷人许多,以至于后来在语文课本上遭遇“叹为观止”这个词时,我一次次回忆起那袋充满人工香精的零食给我幼年味蕾的震荡,香气涌动于舌尖〃噼啪〃作响,天空如同口腔在那一刻骤然密布绛紫的闪电,强大感官刺激瞬间重组对世界的体验,蜜桃的明艳滋味刻进从杂货店走回单元楼那几十米田字格的人行道,令回家的路神秘动人。幼小的我茫然再生。
爸爸的味道是热巧克力的味道。小时候他在英国,我不知他的模样,不过当家中收到大罐巧克力粉,三大勺巧克力粉叹息一般沉进滚烫的热牛奶,搅动原本自以为平滑的心灵表面,满屋就升起一种不可遏制的温柔。到如今,我仍习惯用碗喝热巧克力,捧起来味蕾就带动整个身体舒展,微麻香甜的烫就柔软了窗外穿不透的夜空和它覆盖下隔开我与汉语的漫漫太平洋。
童年东北家乡的冬天是酸菜发酵的香。临近年根,八纬路24号院的居民把楼道里深褐透绿的缸上压的青石搬走,从缸里捞出腌的酸菜,用来炖排骨、白肉。除夕那晚端上桌的锅菜,要炖许久直到入味。就像姥姥为过年蒸的面制生肖动物得提早用红枣捏出眼睛,定型蒸好摆上家里每一个窗台,就像酱牛肉和肘子得焖在锅里七轮才滋味丰满。我深呼吸告诫自己不要着急。味蕾在哀叹中激动,说服童年的我将有奇妙的美味报答我的等待。
我曾经以为,长大就意味着味蕾吐故纳新,馋不再主宰身体。自从停止长高,我不再如青春期每天吃食堂时那样坐立不安地长久渴望食物。新的异域吃食只令我心智好奇,对味道本身逐渐兴趣阑珊。
馋渐渐消失,直到我远离家乡和丰盛熟悉的食物。
在他乡,我才意识到,对食物失去兴趣其实是种特权。身处异国之初,当那种烧心的馋不期然光临我,我还为味蕾复归生动而心喜。一天天过去,馋开始不定期发起猛烈突袭,我丢兵弃甲,焦躁不止。
那种馋并不是饿,它专属对中国食物的想念,寿司和西餐菜谱平靖不了它的进攻。舌头着火,味蕾任最高统帅下达命令,我抓心挠肝,揪紧被角,在向往中说服自己睡去,要修道士一般自我克制,战俘一般放弃渴望。可抵抗总是徒劳,味蕾硬要随我前往味觉激活的嘈杂梦境。想象中我是大厨,梦是滚烫炒锅骤蒙凉油,哧啦出一室喧闹微醺的热香,亲人相聚,盘盏皆暖。有一些凌晨我醒于怅惘,哭成一个渣状的傻逼,月色明朗如水泻在我被子四角的牢房,让我期待追回糖浆一样香腻流淌的记忆。
两年前一个回不了家的大年三十,我在芝加哥逐渐丧失了耐心。美式中餐和牛排都不能再宽慰我的味蕾,它近乎疯狂地提出一个简单却神圣的要求,我只能臣服。它想要的是一碗热汤面,就是以前家人总会在年三十那天中午做的那种阳春面,简简单单的素面,正好梳理年夜饭前的肠胃。面里有青菜安顿过年前总是兴致高涨期待厚味的胃口,有宽汤慰劳早早就为除夕和响亮鞭炮而激动不安的身体。
那年大年三十是一月下旬。芝加哥尚未从冰雹中复原就又蒙新雪,全城白雪覆盖,从我住的高楼阳台望出去,街道上的零星旅人缩小成抽象的点,行走于风中方向难辨似布朗运动。街上的皑皑白雪与海一般宽阔的湖面结成的无边际的冰似乎反射出来自太平洋另一边的光芒,把我的眼睛刺得焦躁不安。那个中午,这件事非理性地生死攸关——我非得冒雪出门,去找碗像汤面的食物不可。
就这样,大年三十中午,我到了唐人街,点了一碗越南牛肉粉。年前唐人街异常安静,多数餐馆歇业,等次日春节当天的舞狮游行。这里是牌楼遍布的所谓“华埠”,店铺大多由老移民开设,沿袭闽粤港台与东南亚华人的春节风俗,让来自北方的我陌生。
是意外出现的东北话,使我的耳朵一下子立了起来。隔壁桌来了个中年女人,用我熟悉的辽沈口音要了菜单,坐立不安地望窗外,看电话,翻菜谱。过会儿有个年轻一些的女人带个四五岁小女孩来了。
中年女人问,甜甜能融入美国社会吗?
年轻女人拍小女孩,要她回答。
女孩扭来扭去,深陷于座位中,摆弄餐具玩。
年轻女人替她说,还是有差距。小孩儿,不用担心,适应得快。
中年女人对小女孩说:甜甜,你要向美国小朋友介绍咱们中国的文化。
两个女人给小女孩点了炸春卷,她们吃牛肉粉。我也慢慢吃我的越南牛肉粉。清汤滚热,豆芽另盛,现扔进碗烫熟,每勺汤不能舀太多,薄盖勺底儿几口气吹凉,等几口,汤就浸出薄荷叶的味道。有熟牛肉、牛腩片、牛百叶、牛筋丁。熟牛肉重,往往被河粉压住,藏在汤底。汤面上漂着的是有点松散的米色牛筋丁和白百叶,一个韧,一个黏。要等吃一会儿,汤略凉之后甜香都透尽了,展出一股淡淡的令人饱腹的油味时,深色的牛肉片和牛腩片再渐渐翻出来。
中年女人接电话,对面的男人想必叫彼得。她讲不顺英文,说:彼得,达令,我和妹妹吃饭,吃完饭买东西,下午见,我也爱你,彼得,再见,达令。
她冲对面的年轻女人和小女孩笑着。讲得慢,语法生硬,吐字格外清楚。
中年女人问年轻女人,钱够用吗。
年轻女人说,花销大,孩子去小朋友家里玩要带礼物。
中年女人拿出一个信封给她。
年轻女人对小女孩说,甜甜,快说谢谢。
中年女人对小女孩说,甜甜,回去了要懂事。
我始终没看出这个小女孩是她们二人谁的女儿。
去年二月,城中偏僻处开了一家据说颇地道的东北餐馆,就叫沈阳菜馆。我期待已久。除夕前那周,独自去吃饭。那时我已经习惯无法回家的春节,味蕾通常只激动了口味,而放过眼泪。
旁边一桌坐一对中国中年男女,点了些典型东北菜。吃饭时两个人背都弓着,下巴眼瞅着快碰到碗沿儿。话不多,漫漫讲着打工辛苦,国内亲人。
女人说沈阳家里老父亲病重,没法回去照顾,惦着,睡不着觉。
男人说分清主次,耐心等绿卡放下来。凡事在于心意,不在时间。
女人说累。
男人说来已经来了,别合计后悔的事。
女人问好吃吗。
男人说真香。
五彩大拉皮那么滑溜的菜,他们拨拉着非要用筷子帮对方弄进碗里去,芥末和麻酱拌匀的汤汁淋漓了小半个桌子。
快吃完,女人接了个电话。
男人说你老公到家了。
女人说你也该回去了。好好吃饭。等三十儿晚上,可得再吃回饺子。
男人说好好过年。
他们站起身来,我抬头。是牛肉粉店那个中年东北女人。她穿一件下摆收紧的绸面黑羽绒服,烫过的头发松散盘起来,盖住略带憔悴的脸。她取一张餐巾纸,替男人擦去袖口沾染的油渍。她是我熟悉的沈阳女人的样子,好像也未及中年。
女人走出一半,又回来,要了个打包盒,把剩的小半盘青椒猪肉水饺和三鲜水饺装起来。桌上和国内小餐馆那样,蓝格子台布上加垫了一层塑料布。女人把塑料布捋捋平,端起盘子,要整个倒进打包盒,大约是看到盘子上多余的汤汁,又放下,用筷子夹起饺子,一只只往盒子里搁。
男人从她肩上望过去。墙上的装饰画是小餐馆常挂的那种似照片翻印又似油画的廉价彩画,表面凹凸不平。绿草地上一幢两层的普通美式郊外住宅,家庭轿车停在街边,两只猎狗围邮筒嬉戏,一个孩子坐在长椅上扭头看向猎狗,举歪了手持的彩虹棒棒糖。
女人拉了一下男人,把剩饺子递给他。他们一前一后走出去。
世间团圆或有多种类型,就像世间的深情。而这些异团圆的指向大概殊途同归,就像与家人的电话里临沉默前的嘱托总是“好好吃饭”。我曾疑惑自己想念的究竟是什么,是家、是人、是国、是热闹、是语言?现在我想,我思念的是一种完整。中国人的团圆仪式总包括吃饭,幸福完满的节日无非寻常夫妻市井家庭,在除夕,坐下,吃顿团圆饭,远方人归来,吃饭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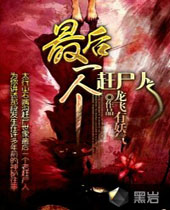
![[快穿]给我一个吻封面](http://www.nstxt.com/cover/0/72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