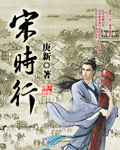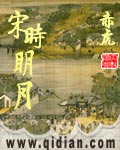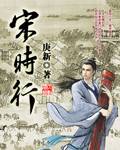宋时吴钩-第3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啥?”孟之经翻了半个身子,胳膊肘拐着地,抬着脑袋,瞅着公输念槐,“小兄当然知道现在还不是吃野味的最佳时候,不过,念槐,你说的也太亏心吧,怎么叫刚能够吃,我与张大哥也就风味鸡吃的比你稍微多了那么一点点,那四只獾呢,嘿嘿,想蒙混过关,小兄这里就没门。”
“嘿嘿,孟兄啊,若一个月后,草转黄时,这野鸡的味道那才是绝了呢,现在嘛,肉还有些柴,不够厚道。”
“我怎么听着这话味道不太对啊,起来了,走,看屯田去。不把你侍候舒服了,你啊,老弟,为兄就不说啥了啊。”
孟之经与张言蹲在小溪边净面洗手,捧着水往肚里灌。
“唉,你们干嘛,停。”公输念槐一歪头,看见两人正喝溪水呢,赶忙制止。
“咋了?”
公输念槐指了指溪水,“两位哥哥,就喝这水?”
两人一脸懵逼地互相看了看,同声问道,“咋了?”
“完了,完了,别去看屯田了,回去给两位哥哥烧大蒜吃去。不拉死一个是不算完啊。”
刚吃完烧烤就喝冷水,还是河水。即使这个时空里一点污染都没有,人的肚子似乎也很难承受。
更可虑的是这一带正闹疟疾呢,谁知道看着清清亮亮的溪水里,其实早已经溶了多少不洁的物质在里面。
“念槐,莫要危言耸听啊,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你没看到吗,出门时我们都不带水。”孟之经把捧在手里的水一仰脖子灌进肚里,不在乎地摇摇头。
“公输公子,孟公子说的是,您过虑了。”张言在一边帮腔。
“好了,以后为兄在你面前就不喝冷水了。还是看屯田吧,老弟若想要大蒜烧着吃,那里也是有的。”
公输念槐手指着两人,再说不出话来。空口白牙,没有凭据啊。难道自己真想用两人今晚上的拉稀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若是两人就是不拉呢?
算了,以后做出镜片来,就让他们看看,这看似清洁的水里到底有多少小虫子。
“这水清吧,这水亮吧,”公输念槐指着缓缓流动的溪水愤愤地说道,“但这水不洁。里面有很多小虫子。”
第四十四章 屯田这件事()
第四十四章屯田这件事
孟之经与张言似笑非笑地看着公输念槐指点着溪水,一点都不着急,等听到公输念槐说水里有很多小虫子时,张言蹲下身子捧起一捧来,凑到孟之经眼前,“公子,你看看这里面有没有小虫子。”
孟之经很正经地凑上去,瞪着大眼珠子一通踅摸,又很正经地摇摇头,“没有。”
公输念槐一甩手,转过身子朝牛车走去,“爱信不信,有你们后悔的一天。等我制出显微镜来,你们就知道这里面是多么的丰富了。哼。”
孟之经与张言嘻嘻哈哈地跟在公输念槐身后,孟之经还说呢,“念槐啊,若你能证明这水里真有小虫子,为兄必为你大张旗鼓。”
公输念槐一边走一边摇头,很多时候眼见并不为实啊。眼见的是现象,现象这词真好。现的象,象是什么,象是表象,是宏观世界的一部分。微观世界眼睛是看不到的,但它依然真实地存在。
还有就是人心,这东西只凭看还真看不透。不是有古话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嘛。还有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的诗句,可见,人心是更难看清的。眼见不为实,此之谓也。
公输念槐也不跟两人废话,一路走向牛车。老牛嚼着青草,听到动静,抬头看了一眼,哞的一声,算是跟走过来的人打了招呼。
“念槐,水里真有小虫子?”跟在身后的孟之经越想心里也越不踏实,追上来与公输念槐走个并肩。张言自去赶牛车。
“孟兄,那些得疟疾的人在哪里?他们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孟之经一听到疟疾,全身就一哆嗦,“念槐,喝冷水会得疟疾?他们在工地上,平时就住在那里。不过得疟疾的人已经隔离了。”
“孟兄啊,怎么说呢,还是到工地上看看吧。小弟好奇的很,现在还不是农闲的时候,怎么就屯上田了呢?”
孟之经抬起胳膊,四下里一比划,“念槐,这一片土地很大,老弟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这里河汊纵横,土肥草茂,不仅要屯田,还要养马。如果能训练出一支骑兵来,何惧金兵骚扰。即使如老弟所担忧的,蒙古人来了,我枣阳军也有得一战。”
“养马?”公输念槐四下里望了望,养马这玩意儿似乎很奢侈,至少后世里他看到的养马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当然当驮马或者耕田来用一点问题都没有,要是作为骑兵的战马,这应该另当别论了。至于枣阳这一带能不能养马,公输念槐不是专业人士,不敢妄加评测。
对于有了战马之后,能否就有了与蒙古人作战的能力,这得分开来说。还是那句话,一两件武器不是决定战争走向的决定性因素。
“哈哈,小弟从不怀疑孟家军的战力与作战意志。可惜啊,孟兄,孟家军只是大宋作战体系中的一小环啊。”
“嘿,嘿嘿,念槐老弟,至于别的环节如何小兄作不得主,凡是有我孟家父子在的地方,必不会让外族肆虐猖獗。”
公输念槐这一点是赞同的,从他的老上司孟辉所言,不管有没有溢美之辞,至少这个孟珙减缓了南宋这艘大船下沉的速度。
而且孟珙去世之后,他的属下王坚去了四川,钓鱼城之战直接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还有一个余玠,与孟珙交好,在去四川之前,孟珙还接济了余玠好多粮草,噢,对了,就是眼前的这个孟之经,还亲自带兵去四川辅佐了余玠一段时间。
余玠现在出世了吗,与孟珙是怎样建立起关系的呢?
公输念槐忍了再忍,终于没有问出这个问题。如果连孟之经也不知道这个人,自己贸贸然问起来,虽不至于让人产生什么联想,总也是件不好解释的麻烦事。
一车三人在绿野丛中踽踽而行,与这片土地比起来,一车三人比一棵草也大不了哪里去,却能把草踩在脚下。
三人一路走来,不时把拦路的石头踢向半空,撵得蝴蝶差点儿扇断了翅膀。穴居的动物或者探出头来侧耳细听,或者撅着屁股准备一窜入洞。
两条腿的从未把四条腿的放在眼里。强大与否看来与腿的多少并不成正比。
路转景移,忽而一转,眼前出现一座木桥,正搭在南长水上。
公输念槐看了看村庄方向,树遮岭拦,竟然挡住了视线,实际距离估计下也就十里左右。
公输念槐与孟之经两人并肩走上桥头,桥不宽,勉强能让两辆牛车交错而过。桥面是用原木一剖两半拼接而成。下面承载的都是粗大的原木搭成的桥架子。
粗大的木桩深深地扎进河床里,支撑起整个桥面。河水流经木桩时,激起了水涡,分成两股绕过木桩后又合成一股,向下游流去。隐有轰轰之声。
过了这座木桥,就是南长水的北岸。
放眼望去,跟南岸有了不同。水洼处处,阳光打在水面上,映出白亮亮的光。眼见着田畴渐少,草茂蒿深。
视线内的土地估摸着能开垦出十数万亩土地,算起来一年就能增加二三十万石粮食,养活五六万人一点压力也没有。
如果真如孟之经所说,这一带曾经就是一片农田,只是后来无人耕种荒弃了下来,那么这些土地就是熟地,把地面上的荒草清理出来,稍稍平整一下,就能下种种出粮食来。如果再早上两个月左右,现在看到的就不是蒿草,而是绿油油的庄稼了。
看样子,一是时间,二是人口,限制了对荒地的开垦整理。
“孟兄,这一片土地要开垦出来,需要的人数不会少吧,总也要万人才能完成。”公输念槐踅摸了一会儿,仍然没有看到人头涌动,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的场面。
“需要的农夫何止万人啊。河道要疏浚,高地要引水,这些水泊子还要围堰造田,哪一项都不是小工程。今冬明春才是**。这一些完成之后,水多的就种水稻,水少的就种小麦与杂粮,明年的这个时候,就不是眼前风吹草低的样子了。”
公输念槐弯身摘了一朵野花,放在手里搓,一松手,野花蔫蔫地跌落下来,孟之经的话从他右耳进左耳出,并不放在心上。公输念槐并不怀疑孟之经的热情,也不怀疑这些宋人的信心。
做事情光靠热情与信心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支撑热情与信心的手段与资源。
在全靠人力畜力的时代,兴修水利,开垦荒田不是小工程,没有庞大的人力物力投入是很难想像的,当然还要有科学的规划与组织。哪一项准备不充分,都会事倍而功半。
“念槐,从此再往北,还有几十里的土地等着我们去开垦。眼前的这一片只是沧海中一粟耳。”
“嗯,没有十年八年是开垦不完的。”公输念槐的嘴又管不住了,毒水又往外喷了。
“孟兄别瞪眼,听小弟说道说道。噢,容小弟先问孟兄个问题,孟兄考虑清楚了再回答,小弟不急着要答案。为何要屯田,谁来屯田,谁来怎样保护屯田?”
“哈哈,念槐,为兄这就给你答案。屯田可以积聚粮草,充实边防,还可招募流民用来屯田,两个问题了啊。至于谁来保护屯田,这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当然是我忠顺军了。怎么样,为兄的回答可满意否?”
公输念槐嘴里叨着一朵野花,斜睨了洋洋自得的孟之经一眼,轻哼一声,“若答案如此简单,小弟会拿出来请教孟兄吗?小弟浅陋,可也不敢辱没了孟兄的见识啊。”
孟之经有些发怔,“昔日我爷爷屯田时,也想过这样的问题吗?”孟之经凌乱了,连孟宗政都搬了出来。不过也说明他在思考,比较孟起宗政的屯田与当下屯田的异同来。
能比较就好,比较就能发现问题。
“孟爷爷屯田时,宋金战争还在进行吧?现在呢,宋金战争早已结束四五年了,这四五年的时间里为何没人来组织屯田呢,否则好好的良田也不会成了现在荒草绿野的地步。小弟想问一下,屯田之策出于何人之手?因何要选在这个时间点上,不会又想占便宜吧。”
公输念槐隐隐觉着这次屯田有什么蹊跷,他不是质疑屯田这件事,而是为何偏偏是在此时此刻进行这件事。
做好事,还分什么时间地点?这是善良的人的想法。但推动屯田的人就不是正常的人,或者说不能单纯以善良不善良来简单划分。
“嘿嘿,念槐想多了。时势异也,不能相提并论。看,快到了。怎么没见到我爹他们,王叔叔也不在。”
公输念槐暗叹,孟之经显然已经明白了些什么,不说就不说吧。自己也不是想要知道什么,只是对这样的权谋有些不齿罢了。
不过,对推动屯田的人还不得不赞叹他对时局的精准把握。去年夏国被蒙古人攻灭,金国与蒙古人在北方开始了全方位的对抗。而南宋方面来自北方的防御压力一下子轻松了下来。
不管金人胜还是蒙古人胜,对南宋来说,都与自己无关。而且还可以坐山观虎斗,顺便把荒废多少年的屯田捡起来,达到巩固边防,减轻内地运送军粮的压力的目的,不得不说这根针还真就插到了缝上。
第四十五章 金点子()
第四十五章金点子
不管从朝堂还是到地方,都是良政,想反对都找不出理由来。这一手玩的确实漂亮,时机把握的精准,屯田这个点选的更是高明。
绕过一个水泊子,爬上一处土坡,眼前是一个村子样的营地。说是村子,格局是按村子的样子布置的,说是营地,是因为这里没有一所正儿八经地房子。
几座用木棍随便搭起来的木屋,就能被称作建筑,算是比较齐整的房子了。房顶上铺着一层茅草,除了地面五面透风,现在这个季节住着,倒是挺凉快的,若是下雨,恐怕比站在雨里直接挨浇还难受。
更多的是一些帐蓬,只是这些帐篷让人看着心酸,补丁打着补丁,布料原来的颜色早就看不出来了。
几条狗儿趴在阴凉里打盹,还有蹒跚着的孩童在帐蓬间出没,偶尔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探头探脑,比公输念槐在非洲看到的难民营还不堪。粗略算来,这处营地住个**百人应该不成问题。
“这就是屯田点儿?”公输念槐指了指眼前的营地,他怎也想不到条件会是如此简陋。
“嗯,这是其中之一,往北往西,还有几处。”孟之经说着话从土坡上走下来,“每一处水泊子处,都立了这样的营地,为的就是取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