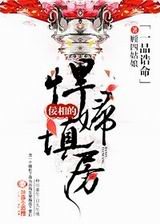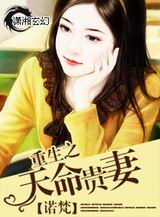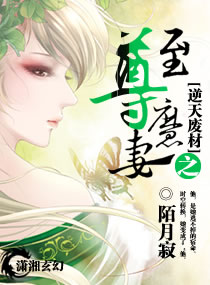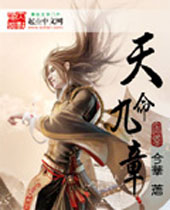正统天命-第9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所以说,哪怕是李唐那会儿,给自己家找了个有名儿的祖宗李耳,在长按修了个号称天下最豪华的道观,自己立了道教做为国教,也一直没放松对道教的监视,没有放弃平衡佛道势力的努力,玄奘法师西行取经回来之后声望一时无两,背后或多或少也有朝廷的推手,为的就是让佛道两家达到一种平衡,否则真的按照当时的律法,特么的玄奘法师是个偷渡客,回来肯定是要追责的。
至于本朝,要不是明太祖朱元璋也需要一个合理的马甲让自己这个泥腿子出身、当过和尚的穷酸登上皇位,只怕依着脾性,早就把宗教平灭了,奈何道教风流是在太久了,民间的影响力绝不是封建小农经济基础支撑下的政权能够轻易拔除的,所以他也只能仗着穷横,把道教挂起来,尽可能地隔绝他们对底层的影响。
这样的势力,能利用就利用一下,走的太近了绝对没什么好处,他现在又不是没有靠山,也用不着天师府方面的倾力支持,大家互利互惠也就好了。
这个话题聊到这里,也就算是告一段落了,杨尚荆话锋一转,就把话题引导了这次出行上面:“如今戬带人乘船,一路南下,却不知这金乡卫到底有什么根底,需要注意些什么,却也是无奈之举啊,还请劳烦忠叔,将徐总旗、刘断事二人找来,和戬说说话,戬也好心里有些准备。”
忠叔应了一声,退了下去,杨尚荆则看着涛涛江水,叹了口气。
大明朝后期形成的文贵武贱的局面,也不是没原因的,毕竟相比于文官而言,武将有点儿不值钱了,先不提光是浙江沿海就十九个卫所,十九个正三品的指挥使了,单单是一代代人积累下来的功勋,就足以早就一群“蒙荫不干活”,或者是“辱没祖宗”的勋贵子弟了,顶着正二品的官职,赶着正三品、甚至是正五品的活儿,简直不要太多,就这个局面,怎么和一帮子通过科举考上来的人对刚?
然而勋贵集团偏生还是握着枪杆子的,想要动他们的利益,就要问问他们手里的枪杆子同不同意,所以哪怕到了后期,文官势力大增,最顶级的那一撮勋贵,依旧有着极其强大的话语权,就算不能说一不二,一些声音也是朝堂上必须要参考的。
第二二一章 用人之道()
二二一章
金乡卫在洪武二十二年动工建造,耗时三年,本身就是一座坚城,按照大明朝的勋贵体系而言,它本来是姓汤的,信国公汤和在告老辞官之后,奉命建造的。
不过呢,老朱这个人疑心病挺重的,所以姓汤的负责营造,用人就肯定不能再让汤和那个派系的勋贵得利了,于是在营造成功之后,直接派了常家一系的人去兼领指挥使一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简单的分权制衡,常遇春虽然死的早,然而早年因为太能打了,死后一串儿荣誉衔儿砸下来,什么“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追封开平王,谥号忠武,配享太庙”之类的,还是给老常家保留了相当多的派系力量,用以制衡汤家、蓝家等等开国老臣的。
等到了朱棣靖难成功之后,这个地儿又换了主人。
虽然朱棣自问对勋贵系统还是有绝对的领导能力的,然而朱允炆不知所踪,所以他也不能就装着逼啥都不干,这万一朱允炆跑到哪个南方卫所,扇乎一下鼓动一下,直接带着一批人马犯了,多少是个麻烦不是?所以在继承大统之后,直接给天下卫所来了一次大换血,北军南下、南军北上的不要太多,金乡卫又是个倭寇屡犯的紧要的地界,所以就直接用上了徐家的人。
不过当时呢,朱棣和魏国公一系的关系僵得很,当时的魏国公徐辉祖还在家幽闭呢,所以用的实际上是已死的徐增寿这个左都督的人,而且这么多年来,因为徐增寿追封了定国公,原本左都督一系的武将也就没作鸟兽散,这金乡卫的指挥使,实际上也一直都是北京定国公徐氏的人。
杨尚荆主管备倭衙门的开始到现在,时间已经是着实不短了,这金乡卫的指挥使姓邵名飞字天举,也是个人精,为了往上爬着方便,和北京方面的联系一直都不少,所以早就接到了消息,还没等杨尚荆的仪仗入城,早早地就在城外五里的地方候着了。
等看见杨尚荆左青龙、右白虎,嗯,也就是左边徐尚庸、右边刘启道地来到了面前,这邵飞邵天举目光连闪,连忙迎了上去:“末将金乡卫指挥使邵飞,见过钦差。”
这话说的很有艺术,让人很是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哪怕对比起兵部郎中来,指挥使显得很不值钱,但是吧,从品秩上来说,指挥使是正三品,郎中只是正五品,所以想要跪舔杨尚荆,就得找一个很新奇的角度了,而很显然,诸位邵飞邵天举,就很有这方面的天赋。
杨尚荆的正五品郎中只是官衔,而他的使命,则是“总督浙江宁波、台州、温州三府备倭事宜”,算得上是钦差了,正三品的指挥使跪舔正五品的郎中不行,但是跪舔钦差,那就是本分了,所以邵飞这一声“末将”放在这个语境下面,简直就是恰如其分。
所以杨尚荆的眼睛就是一亮,连忙走上前去,伸手扶住他,哈哈笑道:“邵指挥切勿多礼,邵指挥镇守一方,劳苦功高,如今非但要防备海上倭寇,便是闽、浙交界之地的流民、贼寇,也要严加防备,出兵剿除,本官如何当得起指挥之礼?”
邵飞的神色就是一松,特么的,这年月钦差下来,就没有几个是不来找茬的,就算这杨尚荆和勋贵走得近了些,就算北京方面也没说他会拿自己开刀,但特么正统元年轩輗下来督军的时候,谁能想到人家一家伙砍下来四十多个脑袋?不过看着杨尚荆现在这个状态,就算是找人借个脑袋立威,也不会找到自己的头上。
所以他伸手做了个“请”的手势,也跟着笑道:“杨钦差,里面请,里面请。”
两人翻身上了马,带着人向着金乡卫城中走去,要不说这邵飞尺度拿捏的非常之好么,哪怕他认出了徐尚庸和刘启道这两个南京勋贵子弟,知道徐尚庸是魏国公家的公子、而且很可能是要重点培养的子弟,也没上前打个招呼什么的,不显得有一丝一毫的阿谀谄媚。
“正如钦差所言,盖因今年浙江水患严重,江河满溢,一茬秋粮几乎全都泡在了水里,不说是颗粒无收,却也是饥馑之年,如今这浙南的流民暴增,都想着往南方跑,去投奔那边的逆贼叶宗留,末将在这金乡卫,确是要海上防着倭寇,路上防着流民。”邵飞一边拍马向前,一边感慨道,“所幸江口、三冠、仙口等巡检司用命,堵截流民,使之不能成了规模,否则唉。”
杨尚荆脸上就露出了玩味的笑容,你丫的这是在和我哭穷啊,就怕我削了你的兵权,把你手上得力的人手全都调走,去了备倭衙门吧?而且之前这话是我说的,你再确认一下,正好给了我一个实锤,我总不能自己打了自己的脸吧?特么的人精就是人精啊,你这个智商扔在朝堂上面当个文官,不说碾压六部郎中吧,就翰林院的那个张丛,你能把十个他吊起来打。
所以他微微一笑,接过了话头:“邵指挥此言不假,本官身上还兼着黄岩县县令的差事,这民间的疾苦,自然也是知晓一些的,邵指挥如今的困窘,本官也是知道的,故此这次前来,也是帮邵指挥出个主意,顺便整饬一下金乡卫的兵备。”
这话说的,前轻后重,我是来帮你的,也是来整饬军备的,你要是不用我帮忙,那我就只能干后面儿的活儿了,这么大一个金乡卫,你呆了这么多年了,别说你肯定有问题,就是没问题,一通儿审计下来,你也得有问题了,到时候别怪我学着轩輗轩臬台,直接给你捅一刀子。
听了这话,邵飞就咧了咧嘴,扬天打了个哈哈:“杨钦差在黄岩县力拒倭寇,连战连捷之事,如今整个浙江都已知晓了,有钦差帮末将管束军队,区区倭寇流民,自然是不在话下。”
第二二二章 “自己的聪明人”(补更)()
第二二二章
杨尚荆这软刀子扎下来,邵飞也只能咧咧嘴,自认倒霉了,他也知道,杨尚荆这个钦差如果想要有所作为、弄出点儿功绩的话,肯定是要从各个卫所抽调人手的,而且是精锐人手,毕竟一个正五品的郎中,他是没职权从卫所防守地域这个层面上进行重塑,以此来奠定自己的功绩的。
毕竟沿海这几个卫所的防守范围、包括防守策略,是户部侍郎焦宏定下里的,那是正三品的高官,外朝的一个大山头,很有可能凭借着备倭的功绩和名头混上兵部、甚至是吏部尚书的,莫说杨尚荆没有那个职权,就是有,也不敢轻动。
大队人马入了城,杨尚荆这边的兵丁满打满算也就两百人出头,被安置在了城中大仓桥附近,金乡卫这城池修筑很讲究,按照的是刘伯温修筑南京紫禁城时候用的法子,叫“八卦乾坤”的布局,除了正常的城池四门之外,还设有四个水门,正好应了“休伤杜景、生死惊开”八门,城池里面的布局大抵就和迷魂阵仿佛,大仓桥、小仓桥是城市中心,也是粮草重地,把钦差的兵丁放在这里,也算是一种对杨尚荆、或者是对皇权的尊重了。
“这邵飞有点儿意思。”洗了把脸、涑了涑口的杨尚荆抻了个懒腰,整个人精神了不少的杨尚荆多少有点儿感慨。
跟在他身边的徐尚庸点点头,脸上全是玩味的神色:“末将从家中外出之前,大人特意提点过这浙江诸多卫所的指挥使,其中这邵飞邵天举,却是着重说过的。”
杨尚荆眉头一挑,脸上浮现出好奇的神色:“却不知魏国公如何点评此人?”
能够以一介指挥使的身份,进入镇守南京的魏国公的眼中,本就说明此人不一般,魏国公还专门给下过评语,这就更不一般了——虽然当代魏国公的老子是个混不吝,当代魏国公本人也是没甚么可以大书特书的,但是能坐到这个位置上,多少都是有几把刷子的,看看当年和老魏国公徐钦一起瞎混,被言官弹劾了的成国公朱勇,现在都特么执掌京营了,杨尚荆还能等闲视之了?
“此人虽是蒙荫得职,却也非寻常纨绔,单论自知之明,却也是蒙荫武将之中少有的。”徐尚庸说的很是慎重。
“国公可曾说过此人的甚么事体?”杨尚荆眯着眼睛问道。
人贵有自知之明,单单一个自知之明,就足以让杨尚荆打起精神来面对了。
徐尚庸略一犹豫,还是说道:“正统六年,常家想抬举他做个福建都指挥同知,被他婉拒了。”
特么的正统六年正统六年那会儿,为了朝局稳定,直接把北京定为京师,南京改为陪都了,所以从实际意义上来说那也是潮剧嘴不稳的时候了,江南虽然不说人心思变,但也是勾起了另一轮的站队,文官系统还好些,毕竟真正的大佬就是陪在皇帝身边的那一批,可是勋贵体系不一样啊,太祖开国、太宗靖难造就出来的两批勋贵,大大小小的山头林立,镇守南京的、随驾北上的、戍守各地的,多了去了。
太宗驾崩那会儿,仁宗打算迁都回南京,就把北京又定了行在,当时勋贵体系里面就是一阵混乱的站队,各级都司、指挥使乃至下面的守御千户所,说是洗了一次牌都不夸张,所以当北京再次被定都的时候,南方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在这种时候,能够看清楚事情,继续抱着定国公徐家的大腿不放,这就本身就是一种定力,他知道到底谁的大腿比较粗,而不是因为眼前的一丁点儿利益,就放弃了真正的大粗腿。
常家虽然很牛掰,但是和定国公徐家比起来,还是差了那么一丢丢的,最起码圣眷方面,徐家就不是常家能比的,毕竟徐家一门二国公也就不说了,常家也不差,但是朱棣的老婆、仁宗的老妈、宣宗的奶奶,她是徐家的人,就因为这个,徐辉祖在朱棣进了南京城之后都没死成,徐增寿一系更是时时有奉上。
再加上魏国公一系世镇南京,平白就要比同在南京的常家高出不少来,两个徐家合在一起,执掌京营的成国公一系都要靠边站,也就英国公张辅能仗着资历掰掰腕子。——虽然有脑子的都知道,分了家之后的南北两徐肯定不能完全一体同心了,但是在涉及到整体利益的时候,南北二宗还是要联合起来的。
邵飞邵天举作为一个正三品的指挥使,那时候改换门庭,实际上就是把一整个金乡卫扔给了老常家,因为常家把他调走高升,肯定是有后手让自家人接任这个位置的,虽然说这在大明的朝堂上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