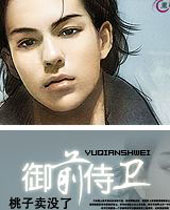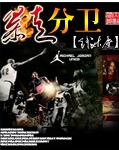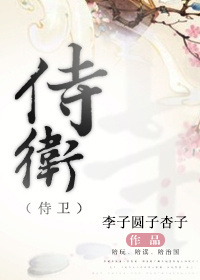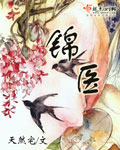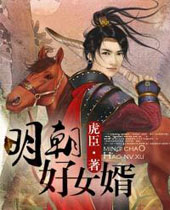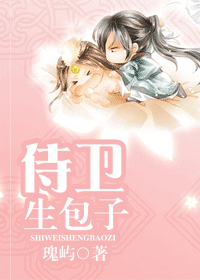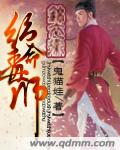明朝锦医卫-第14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热,看了几个郎中,都说可能不好了,后来经人介绍才来了白记药铺,一剂小剂量的青霉素下去,没几天,这位街坊的小儿子便活蹦乱跳了。
如今,这位街坊不管拿什么药,有事没事都要来这白记药铺转一趟,有时候甚至根本不是来买药,就是为了给张阳送点土特产,因为跟张阳同样姓张,这位张大妈又听说张阳初到大明,举目无亲,简直就要把张阳当做本家的小辈儿一样对待了,这会儿一听说张阳吃了官司,哪能不着急?
“还不是前几天那个,那个什么自称白家表少爷的人,痴心妄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要娶白姑娘,发现白家根本不拾他这茬儿,竟然失心疯一样,告到衙门去了。县老爷他也糊涂,这样的明摆着的事儿,便将那浪荡子打发了便了了,还要过堂,真是!嘛,药铺的人现在也都去了,就在静海县衙门,我这也准备去看看呢,要是县老爷判得不公,我们可不答应。”那妇人的嘴很快,仿佛一顶机关枪,还没等人听清她说了什么,话都已经说完了。
“一起去,一起去。”听完妇人的说辞,张大妈马上拉着那妇人一起往静海县的衙门口赶去。
白记药铺到静海县的县衙并不远,基本都算不上出城,就沿着运河往南走,一会儿的功夫便到了。
在如今大明朝,静海县东西长220里,南北宽120里,东至渤海170里,西至顺天府文安县界50里,西南至青县界60里,北至顺天府武清县60里。
后世天津市中心的大、小直沽,津南区的咸水沽及东丽区军粮城,在这时均属静海县。
天津有句老话“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
也就是说,天津卫的前身,其实就是静海县,再加上南运河从静海县穿过,大小漕船连绵不绝,也让静海县的沿河两岸繁华不已,虽说是一个县,却基本更像是天津城一部分。
到了破旧的静海县县衙门口,县衙门口的大街上已经挤满了人,原本从白记药铺往这边走的时候,还只有几个街坊一起,可一边走,一边一传十十传百,不一会儿,似乎整个南城的人都知道了张阳要在静海县过堂的事儿,有些人是为了给张阳打抱不平,给他助威;有些人则纯粹觉得此事新鲜,要去看个热闹。
大明自太祖朱元璋开国以来,一直是允许百姓们到衙门旁观官员审案的,一是为了防止官员徇私枉法乱判案,其二也算是一种普法教育,效果倒是不错。
再加上,朱元璋时期颁布的大诰中,明确命令百姓们“互相知丁”。要求市井村镇中的老百姓对自己的邻居,一定要做到“互知业务”,也就是知道他们平日里从事何种职业;还要做到知道邻居家里几口人,几个人从事农业,几个人读书,几个人从事手工业或者商业;对于读书的邻居,一定要知道他的老师是谁,在哪里上学;给别人做老师的,也必须知道他所教的学生都是谁。
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大明的社会彻底变成“熟人社会”,这样大家知根知底,就可以有效地减少作奸犯科的情况。
虽然,自朱元璋之后,大诰基本就跟某国如今的宪法一般形同虚设,然而在朱元璋那会儿,大诰就跟红宝书一般,基本上是人手一本,各级各部门还要经常性地组织学习、宣讲大诰的精神,并且还是学子们除了四书五经之外的必修课。
所以,即便是到了如今,大诰在大明社会中的影响也是无处不在,就拿这会儿来说,恰恰是因为邻里街坊们全都是熟人,所以原本只是几个人去看张阳过堂,而这会儿,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天津卫的市民要上街游行呢!
只是因为有着官不修衙的传统,静海县的县衙毕竟简陋狭小,根本容不下这么多人,衙门的皂隶们只能大声安抚民众,有限地放入了一些年老德昭的人进了衙门,而剩下的则大多都等在衙门外面
甚至就这一会儿的功夫,一些心思灵活的小商贩,已经推着货车开始在人群中叫卖了,几个小孩儿凑在一起,也开始跑跳打闹,一时之间,静海县的县衙外面仿佛开了庙会一般,好不热闹。
静海县的县衙前有照壁一道,照壁后为牌坊,牌坊上有匾额题“忠廉坊”。
牌坊以里为大门,大门两边的墙呈“八”字形,所谓“八字衙门朝南开”。
八字墙上可张贴告示、榜文,公布科举考试录取结果等。
牌坊以里,设有医学、阴阳学,右侧设有总铺(急递铺),以便于县衙公文的快速递送。
牌坊正北为鼓楼,为两层,是县衙中最高的建筑,便于报时和瞭望。
鼓楼外墙左右,分别建有申明亭、旌善亭。就是张贴有各项政策实施公告,案子判决结果和对于贞洁烈妇、好人好事的表彰等内容的地方。
静海县的县衙不大,进入鼓楼,便算是正式进了县衙,过楼之后,过了仪门即是县衙的核心建筑——大堂。
而这会儿,张阳、杨慎、唐伯虎,连同静海县的县令大人和他的师爷正一起坐在大堂之后的二堂,堂上一匾,上书“省观堂”。
这个二堂是个面积很小的房子,不过是大堂和三堂之间的一个穿堂,不过好在私密性不错,适合临时待客,商议一些机密事情。
“张大人,下官听说那原告许宜找了王世杰来帮讼,这王世杰是个落地的秀才,本身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可是却凭着对大明律的熟知,再加上他牙尖嘴利,是天津卫有名的讼棍,惯是会胡搅蛮缠,即便没有道理也让他给赖出三分。一会儿过堂,张大人可要小心,莫要着了他的道儿。”静海县的县令老爷依然坐在张阳的下首。
“多谢县令大人相告,张某省得,不过这次张某请来为我帮讼的人,可是江南第一才子,难道还会怕了那个什么王世杰不成?”张阳转过头笑着对唐伯虎说,“倒是让唐兄大才小用了啊。”
“哈哈,唐某我虽然也算读过几遍大明律,可是这上堂为人帮讼的事情,以前还真是没有做过,这一次第一次上堂,倒是怕给张小兄弟你弄出什么纰漏来。”张阳不怎么懂大明律,原本他是准备找杨慎帮忙的,可是生**凑热闹的唐伯虎倒是自告奋勇了,看唐伯虎如此热衷,张阳自然也不好打击他积极性
“唐解元的大才海内皆知,下官自然也是久仰已久,只是各位都是谦谦君子,那王世杰确实鄙陋小人”静海县县令跟那王世杰确实打过一些交道,深知此人刁钻,还是有些担心。
“不妨事,不妨事,这种简单明了的小案子,凭那王世杰还能翻过天去不成?!县令老爷,我看时辰也差不多了,赶紧升堂审案吧,之后,唐某还与我这两个小兄弟相约吃酒呢,可不要耽误了。”唐伯虎摆了摆手,一脸的不在意。
“啪!”
“原告许宜何在?!”
公堂之上,惊堂木声响起,静海县县令坐在大案后面,沉声喊道,而三班衙役则拿着水火棍肃立在大堂两侧。
“回禀,老父母,在下便是原告许宜!”许宜因为有生员身份,站在堂下并没有下跪,这会儿的许宜可不是之前那副潦倒的样子,已经换了一身儿崭新的长衫,之前面上的菜色也少了许多,倒是让人看着顺眼不少。
而站在许宜身旁,一个圆脸儿,身材不高,唇上有两撇山羊胡的死胖子,就是那个讼棍王世杰。
“许宜,你递上来的状纸,本官昨日已经看过,你告白家一女二聘,告张阳强夺人妻,只是你的一面之词,可有何证据呈上?”静海县县令坐在堂上大声询问。
“回禀老父母,原本生员来天津卫时,曾随身携带一封书信,是我那姨母,也就是白芷的母亲亲笔所写,上面记有两家所立之婚约”许宜低着头向静海县县令说道。
“如此,速将书信呈上。”静海县县令点了点头说道。
“只是这封书信,被那张阳狡计骗去,扔入河中”许宜有些吞吞吐吐地说道。
“那就是没有婚书了?那原告你可有媒人作保,证明两家婚约?”静海县县令继续问道。
“这这个因为两家订婚之时,我与白芷表妹年纪尚幼,是以并无媒人作保”许宜继续回答。
“放肆!既无婚书,又无保人,你的父母又已不在人世,单凭你一面之词,如何证明两家曾有婚姻之约?!左右,将那许宜给本官架出”静海县县令一阵恼火,这堂下的许宜什么证据都没有就来告状,难道是专程来给自己添乱的?要知道张阳他们这会儿可还在候着等待过堂呢。
“大人!听生员说完,虽然生员既无聘书,也无保人,却曾给了白家聘财!那物贵重,想必还留在白家,大人若不信可找来白家人对峙!”许宜大声说道。
“大明律明令,凡男女定婚之初,务要两家明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凡招婿须凭媒妁,明立婚书,如今你既无婚书也无媒妁,还有什么可说的,不要在此胡搅蛮缠了!左右,还不”静海县县令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且慢!父母老大人,虽然大明律中要求男女双方订婚要有婚书媒妁,可父母老大人,您莫不是忘了,在大明律里还有一条: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笞五十,其女归本夫,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亦是。既然,许宜他能证明白家受了许家的聘财,父母老大人为何不传那白家父女上堂对质?!”旁边王世杰终于发话,声音语调不紧不慢,却让人觉得很不受用。
两次被打断的静海县县令很不爽,但是偏偏这王世杰却找到理上。“如此,便传白家父女到堂!”静海县县令揉了揉眉头,大声发令。
190章 利嘴()
“堂下所跪之人可是被告白安和白芷?”静海县县令拍了一下惊堂木,大声问道。
“草民正是!”白安与白芷跪在堂下回到,白安没有功名,白芷也没有正式嫁给张阳,并没有命妇身份,因此仍然见官要跪,而唐伯虎则有些云淡风轻地站在一旁。
至于张阳,他毕竟有五品的品衔,若是普通的小民随便告他,不管是否有理,都要先挨上30板子,而许宜因为身有生员的功名,可以免除这顿板子,也不代表,张阳就要抛头露面,当堂与他对质,以失了身份,所以这会儿张阳还坐在二堂,听着前面的动静。
“罢了,你等二人起身回话。”虽然白芷还没有嫁给张阳,不过这事情也算是板上钉钉,静海县县令也不敢过分得罪。
“谢县令大人。”白芷扶着自己的父亲站了起来,然后冷冷地看了旁边的许宜一眼,要不是这人前来告状,自己的老父亲又哪里会遭这样的罪。
“白安,原告许宜曾说,你曾受其财礼,将女儿聘嫁于他,可有此事啊?”静海县县令拿腔拿调地询问白安。
“回县令大人的话,此事草民尚是第一次听说,草民一家与那许宜家中断了来往已有十几年,何曾受过他家的财礼?!还请县令大人明鉴!”白安低头拱手回话说。
“许宜,白安说并不曾受你财礼,你怎么说?!”静海县县令又转头向许宜询问。
“回禀县令大人,可否让学生询问我那姨丈几句?”许宜不慌不忙地回答,待到静海县县令点头,便转过身来,向白安行了一礼,而白安只是冷哼了一声,不过许宜显然并不以为意,“白姨丈,我们还是初次见面,没想到却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实在是令人尴尬我只想问白姨丈,你家可有一枚半月形状的青绿色玉佩?上面刻着云纹。”
突然被许宜这么一问,白安和白芷也是一愣,白安更是脱口而出:“你怎么知道我家有此一枚玉佩?”
听到白安如此说,许宜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转头又对静海县县令说:“大人,白安承认有一块半月形的玉佩,那块儿玉佩正是我母亲所给白家作为订婚财礼的,既然此玉佩还在白家,那么”
“哼哼,笑话!天下有半月形玉佩的人多了去了,难道只要有人有这样一块玉佩就是你的媳妇儿?”唐伯虎啪地一合扇子,冷笑地打断了许宜的话。
“唐解元所言甚是,许宜,你若没有证据,不要胡搅蛮缠!”静海县县令附和着唐伯虎说道,这静海县县令同意过堂审这件案子,已经是给汪平和的面子了,可不代表他还要帮着汪平和判冤案,得罪那张阳。
“回县令大人话,学生若是没有证据,哪敢来此胡搅蛮缠,之前学生所说的那块半月形玉佩原本其实一块圆形玉佩所斩成的二块中的其中一块,而这另一块儿玉佩,恰恰就在我身上,不知县令大人可否令那白安拿出玉佩,与我身上这块玉佩相和,若是能严丝合缝的对上,那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