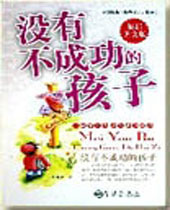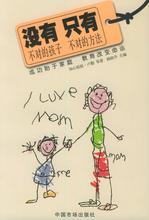����������-��1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ߣ����ɣ�����绰�ǵ�ʱ����߲��Ա�����õ�һ֧ר�ߣ������Ϳ��ڽ���״���´�Ϊ�����ҪԱ�ļ��е绰������շתֱ����ϵ�����˽�������ȻТ�²���Ը�������е绰�����Լ���ר�߸�Ǯ���������С���ϣ����Կ���Т����ʱ�������ˡ�
�������ҡ�Т�ϸ硱
����һ�Ű�������Ρ��⽻��������γ�֮�ᣬ��Т�µĽ����������࣬�ұ����ı��ֿ����Ǵ�ʹ���ı�̬�ȵ�ԭ�����ڡ��⽻�����Ĺ����ձ��ܵ����ڿ϶���һ���γ�����������ҾͲ����Ǽ���ǰ��������ѹ�ƻ��ż����ˡ��Һ�Т������ҵ�ϸ�û���κ�������ͻ�����ǽ��ر��ֵ��ڡ��⽻��������Ŭ���������������̽緢չ�������Ϻ�ˮ������ˮ��Ҳ����������ɣ��������������ˡ�
һ�Ű���������Т�������������˹�˾���ĺ�������٣�Ҳ����Ǯ������������ͻȻת�������롰��ʽ��������硱������������ҵ�Ȼ˵�ã���������ϲ��Ҳ�н���������ʮ�������������ٳ������Һ�Т�£������ʰ�·���κͰ����õ�ס��һ�������ͣ����Dz�����ʽ����ʽ������Т�½��ҡ�Т�ϸ硱�����ٵ����кã�˵�����ˣ����Ҿٱ������Ǿ��ơ�
�����Ұ������������������ס�Т�Ⱥ���Т�ǣ�����Ҳ���ܸ��ˡ���Т�������������ң������������ת���˸��ף���������ЦЦ���ͷ����Ȼû˵ʲ�ᣬ��Ȼ����졣��Т��˵������Т��������������Ȳ�û����ʾ�����������������Կ���Т�µ�����ˡ�
���ǣ�����ʮ�꣬һ�ž��������ң�����û�ϵ���������ֵļ���仯��Т��ȴ���ҽ��н�Զ��ʵʼ����δ�������뵱���ġ����ֲͻᡱ��������ڼ���ǰ�ŷ���һ�������ֵ��ܵ��龰��������Ŀ��Т��ȴ�������š�һ�κò������һ��������飬ȴ�����������Ť����˺�÷��飬�����������̾��
�����������������
Т���ڸ����������죨Ԫ��ʮ���գ����һ����ᣬ�ʹ�绰��Т�£�Ҫ�������Һ�Т��ȥ����հ�����ݵ��¡�Т���ڵ���Լ�Ҽ��档�����ĵ������ϵ������ʰ�·��¥�İ칫�ң���û���������㼱��˵�����������·�����̫ͻȻ�ˣ�����ȥ����֪�����Һ�Т���Dz���Ҫȥ����������һ�棿��˵�Ѻ�Т��̸�����������ã�������˵��û�����⣬ֻ�ǵ��첻�У�����Ҫ��һ���졣��˵�������İ��ţ�ͬʱ�������й�ʮ���շ����¹ʵľ��������������ĵ���������̸���У����ó�����ҽ��С��Ĵ��÷�ʽҲ�൱���½⡣���꣬�����������ң����װ���ص���ѡ���ڴȺ��Աߣ�������ͷ弡��ĵط������Ҷ����µ���ʮ�շ��ȡ�Т�����ۺ��ף��Եú�ƣ��;�ɥ�����Һܸ��Ե�˵����������ǰ�������ǵ��¸��߹��ң����Ҷ���е����������Т�ȵ��£��Ϸ���Ҳ���á���
���⣬Т�����컹¶��һ��������������Ϥ��ʮ����Ҫ���¡���˵��������ǰ������������ϣ��������������ǻ���ɢ���ؼ��ɣ�Т����Ϊ����������Իء�����˵�ⲻ�Ǹ��˵��£����в��ˣ���������ĬȻδ�����ơ�
����ȷ�����������뷨��ֻ��Т�¸��˾��ò��ף���δ�հ졣����Т��춶�������������淽��Ůʿ������ĸ�������ᣬ���Ԫ�¶�ʮ����ȥ����������������������Ҫ���游����������ָɽʱ���Ұ�Т�����ᵽ������ǰ�л���֮����¸�����Т�գ��������������µĴ������н����ӵ��˽⡣��ʱ�������֮�飬����̫�㣬Ҳ����Ϊʱ̫�������ұ��벻�ܻ�ؽ��˾�ʵ���������ù����˽⸸�����������Լ����µĴ���������ǰ���н����ģ����л���������ۡ�
���绽�겻��
Т�±�Т��С���꣬����С���꣬�Һ���ϧһ�žš���ǰ��������������ദ�����¡�һ�žš��꣬���ԡ������ᡱ��������ǰ�����ô���ʣ��ص�ǰ��������һ�ˣ��DZ߹��ĺ������С����ԱҲ�����Ҿ�ϵ���ȣ�����Ŀ������ȥ̽��Т�²���ο��ο������ʱ���Ѿټ����������ޡ�
���ڲμ�һ��������ϵ����ң����ڽ���ɽ��һ���൱�����Ķ����������棬���Եúܸ��ˣ������Կ��Ź��á���ɽר�õļ��ճ����ܵ���������ҵ�һ��ɽ��ȥ���������ȫ�ǵĵƻ�ҹ������ȷ�൱׳�۶�����ɫ����ʮ������ص����ң�����������̫̫������Ҳ�������㣬����ĵúܿ��ģ�������������Զר��ȥ̽�����DZ�ʾ��л��
����Т��˵���ľ�����ƽ����������һ�ۿ���������������ȥ�����꣬�����ij����˿��δ��������һ�������ϼ��ȵĴ��ˣ������ؿ̻�����������Ƥ����Ѫ˿��˫�ۺ��������ݵ������ϡ��ҹ��ĵ��������Dz���˯�߲��ã�����ȴ�ǰ�����˺ܶࣿ����Ц˵�����������˯�úã���
����������£���Т����˵��Զ�ȶ�Т�����ø������ʡ�һ�Ű������Т�伴Զ�����⣬�������ڸ������ԣ���Т��������Ӱ���롢��������ڲ࣬����С���������롣�ʾ���������Ȼ�뿪��������ʧ���Ѻ����ġ���Ҫ��Եģ�������һ����Ȼ��ͬ�ں����������һ��������������κ�ֻ����ʵ����ᡣ���ռ������Ժ�ˮ�ɱ���ħ����һϦ֮����ʧ���������������־�䣬�����κδ�����ͬ��λ���ϵ������ܳ��ܵ��˵ġ����ԣ��������������ҵIJ�������Ҳ�������½���ĵ�Ȼ��֮��
����������������һ��
��ʼ�պܸ�лТ�ºܳ���ذ����Һ�Т�ȼ����˸�������һ�档
Ԫ��ʮ��������һ�㣬Т������˵������ʮһ�����ᵽ������˹��·���εġ��⽻���γ������ᣬ�����Һ�Т��ǰ�����ڻ����õ������������漴֪ͨТ�ȡ�����ʮ���Т���ȵ���ʮ����ʮ�˷�Т��Ҳ���ˡ�ʮһ�㣬�Һ�Т�ȴ��Т�µij�������ҹĻ�������֪�������������ֱ�����ܡ�
�Һ�Т�Ƚ��������ã�������ǰ�����Ϲ����ڳ����м�λ�����ߺ������������飻���ᣬТ�´����ǽ���ΧĻ���ᣬ�����ܵ�ͣʬ����䡣Т���ȹ��£���һλ���ֽ�����һ�����м�ı���������������Ͱ�Ȼ�������С����߽�ע��֮��������ò��Ϊ���꣬˫Ŀ���գ�˫���ܺϣ�Ӧ���Ѿ���������������Ψͷ���Լ����ɣ���ɫ�Ұף�����˯״�����漴����ߵͷ���������£�Т����������ǰ������һ�棬���¹�ߵͷ�������������������Ȼ���Һ�Т����ƽ��һ�����������غ��Լ������棡
�ұ�����ߵ����غ��š��ְ֡����⾹����ʮ���������״ε��Ÿ��������������ְ֡��ְ֡�������������Ը��ĵ�һ�������������������ij���������ֻ���Լ����õ����������߸��ף���������Ϣ��������һ����ú�Ŭ�����ְ֣�����ģ��밲Ϣ�������ҿ�����ˮһ�ε����ڵ��ϣ������ı��ң�Ī��Ϊ���ˣ�Т�������������й�ݡ����ᣬ��������һ���ؽ��������ϣ�ǰ��Լ�����ӡ�
��ȥ��ˮ��Т���������˳����ã���������л���ǡ�Т�����ɳ��ֱ��Һ�Т���ͻؼң���һ�ж����������½��С��ܼ�����������һ�棬�������ӡ�
������������������
һ�Ű˰���Ԫ��ʮ���գ���������ĵ����������ʱ��������Т�ȵ���Т��Ժ���칫�ҡ���Ժ���Ȱ�ο����˵����ͳ������������̫����Ҳ̫�죬Ҫ���ǽڰ�����˵�Ѿ�֪����ȥ����������Т�䡢Т�º����ǽӴ���������ҹ����ȥ���ܻ����ü���������һ������Ρ���Ҳ�Ѿ����������ŵ�ʱ����������˶�Ҫ����������Т����˵������ͬ��
���⣬�������ص�˵���ھ�������������ڶ��죬Ҳ����ʮ�������磬Т�����Լݳ�����һͬ��ͷ弣��������������ȵ��Ǵ�������ǰ��ʱǰ����Ϣ���ĺ�Ժ����춳���ֻ���������ˣ�̸���������մ�δ�����Ļ��⣬��;�������ڸ���Т��˵���������һ������Ҫ�����㣬���ڡ���ͳ���Ѿ����ڣ�Ӧ����ʱ���ˡ�����ͳ����ǰ����棬ҪТ�ϡ�Т�����ֵܹ��ڡ�����ͳ��˵�⻰����һ�����ǰ���������Ҳ�������������Ժ�������ᡮԺ����������һ��������ʾ�˽⣬����˵��Т�ϡ�Т�ȶ������Լ��ijɾͣ�����ҪЭ�����ǡ�����Т�ǰ�ο����˵�����ӹ�ϵ�������ģ����ܷ�������ι��ڣ���������Ȼ����ʵ�վ�����ʵ��
������Т����һϯ̸�������ҿ�����ᵽ����������ľ������Һ�Т�ȵ���ʼ�շ������ϣ��������Ըһֱ�����ն�δ����ʵ����������ܶ��꣬�����룬������ж�Ρ���ͳ��ְ���ᣬ���DZȽϺõ�ʱ����Ҳ�Ƚ����װ��������������Ǹ���һ��������ܰ���龰�����⣬�Ͼ�ֻ���Լ�������
���ø�����ǰ����ȷ�Ľ��������Т˼�����Ե���η�κ����裬Ҫ����ȥ���������Ϊ��ģ�ֻ���Ұ����ף���ǰ��Ȼ���л������Ҫ�������κ�ǣ�ҡ�
��һ�����������������������֣����������Сѧ��
��С������������һ��������ʹӿα��̲��б������˲����游����ʱ�Ĺ����¼������Ҷ��游���ޱȾ�η���������ž���ίԱ��ίԱ������װ�գ�Ӣ�˻����������ҳ�ݵ�ż��Ȼ�������߲����ʣ�ңԶ���������ߵ����ǡ�
����ίԱ����������
һ����һ���������ж��Ź�С���꼶����һ�η�ѧ����Т�ȴ�ѧУ���Ŵ���½�������·�ؼң��м�λ�ϲ�������Χ�����³������������Һ�Т��ʱ������һλ����ɤ��ָ�����Ǻ����ܻ���£����������������Ǿ����Ͻ������ӣ���ίԱ�������ӣ����úÿɰ���һ��˫��̥����������ȫ��������ֻ��С�۾��ص�����һ�ۣ��ӿ�Ų��ؼҡ����ǡ���ίԱ�����⼸���֣��������Ǽ�ס�ˡ�
���Ƶ������ظ������������Σ����������ֹ������Ǿ���Ҫ�������š���������������ҹ������������ţ�˭�ǡ��Ͻ�����˭�ǡ���ίԱ�������������ǻ����������ӣ����ŵ�ʱ��һ�����������ѵĿ���˵��������Щ��ʲ����ڱ������ң��ܶ��˼����������ӵ�̨�壬ϲ����˵�˵�����Ҫ����Щ�˽��Ļ�����������������үү���ְ֡����裬�������衢�̵�һ����ӣ��������ӳ������������ϲ����¼���һ������û�е�̨�壬���ǼҸ�ʲ�ᡮ��ίԱ����������й�ϵ�����Ҫ������ɵ�£���Ҫ����Щ�ˣ����ڶ��������Ų����Ƿ�ѧ���پ����Ǹ���壬Ҫ������ѧУǰ����һ����Զ��·�ؼң��ܿ���Щ�ϱ��ǵ�ָָ��㡣������������Щ�ϱ��ƺ����Է������ǵĹ��¡�
��ξ����ǵ�һ�����ˣ���������ǰģģ�������ᵽ�ͽ�����ij�ֹ�������Ȼ�й��ɻ�һ���Ӿ��ˣ��Ͼ����ף������ű�֯�Ĺ��º�������ı���������˹�ȥ�����ڻ����������治֪����ʱ���ű����ʵ��������ʱ����ʲ�����ĸ��ܣ�
������ͽ�ı�����
��Сѧ���꼶�����У�Ҳ���Ǵ�һ���ľŵ�һ�������⼸���������û���ƽ�ȣ�û���κ��쳣�������ŵ�ÿ��ı㵱���Լ���ѧ�õ��ľߣ�������ͬѧû�����������Ǵ�һ�����������ᣬ�Ҿ�ͻȻ�仵��һֱ��һ����������б�ҵ����û�к�ת����
�Ƕ��ڼ䣬��������������£������ҵ�Ψһ�ĵ�����Ʒ�����Ǽ�յ���ڷ��䵱��û�е��ֵĵ��������ķ��������ģ����������죬ȴ�����쳣���д��Һ�Т�ȵ��ھ�С���Ѽ�ȥ�棬�����������ת�����ü���������Ľ���ص���Ҳ�����ᣬ����֪��������������·�ķ�����ɹ�����Ŵ���Т�Ⱥ�����������˯��С���䣬��ͷ����������������������¯�����ȣ����Ͼ���ʱ�����ϵ���Ƭ�����ȵġ�����������ֻ��ȥ�ľߵ���ɫֽ�Ѵ��Ӻ�����������Ǭ���ÿ����ľɱ�ֽ���档
�������һ��������취����Ҫ�Һ�Т�ȷ�ѧ�ᣬ�������Ķ����г�ȥ���㷷������������������ı��˴��ש�ؼң�Ȼ���óɴ�С���ȵı���Ž����裬�������������ƶ�����Сʱ��������һЩ��ʣ�µı���ͷ��ڷ��м䣬���������ڻ������ϾͱȽϺ�˯Щ�����������У�Ӧ��û�еڶ��ң�����������Կ����˵ġ���������£����Կ����������ӵ���ࡣ
���������ʲ��С���ͽ�ıڡ��ˡ�����˯����һֱ�����˴�ѧ�������ã���������ʮ���꣬���������и�����������⣬�������춼Ҫ��������Ĵ������С������������������������ַ��ھ����ᶼ�������ţ�ס�ڸ��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