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聪明太多,悲悯太少,格将焉附?
素质隐藏在混沌之中
理查德·道金斯 《再创未来》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颜色最多的那盒蜡笔中藏着混沌的可能
“大众教育”主题图书一直是大众阅读热点,但其中很多“畅销书”不过是非教育专家的“客串”之作——它们当然并非一概糟糕,但我以为,关于“教育”,专家的声音更重要。
我们是一个积弱积贫的国家,有关教育,向来欠缺发达。建国至今,尽管全国成人文盲率已由80%下降至872%,但文盲绝对人数依然高达8500万。这不应该是一个被忽略的数字。在如此语境中,一套可靠的“专家指导”便有可能像一位不会离开、不会下岗、坚守职责的教师?
仅以“素质”教育论,多年来,这个“最强音”其实并不清晰——你以为会弹奏莫扎特《唐璜》就是高素质?你以为能对达利的那两撇怪异的胡子发表一孔之见就是懂艺术?好像并非那么简单。我一直以为:所谓“素质”,所指的是一个人的“综合竞争力”或说“综合魅力”——它是教育中的教育,犹如文学中的文学。它与所谓“基因”的复合与难言,好有一比。
言及“基因”,牛津大学学者、基因专家理查德·道金斯在《再创未来》一书中说:“你可以把基因比作食谱,你按照书上的食谱去做,然后从烤箱里取出来的是蛋糕,但是你无法把蛋糕捏碎,然后说这一小块是按食谱中的这几个字烤成的,那一小块是按食谱中的那几个字烤成的。没有‘烤蛋糕基因’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如果你改变了食谱中的一个词,烤出来的蛋糕会是另一种滋味——甜一点,油大一点,或者其他滋味,而不会只是其中一小块的滋味发生了改变”……
道金斯如上言论,其实最形象也最恰切阐明了“素质教育”概念中通常最容易被忽略的那一面——那就是,说到“素质”,一定综合、混沌、暧昧、难于拆分——而所谓“素质教育”,也刚好就是道金斯所言“食谱”上的那几个关键的字么?它也许是一个眼神?也许是一个嗔怪?也许是一句赞美?
画家、诗人席慕容曾说,如果可以,家长第一次给孩子买蜡笔时,要选颜色最多的一种——因为,那将是孩子对色彩世界的第一次体验。延伸席慕容的关照,在素质教育中,全是看似一片混沌的多多细节——第一是细节,第二、第三依旧是。
“磕药”后的恍惚
连岳 《来去自由》 四川人民出版社
当琐屑暴力、细末血腥相汇,会发生什么
书中最好看的,是“连城诀”一辑。如此赞美有可能被解释为该书的其它部分不好看……如你所知,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就个人偏爱而言,我最感兴趣的,是连岳文字中那些样貌轻扬、由诸如飘升感、陶醉感、忘我感之类混杂而成虚无感的那类文字。我把这个意思说给一个朋友听,他说,你的意思不就是“磕药”后的感觉?这个联想让我哑口无言。
开列在“连城诀”下计有文章60篇。那其实是并不靠色的60篇。其中《偷偷吃了食指》、《苹果上的梵文》、《每年空虚一次》、《憋尿》等二十来篇,我个人最喜欢。它们甚至让我再次与诸如“疏离”、“背叛”之类的情感范畴狭路相逢……原本都已是一些让我很陌生的冲动了。比如,看完《每年空虚一次》,我就想:我为什么要上班?
我上班的地方在一幢写字楼的第十二层。每个周末下班后,我都会乘电梯到位于该楼地下二层的游泳池去放松一下。因为那个游泳池小得不能再小,所以,在我嘴里,“游泳”被改称为“划水”,力避夸张。有好几次,我钻进电梯等待从十二层下降到地下二层,“划”走一周困顿,可奇怪的是,十多分钟过去,电梯却一动不动,稳稳当当停在原地……好安静啊。
如你所知,信号再灵敏的手机在电梯里也不灵。其实我一个人呆在电梯里也就十来分钟,可那十来分钟委实恐怖……在茫然惊恐的那个间隙里,我甚至连中国出版业的前世来生都想到了。那真是一个标准的现代化孤岛……太安静。
而在《来去自由》之《自私地飞向木星》一文中,连岳的经历与我截然相反——那天早上十点半,连岳在十二楼被十八楼的一个编辑叫去领稿费。电梯在那个时段最清闲不过。连岳按了按了向上按钮,十八楼键灯熄灭后,电梯却不停。更奇怪的是,电梯在十九楼也不停。楼层显示灯不一会儿就跳到了一百层。又过了一会儿,楼层显示键由原来的自然数变成了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冥王星。木星键亮着。顺应命运的安排,连岳自私地飞向木星……
引述如上两个细节,事实上不是要描述我与连岳的相似,而是相反——他向上,而我向下;他按动木星键钮,而我按动的是游泳池键钮;他要奔赴的是太空,而我需要潜入的则是那个脸盆大小的冲凉之地……正如我在网络各式论坛多年只潜水不发言只观望不结交后所得出的深刻体验一样:关于文字,关于汉语,如我之类语文工作者过于一相情愿的乐观都太夸张了。
在《人立在床头的蛇》一文中,连岳写:“我躺在床上。睡着了。外面下雨。被窝里是热的,而伸在外面的手微微有点凉意。明天不用早起。我像一枚好钢造的硬钉子,倦意则像一把手柄已被握得油亮的铁锤,把我敲进新鲜的、刚刚刨好的、厚软的松木中”(P184); 在《上帝规则,魔鬼规则》一文中,连岳写:“上帝先造蚊子,人睡不着,被咬得起包,整夜抓挠,他再接着创造蚊帐,人杀了一头公羊做燔祭感谢它……上帝的规则是:先给出痛苦,然后给出路;他在帐篷边和城市外面无所事事地游荡,魔鬼其实很无聊,在山上、平原上挖了成千上万个坑,人们就在报纸上谴责他。魔鬼只好连夜加班制造瘟疫,让坑起作用……魔鬼的规则是,制造麻烦,然后将之合理化”(P210);
在《如果我有四只翅膀》一文中,连岳写:“我要和叶芝一样,找个湖心小岛,养一箱蜜蜂,种九行豆角,在蜂鸣声中,睡个死去活来的午觉。我还要在湖中潜水,要潜一百五十米,在深水里打坐一会儿,仿佛处在虚空当中,我的肺缩小了十六倍,而耳朵敏锐了二十倍,听见深水鱼苍白地游弋,听见水草顺着几缕阳光向上攀爬”(P226)……
如是汉语,已多有令人“惊艳”之处。扼要说,在将王小波的松弛、卫斯理的奇幻、罗素的晓白、星爷的怪诞之类一古脑放到锅里垮炖三五年后,连岳端出了一块儿属于他自己的味道怪异的蛋糕:它是城市的,却有郊外青草之味,它是理工科的,但也有旧式文人细若游丝的精致;它洋溢着颓气、顽气、嚣张之气,却也弥漫着梦想与失落交错而成无数碎片之光……而如是斑驳,连岳下笔不过三下五除二……恭喜。
后来我才知道,我在电梯里那十来分钟惊心动魂,其实不过因为昏头昏脑忘了按动泳池键钮,它与连岳在文中所隐喻的现代人如影随形般的“恍惚”主题相距霄壤。说到“恍惚”,我以为它正是连岳“连城诀”辑中表达得最为出色的一个主题。他以散漫而真假莫辩的叙事,不怀好意地混淆着幻觉与真实、永恒与偶然的界限,并以寻常汉字导演出一幕幕藏匿于现代生活皱褶中无穷琐屑暴力、细末血腥……了得啊。
顺便说一句,读《来去自由》事实上无助于了解连岳本人,甚至完全相反。比如,在我阅读时的一个恍惚中,我见到连岳本人时便迟迟不肯上前与之握手寒暄——我担心的是他右手食指是否健在。我的疑问是,连岳右手食指第一节是否果真巧克力味、第二节是否果真草莓味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可能永远不开会?
往上爬不如向前进
廖筱君 《不怕改变》 圆神出版公司
往上爬不如向前进
在哲人喜欢探究的范畴中,“改变”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与熟人社会的迂缓与舒慢相比,今天陌生人社会已是每时每刻都处于“改变”之中。
关于专栏写作,我的“计划生育”做得很糟——我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码字的速度。比如,我的“改变”永远赶不上世界之变。与我合作很多编辑MM不断跳槽,我始终无缘与她们相见——她们总是在我最想与她们一起共进工作午餐的时候跳槽离岗,绝尘而去,却把作者我留在原地。
在这种心境中,读台湾新近畅销书《不怕改变》,深觉其主旨至少可能安慰与我类似的仓惶懦弱者:“很多时候,我们或许无法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却拥有改变自己的权利。千万不要怕改变,有改变才会有新契机,有改变才会知道自己的希望与极限,有改变才会体会到人生是自己的……转身不一定最软弱,往上爬不如向前进!”
——这主意不错。当然,对富人或那些雄心勃勃的家伙而言,如此“规劝”大抵无效。小布什或许就最反感别人对他和他们国家的“改变”。“世贸大厦”一夜间沦为废墟之类的“改变”其实还仅为表象——而实际上,它所试图改变的,是整个美利坚对自身核心价值的坚信……这很糟糕。
给所有游记敲响丧钟的游记
列维·斯特劳斯 《忧郁的热带》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用游记的方式给游记敲响丧钟
书一开篇,作者写:“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然而,现在我预备要讲述我自己的探险经验……”
在书的末尾,作者写道:“对一块比任何人类的创造物都远为漂亮的矿石沉思一段时间;去闻一闻一朵水仙花的深处所散发出来的味道,其香味所隐藏的学问比我们所有书本全部加起来还多;或者是在那充满耐心、宁静与互谅的短暂凝视之中,这种凝视有时候,经由某中非资源的画像了解,会出现于一个人与一只猫短暂的互相注目之中……”
这一头一尾间所形成的落差或许正是作者对人类自身各种欲望、理念乃至行为的警惕与怀疑?
评家James Boom称本书为“一部给所有游记敲响丧钟的游记”,“一部关于它自己文化的书,也是一部否定这种文化的书”,“一部关于20世纪的书,也是一部否定20世纪的书……”
这些“标签”式的提炼看似轻松,但其“提纯”的过程并不容易……我知道。
《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PART 5
谈话即道路
林芳谷·孙小宁 《十年来去/一个台湾文化人眼中的大陆》 台海出版社
谈话即道路,交流是天堂
对大多数人来说,林谷芳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记者孙小宁跟随这个名字多年,与林芳谷一起完成本书。全书近30万字,对话体,因为我也做过记者,看见这样的耐心、规模,便马上计算采访时间、进度、精力投入,直至进入成本、退出成本之类。算完后,我再次发现自己俗不可耐。对本书以及它的两位作者而言,我的计算几无必要……正如很多时候谁也无法为一种感动或迷恋开列加减乘除之类的算式一样……那写仿造时下流行的“天气预报”语文、编造诸如“伤心指数”、“眼泪指数”的家伙其实比天气预报语文更扯淡。
该书第八章,林芳谷与孙小宁谈及大陆流行语中最为常见的“搞”字。林说:“比如开会,大家习惯说你是搞什么的。‘搞’在台湾不仅是‘俚语’,还带有一定的贬义,所谓‘胡乱搞搞’。大陆这个习惯用语有它的历史背景,我还能谅解,但即使排除了视‘搞’为低俗的‘偏见’,这种大家都用一个词的现实仍然显示了社会一定程度的‘无文’……‘不文’的根本是什么?就是蔑视学问、修养,它存在的原因其实不只是因为现实困厄,更在于只将言语作为力量的展示,因为不留余地,所以不容易有一颗体谅别人的心……发生在社会精英、知识阶层身上的‘无文’,往往内里透着一种‘输不起’。需要制式地被介绍,需要粗声大气地表达意见(P147148)”……
这段谈话一再挑剔动词“搞”并对其所旁涉的心理现实、历史现实乃至于未来现实认真研判。对应林的提示,孙小宁更是将话题延展至诸如“大众语境”、“精英语境”、“历史依据”、“现实依据”、“精致文化”、“粗鄙文化”等宽阔视野……沉浸在如此开阔的无奈联想中,曾被我关注过的诸如“欢迎来搞(稿),搞(搞)费从优”之类的下三路“流行语”顿时从一个“笑话”延展为一个细节——一个巨大悲剧的细节——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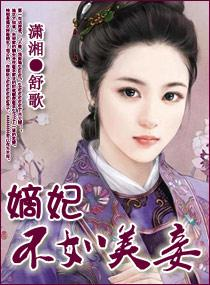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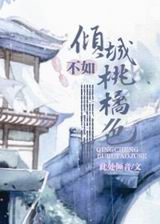
![[系统]亲,你走错剧组了封面](http://www.nstxt.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