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固然有可能被拍成拙劣的电视散文,可陈凯歌、张艺谋他们也很难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拍得尽如人意。
《白镜头》中全部照片均以“SARS”为主题。它们被分成记忆、状态、心情、民间、行为、爱情、时尚等十个部分。在那数百幅图片中,贯穿始终的细节是口罩——这也是该书名为“白镜头”的原因。而当口罩与记忆、状态、心情乃至贩夫走卒、时尚美人、北京土著或北漂老外紧紧贴合到一起后,一种怪异的“哲学风景”也便随之诞生:无论那只口罩十二层、二十四层、三十六层,它都如一条醒目警戒线,消弭亲密乃至过度亲密,催眠热爱乃至无限热爱,并直接破灭掉人与人、人与空间、人与动物、人与舟船车马间的既定关系……
于是,那数百只口罩也便大致等于对尊严、现实、生命、距离、流行、瘟疫、历史虽然琐屑而又真切的注释。并且,就算后来口罩已经摘掉,但那无尽混沌或清晰的创痛心路不该被遗忘——我知道,疫情缓解未出一周,街边大排挡便已车水马龙酒翻钵倒无非缘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不朽人性,但健忘确将使我们失去更多——很久很久以前和很近很近以前,我们遗忘的速度乃至决绝,给人印象太深。
所以,至少那些被隔离、消毒、疑似、新增之类苦苦围困过的人们,会经由此书,将那种种掩蔽在白色口罩后面的空虚、惶恐、无奈、无助一一仔细珍藏——我是想说,事实上,“遗忘”比“SARS”本身更可怕。人生一世,谁能不流泪?可假使一再流淌相似的眼泪,那它与一再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也便全无区别。圣经中有一句话我喜欢:“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在我看,这句子后面没直言的那个非常“巨变”一定关乎”记忆“。一个没有记忆的人,永远没有精神泉源。
在“SARS”最为猖獗时,某报“天天副刊”曾就“SARS”缩写特别征寻另类解读。后来,非常流行的一个“另类解读”据说即出自一个读者的异想天开:原意为“急性重症呼吸系统综合症”缩写的“SARS”,被某读者重新定义为“微笑,并保持微笑”……延续如是创意,我以为更应郑重提示的,正是记忆——不仅深刻记忆,并一直保持记忆……就像《白镜头》封面上那位优雅的封面女郎一样:尽管口罩已经摘下,可那环无形口罩清晰的“晒伤”依旧清晰。
水一直在滴,石始终未穿
金敬迈 《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 中国电影出版社
熟悉自我灵魂中的每道伤痕
在囚禁期,金敬迈犯了眼病。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破例得到一瓶眼药水。那眼药水儿是玻璃瓶装的,瓶口儿比牙签略粗有限,瓶子的尾端有一个橡皮塞,用拇指轻轻按动,药水就以一滴一滴落下……眼睛复原后,金敬迈冒天下之大不违,私自藏下了眼药水儿空瓶,每当夜深人静时,金把清水注入瓶中,一滴一滴往地面上滴洒。他把这个无聊游戏命名为“水滴石穿”。最终的结果如你所知:水一直在滴,石始终未穿。
上面这个细节出自《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读完它,我奇怪地想,就算到了二一六年,至少还会有两三个人将本书与另外一本叫做《欧阳海之歌》的书对照着重新翻看?如你所知,这两本书的作者是一个人——金敬迈。他的至爱亲朋都叫他“老迈”。如此称呼亲切而外,也是写实——如今金敬迈真的已老。在《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一书扉页之首的那张照片上,金老态龙钟,只有目光还是一副杠头神色。这也是细节之一。“杠头”和“水滴石穿”……我说不清楚这其间的对比在暗示我什么。
《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一书也被出版者称之为“秦城监狱囚禁生活纪实”。可就书本身而言,读者更直接的阅读感受是,其实比躯体的囚禁更更为振聋发聩之处在于,该书用丰饶的细节记录下一个灵魂在地狱般空间中不可能翱翔的翱翔、不可能逍遥的逍遥。而如果没有本书,我们通常会以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长达七年四个月总计3169天的漫长岁月里,尽管老迈已经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长相,但他却一一记录下自己灵魂的每一个颤抖,每一次痉挛、呕吐、绞痛直至内出血,于是,他的《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其实也是那个已逝去时代灵魂的照相。
孤独是痛苦的。寂寞是痛苦的。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长相却熟悉自我灵魂中的每道伤痕,也终于惶恐不安。老迈的办法是,将一只始终舍不得穿的深色袜子放在一个浅浅的搪瓷饭碗里,然后将其浸满清水,一面“镜子”也便制作而成。在这面镜子里,他看见了自己,也嗅出记忆中的霉烂气息(P15)……而现在,读者终于可以相信,他看见的,还有自己形容每道褶皱背后时代的浓郁阴影。
被单身囚禁时,老迈37岁。获得自由时,他45岁。他在秦城监狱一共呆了3169个日日夜夜。他挨过无数巴掌,总计被打掉八颗牙齿,关押他的牢号是20446……作为时代阴影,尽管这些数字单薄得有些沉重,可我依旧以为,有这些单薄的沉重或沉重的单薄,总比什么也没留下的空白好。好很多。
说到影片《无间道》片名含义,导演刘永强说,片头有字幕解释——所谓“无间道”,即《法华经》中所言“无间地狱”,意为痛苦不可超生,而该片的片尾字幕上提示出的,却是一个反向主题:即有时候,永生更是一种惩罚——在那后一个语境中,只有死亡才可以永生……刘导演的话提示我想,在《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中,读者看到的已经不是金敬迈而是老迈——他们已是两人而非一人。金敬迈早就死了,而活着的哪个杠头已经不再是他。这意思用老迈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醒来’的人——体温37。5℃,正常偏高,略带低烧……
如你所知,二一六年是文革五十周年纪念。
生活就是串味儿
卡尔维诺 《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 辽宁教育出版社
生活就是串味儿
在本书中,卡尔维诺顺手还镶嵌上了对人类生活态度的多种假设:轻逸,迅速,确切,易见,繁复……
这其中的每一项,除专指文字生命状态外,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情境的一种浓缩。它甚至可能成为我们未及展开的未来生活的扼要提示:你轻逸了吗?你确切了吗?你繁复了吗?
文学日益边缘化,其实很正常。为这个“正常的灾难”大呼小叫长吁短叹,多余。这个“正常的边缘化”其实刚好将文学送回到常识:它其实仅仅是一枚橄榄或怪味豆?
这样,将卡尔维诺原本标明为“文学”的备忘录当作一种现世生活范畴的假设,或许更符合卡尔维诺原意——太多的现世悲剧其实不过因为错位:该“轻逸”的时候我们“繁复”了,该“确切”的时候我们“迅速”了……
更多心怀鬼胎的误读出现于阅读《寒冬夜行人》中。它为什么被评家称之为“小说中的小说,文学中的文学”?
小说十余万字。但卡尔维诺在其中处处埋雷:情节的雷、思辩的雷、探究的雷。它以一男一女两位读者为调换装订错误的一部小说相遇、相知、相爱的故事为线索,并杂糅10部不同作家所写小说片段,制造出一种迷宫般的阅读效果。甚至卡尔维诺本人也在小说中以角色面目出现,上窜下跳……它使这本小说的阅读更像一个考验读者耐心的文字游戏。与电脑游戏不同的是,它只能在想像中完成。
假使上帝不允许想像出错,想像便早已不复存在——如你所知,很多时候,误解也是一种想像——在贫穷的时候把自己想象成百万富翁、在挥金如土的时候把自己想象成街边乞丐……
至于《寒冬夜行人》,则须顺从卡氏的故事逻辑,把自己想象成那位“女读者”或那位“男读者”……直至干脆把自己假设为那张“宽大的双人床”?……随便。
在《寒冬夜行人》的第三章,卡尔维诺假借他人之口反复强调:“生活就是串味儿”。仔细想,“串味儿”既是“想像”的别称,也是“想像”的要害。
调养文字
恺蒂 《书缘·情缘》 辽宁教育出版社诉尽平生云水心,尽是春花秋月语假如文字也自有其生命,一个作者的文字就像他养大的“孩子”。
笼罩在这一比喻中,恺蒂对自己的文字施行何种调养、照料、呵护,其文字才有了现在也清澈、也沉潜、也丰富、也单纯的模样?我还没想明白。
依我之见,在汉语写作者中,如恺蒂一样稳健灿烂兼有、资讯识见具佳者,并不多:说中年别恋,恺蒂说:白头到老不难,烂漫很难,而现实最多的,是那种“努力着的不愿宣布失败的婚姻”(P93);说窥视情结:恺蒂说:隐私有市场价值,远非媒体一厢情愿可以解释,“所谓尊重别人隐私只是一个道德上的梦想,是一个大家为了礼貌而遵守但是内心里又时时刻刻想打破的神话”(P168);说英国文化的内敛,恺蒂说:英国文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在于,它有一种“表面上的温文尔雅”,“大家喜欢的是有话憋在肚子里的礼貌”(P266);说男女平等的虚空,恺蒂说:“三十之后,男女之间的游戏规则就变了”,“有人讥讽三十多岁的女人就像是一个急着等待受精的卵子,想的就是找老公,生孩子(P248)”……
读完《书缘·情缘》,发现所谓恺蒂文字的干净,仅止表象。其内里品质,应是“妥帖”与“确切”。没有这些,所谓“干净”也便无从说起。
某日与恺蒂fans交流阅读《书缘·情缘》心得。出乎预料,该fans摇头再三。问及因由,他直抒胸臆:不好看不好看不好看了,恺蒂已经去南非了……这等于说,很多读者对恺蒂的喜爱,其实也是对沉潜、清澈、冷峻并幽默的英国散文的喜爱?
她们的故事
克拉克·舒曼 《不朽的音乐之魂》 贵州人民出版社他的故事,她的故事,我们的故事丛书共四种,传主均为德国知名知识女性,包括著名俄裔学者、作家莎乐美,有十九世纪著名的女钢琴家克拉克·舒曼,德国犹太哲学家、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以及十八世纪德国才女卡洛琳·谢林。
“本世纪即将结束,统治了两千多年的男人故事(His story)在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女性的呐喊中变得苍白无力,是时候了,是该拿起笔写下我们的、她们的故事的时候了……”
这段话是该丛书主编徐菲所写。她的话里好像憋着一口气?
尽管……但是……
肯特·基思 《似非而是》 中信出版社
还是要建设,还是要行善事,还是要心存高远
当“简单”成为大众需求之梦,满足它,便是商机——从“手机”到“洋快餐”,证例多多,不说罢。
在图书产品中,近年最著名的“简单”便是那坨“奶酪”和那位“富爸爸”了,也可免谈。唯一可说之处是,当那坨“奶酪”和那位“富爸爸”瞬间繁衍出无数后续版,进而成为一个全然无序的庞大“家族”后,老子、儿子、孙子辈分乱做一团……不像话。
一切都难以预料。谁也没想到,“奶酷”、“富爸”之后美国人民还能对一本初版于十数年前的小书《似非而是》重新产生阅读兴趣——它“简单”之至。在那五万来字中,作者不过是为读者开出了十数条老生常谈。并且,就连阐述那十来条“戒律”,也被简化到四个汉字:“尽管……但是……”
或许,正是这样的简单,使得读者对它感觉亲切?或许,在日渐焦虑、劳碌的都市生活中,“简单”已成为现代都市人最向往的乌托邦?
“思想最博大的最大的人,可能会被头脑最为狭隘的最小的人击倒,但还是要心存高远”;
“你如果成功,得到的会是假朋友和真敌人,但你还是要成功”;
“你如果行善事,人们会说你必定是出于自私的隐秘动机,但还是要行善事”;
“你穷数年之功建设起来的东西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被毁掉,但还是要建设”……
面对如此老生常谈,我的揣测是,它之所以得以击中现代人的情感软肋,不过因为在一个在在剑拔弩张、标新立异的年代,“老生常谈”已十分稀罕。
当然,诸如《似非而是》之类,“简单”只是它的外表——其所言“是”或“非”,就像两颗钉子,而当那两颗钉子上被不同的读者悬挂上不同心情的皮氅或礼帽时,“简单”不再——美国人民对它重新焕发出的阅读兴趣即因此而来?顺着作者肯特·基思的思路或句式,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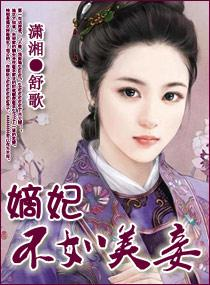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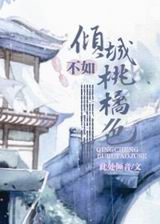
![[系统]亲,你走错剧组了封面](http://www.nstxt.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