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丛书中收有《手痒》(陈村)、《脑袋书本及其他》(赵汀阳)、《星光失眠》(何立伟)、《爽呆了》(王玉北)四种。此四种个人集中,要论嘀咕状态,陈村最佳。在时尚的剪刀劈头盖脸的削删中,所谓“嘀咕”,不仅要学习,而且要修炼:它要求你符合时尚潮流,也要求你多少倾听一以下来自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多方照应,殊为不易。不信你就试试看——在整体阅读氛围愈发一地鸡毛的现实语境中,全无个性之神韵的“鸡毛”没人要看。弄出点动静不难,难的是这点动静尽可以没什么意义,但必须不讨厌并同时讨人喜欢。在今天,讨人喜欢多难呢。
这样,“嘀咕”已大致就是一门学问。就说陈村,其“嘀咕”策略便是凡事倾听自我内心的动静:浑浊就浑浊,激烈就激烈,迟暮就迟暮,庸常就庸常。因此,无论何种规格的时尚的石子儿,在陈村的水塘里总可以激起或大或小的涟漪。陈村自己恐怕也没想到,作家出身的他而今已是一位“嘀咕老手”。
说王小波,陈村说:“那个叫王小波的人终于死了”;
说美女,陈村说:“一个城市大了,很难没有美女”;
说休闲,陈村说:“它的一个最神圣的职责就是‘花钱’”;
说围棋,陈村说:“棋力的较量,常常也是坏心肠的比试”……
粗粗统计一下,在《手痒》一书中,陈村文字所涉及的内容包容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各方面。从钟表,到睡眠,从婚典,到美女,从时装,到烹饪,无一不谈,无谈不妙。有人说,当有人开始向爱因斯坦询问与物理毫无相关的问题时,爱因斯坦便不再是一位专家,而成为一个名人。
与之相似的话可以说给陈村:在他这些明显将就各种报章副刊编辑死缠硬磨一挥而就的短章中,机智与平和杂糅得那么圆融妥帖不假,但因此浪费掉的的其实是一部心灵之作的创意?也未可知。
与陈村相似,作家何立伟不仅完全沉浸于一种“格言写作”状态中,甚至亲力亲为,为自己的格言画插图。或许刚好相反——先有图画,然后再填上格言?
“祖父的额头已经干旱许久,我希望雨季到来”。
“我常常在牌桌上用一双颤抖的手捉紧自己未知的人生”。
“门是生活之书的封面。你用新的激动翻开它,遇到的却是老故事。”
“把裤子熨得那么直又有什么用?如果我们的膝盖是弯曲的。”
“最难兑现的承诺最容易说出嘴来。”
“星期天和它的无聊的烟灰被弹在一只苍白的玻璃缸里,我打一个哈欠便准备去失眠。”
“我喜欢用最清晰的声音,表达最暧昧的情感。”
“在开胃酒还未上来之前,亲爱的,先上一点开胃的争论怎么样?”
……如此清新、短小、聪慧、敏捷,并间杂着沙哑叹息的短句、格言,读来确如时令樱桃般可心可口,但真就无休无止读起来,读下去,也有腻烦,并且担心——正如何自己所说:“用一只笼子把飞翔关住,用一句格言把真理关住”……在清新、短小、
聪慧、敏捷等丰富感受将我们的五官娇宠得熨贴完美之后,思想的行进便很容易偃旗息鼓?
时尚剪刀的嘁嘁嚓嚓有明快悦耳节奏,但事实上它也把一切旁逸的思绪以及生长于时间长河里的内省与呐喊统统切碎再切碎,同时,也让所可能恒久的闪光细碎到粉齑,细碎到近乎于无?从宏观上看,尤其站在一位资深作家的角度上看,它或许正是一种才情的挥霍?我不知道。
“环保”心灵
亨利·梭罗 《瓦尔登湖》 吉林人民出版社
睁开眼睛才会天亮
本丛书所收文字主题多与“环保”相关,但并非狭义“环保”。
在一个聒噪年月,就算仅止“泛环保”,益处依旧多多——相对于地球、天空、心灵、爱情、儿女情长柴米油盐而言,其实样样不离“环保”。
在此套“绿色传典”中,多种名著级畅销书、长销书、经典书尽被网罗其中——从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
其中包括已有多种版本的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
在《瓦尔登湖》结尾处,梭罗说:“使我们失去视觉的那种光明,对于我们是黑暗。只有我们睁开眼睛醒过来的那一天,天才亮了。”
梭罗的话是问题?还是结论?
尴尬的非正常生活
洪晃 《我的非正常生活》 海南出版社
A cat has nine lives。
本书完全按照畅销书“模版”制作而成,作者、出版者对此心知肚明。女主角即作者本人对自己的美丽已不自信——她知道,在一个女色、男色轮流坐庄的商业社会,一个年过四十的女人毫无廉耻地在书的内文或封面上刊登用铜板纸印制而成的彩色照片,很无聊。
于是,在书籍封面中被特别提取出来的元素基本不是图像信息,而是可由读者任意虚构与想像的文字信息。这些信息就其审美趣味而言,基本全无超过作者曾在《三联生活周刊》之“生活圆桌”栏目中所发小短文的可能,尤其没有超过“男人分两截”——那篇拿男人开涮的妙文。不过,它们在商业推广上已是力挽狂澜……归结起来,其要害即作者在本书中的那个一而再再而三坦白,二十五个汉字:“章士钊的外孙女,章含之的女儿,乔冠华的继女,陈凯歌的前妻”(P100)……除此之外,另有一个生硬标签:“名门‘痞’女”。
这是一本“邪门”之书。其要害在于,作者像开“趴剔”一样将自己的各路朋友拉来凑数字,撑门面——酒肉朋友廖文在场,海外朋友刘索拉在场,业内朋友朱伟在场,同行朋友伊伟也在场……细究如是,也就发现,如此“邪门”之可怜,也是无奈。它意外证明,说到底,洪晃对“成名”一事终究缺少真实兴趣。因为,她甚至对成名“规定动作”——写书这样的大事亦是如此儿戏,直至敷衍、搪塞。
这个矛盾很尖锐,也很有趣。书中无处不在的所谓“无名压力”,对洪晃而言,仅止皮相。
洪晃真正的危机来自于其“文化身份”的尴尬:在一个不需要淑女、不缺少才女、更不发愁美女的年代,一个“出版女”的动静,充其量不过是其在圈子里已有动静极为有限的一个放大版,仅此而已。
我的这种解释,在作者本人,有另外一种表述:“违背我信念的手段是我达到我信念的捷径……我知道捷径,但是我没有决心去做这件事,这就是我的教育给我最深的信仰和绊脚石”(P101)。要我说,除此之外,“我的教育”还是一个“熟人社会”的紧箍咒——而这个紧箍咒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里已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顺便可提的是,在本书封面上被强硬推出的所谓“名门‘痞’女”概念,其创意自是为了扩大读者半径——“痞子”大众耳熟能详,而“一个出身名门的痞子”、“一个出身名门的女痞子”更该吊足大众胃口……而这本身,其实即洪晃所谓“违背信念的捷径”。其糟糕之处除了凭空制造无数误解、歪解、曲解外,还基本掩蔽掉了洪晃原本异常突出的那种有教养的傲慢或偏见,它与所谓“痞”其实根本不搭界。
韦莲司与胡适
胡适 《胡适与韦莲司》 北京大学出版社
春者,天之本怀;秋者,天之别调
撰写本书时,周质平将主题聚集于胡适情人韦莲司。线索从胡适《留学日记》中零星记述中考证而来。
韦莲司,美国人,胡适说她人品高洁,学识丰富,特立独行,不恤人言……韦莲司与胡适神交逾50年,仅胡适写给她的信件即有200余封。
在撰写如此“故事”过程中,周质平曾担心自己是否因为本书写作而成为“胡适的罪人”——破坏胡适形象,但后又改变看法。
周认为,自己写作态度认真严谨。不过,问题在于,是否只要认真严谨,便可能还原出一个真胡适?一个被掩蔽在传统孝道背后、满怀一腔悲寂的胡适?
功夫在诗外
黄灿然 《必要的角度》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为月忧云;为书忧蠹;为花忧风雨;为才子、佳人忧命薄
黄灿然是我敬佩的作者,他出的所有书我都买,买不到就到网络上去找。再找不到,就托人向作者索要。
《必要的角度》一书是黄灿然有关翻译技巧尤其是诗歌翻译技巧的心得之作。
书中P223页文章名为《一部失败的布罗茨基中译本》,文中条分缕析,焦灼于一字一句一段一篇……我的感想是,所有媒介从业者或广言之文字工作者其实都可以将本书列入学习范围。
常言说,功夫在诗外。在一个就连手机短信息都百般追求“文才斐然”的年代里,这句老生常谈的重要性远未引起足够关注。对一篇论文而言,长句好?短句好?对一个编辑而言,当来稿基本合乎要求,作者行文中的那些个人趣味与个人习惯该删不该删?对于一篇刊论而言,大是大非确认无疑后,要不要锋芒毕露句法奇崛?凡此种种,黄都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尤其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黄对语文技巧全方位的研判和考量。依黄之见,倒叙还是顺叙、横切还是纵劈,低密度还是高繁复,其实不仅仅是技巧,而且更是作者综合实力的整体体现。“为什么需要活力?其中一个原因即是为了避俗。模式化的句法、词语与模式化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是紧密联系的。一个敏感的写作者往往思想、思维超出一般模式……而平庸的意思是,你挑不出他有任何语病,可是也看不到他有任何真知灼见”……
经过黄的提示,转身再去看日出一刊的那些狗屁杂志、狗屎文章,端的“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噩梦”。
破落美丽的天堂
黄永玉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我就在每个碎块里微笑
散文、随笔外,书中也收入黄欧洲写生多幅,有图有文,相辅相成。
黄永玉属于那种经历芜杂、一生传奇不断的作者,连同他的文字,也如是。其文字算调性繁复,且极富画面感,既令人心动、感慨、唏嘘,也裹挟着衰老与年轻、苍凉与优美、狡黠与纯真间无休无止纠缠不已的对抗……说不出什么颜色,但绝非主旋律。
在《永远的窗口》一文中,黄说,他和太太曾为香港蜗居专门买回“漂亮的印度浓花窗纱”打扮窗子,而使其成为“破落美丽的天堂”……
在一种胡乱的联想中,那个“破落美丽的天堂”,其实便是一个自在安宁的灵魂寓所?
在另外一本名为《给艺术两小时》的书中,黄在岳鹿书院演讲的言论被记录下来。
那书书名略带反讽意味——意思说,“两小时”之外,大家尽可声色犬马,歌舞生平,或者相反,饥寒交迫,嗷嗷待哺?
如果不是反讽,警醒的意思总是有的,比如,给艺术两小时,不是岳鹿书院这样的集合,而是每天,自己,过问一下心灵,时间一久,那“过问”或许就会产生化学变化?
一个好的书名多半诱人联想。那种想像空间尤其大想像边界尤其缥缈的标题——财迷地说,标题本身先就挣到钱了。
与自撰文字相同,口语中的黄永玉一样出言不逊。已经很老的黄依旧如孩子般热爱着,疯狂着,悲悯着,无奈着……
于是在演讲中,豪气万丈亦成为黄的最大魅力。他在北京购得7亩地界,自己设计“万荷堂”。“万荷堂”被3000亩果园环绕——有桃,有李,有苹果……黄为此自作诗句感慨万千:“十万狂花如梦寐”……
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在黄诗人一派骄傲耀眼豪言的余响中,想起他感慨张志新烈士时娓娓道出的咬牙切齿:“如果把我切成了碎块/我就在每个碎块里微笑……”
或豪放,或娓娓道来,当其出自真心,即本色。
《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PART 4
所谓传记
基蒂·凯利 《南希外传》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回忆的片断,欲望的火焰,痛苦时的迷失、愤怒、嚎叫
在纸媒上有可能直接吸引眼球的,简单就是“秘密”二字。因此人物传记中若无独家爆料几乎难于成篇——当然,读者允许那些形形色色、千姿百态、五颜六色的“秘密”内容质地各不相同。
美国著名记者索尔滋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到延安时期因为生活艰苦工作繁忙,毛泽东严重便秘。这个消息当时延安上下都知道。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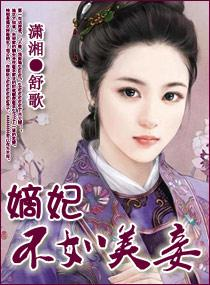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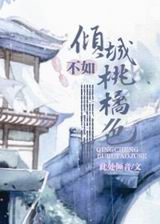
![[系统]亲,你走错剧组了封面](http://www.nstxt.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