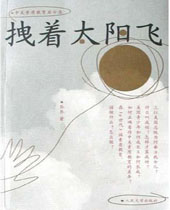太阳发芽-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没有,没有的事,团长说了我跟老王是七连的骨干,七连全靠我撑着。”“他们把你跟老王比?”“老王开荒四亩半威震古尔图,谁能跟他比?就我老李能跟他比。我弄的花果山比他的四亩半先进多了。”“先进个屁!你俩二球货,老王爬在自己开的荒地里,一辈子也爬不出来,你呆在你的花果山上一辈子当猴子。”“团长说了,猴子象征智慧,猴子聪明伶俐。”“你真想当猴子?”“当猴子没啥不好嘛。”“猴子是原始社会的东西,你想当猴子想从你老娘的肚子里爬回去,回到原始社会?”老李脸发白。老婆说:“你真有这念头,不单单是你老娘倒霉,你李家的先人可就全倒血霉了。”老李望老婆一眼,又望墙角,老李的目光仿佛蛛网落在那角落里,老婆说:“你李家的先人得从墓坑里爬出来给你腾地方。”老婆说:“你听,你李家先人在墓地里跳舞哩,那个长尾巴的老东西是你李家第一代先人,瞧他跳得多欢势,你跟着跳嘛。”老婆捅他一下,老李缩,老婆说:“看亮清,你老先人长尾巴的,育下你这后人也想长尾巴哩。”“你敢作践我先人?”老李“哇”一声跳起来:“你敢作践我先人?”老李把老婆推到墙角,转过身给李家先人磕头,老李泣不成声说不出话。外边刮风,乌云埋了月亮,老婆说:“你先人叫风刮走了,回老家了。”
那年冬天,老李回了一趟老家,那豫南山区的一个小村庄。他进村的时候,他娘刚刚升天,族人正要拍电报叫他,他就回来了。他说俺回来了。老乡们伸脖子朝大路上看,大路上覆盖着积雪一样的灰尘,老乡说:“就回来你一个?”老李说:“工作紧张,老婆娃娃没回来。”老乡们说不是这个意思,老乡们说张家老二也在新疆工作,去年回家探亲,满满拉一卡车东西,你咋空手两吊回来了?你娘走之前,还说我娃干大事了,没想到你空手两吊回来,你娘要见了保管上不了天。老李给大家让烟,“红雪莲”烟。怕俺娘念叨俺,俺没给准备急巴巴赶回来。老乡们噢一声:没做准备,急巴巴赶回来的?怪不得空手两吊,下回可不能空手两吊。好多年后,老李成了古尔图首富,衣锦还乡,身后紧跟着两辆大卡车,老乡们喜气洋洋,放鞭炮欢迎他。
老李回到古尔图的七连,再也不提调离的事情了。连长很高兴,菜园的西红柿又肥又大。
老李没动静,老王以及那些想调走的人很着急,他们找老李问是咋回事,老李说:你们没长眼睛没看见?大家说:“我们把你当先锋,只等你打开缺口,我们大家好冲出重围,没想到你他妈大逃亡啊。”老李默不做声。过两天,二排发生了一桩人命案,大家才恍然大悟。二排有位上海女知青,为了调动让排长尝了鲜,排长尝到甜头不停了,吃下去要没完没了地吃下去,知青只好把自己挂起来,挂在高高的沙枣树上,小小的身体像只鸟,离地很高。大家都奇怪。“上吊就上吊,一板凳高足够了,吊那么高干吗呀,又不是天葬。”一直不做声的老李忽然冒出一句:“吊高一点就能离开这地方。”老李一句话把大家震得翻白眼了。
古尔图荒原郾迁徙(1)
内地的支边青年源源不断,七连人也多了枪也多了,连长、指导员派头十足召开誓师动员大会,主席台上放着一堆用坏的坎土墁,那是父亲老王开拓荒原的见证。小伙子们脸红了,脖子粗了,热血哗哗响。
队伍开到荒漠边缘,父亲老王打头阵,那股疯劲看得小青年们咂舌吸气。他们在课本上学过英雄郝世才在南泥湾每天开荒四亩三分半的事迹,事迹在他们眼前展开,一直展到荒原尽头,他们亲眼目睹了大地的能手。父亲老王在他们心目中当了两礼拜英雄。那些日子,他们天天围着父亲老王,他们把父亲老王当做神话里追赶太阳的夸父,他们当中有才能的人绘声绘色地说:“我们看见太阳从你的背上滚向地平线,大地就出现了。”
那些日子,父亲老王享受了许多赞誉、香烟和饼干。连长、排长们眼馋吞口水。父亲老王仅仅风光了两礼拜。第三个礼拜,上帝厌倦了,小青年们被分到各排各班,扛上坎土墁开进荒原,荒原开始袒露它的真实面目,他们在短时间里经历了原始先民数千年的艰辛和劳累。父亲老王再次出现时,他们远远躲开,他们说他们看见荒原从父亲老王身上展开,伸向无边无际的远方。连长给他们的指标是荒原的边缘。两礼拜前,他们是荒原的观赏者,他们用肚子里干巴巴的几滴墨水拼命地构筑荒原的原始美感,诸如粗犷之美,阳刚之美,狞厉之美,一旦他们走进荒原,什么感觉都没有了。父亲老王走近他们时,他们一哄而散,散入荒原的角角落落。十多年后,他们才钻出来,搭车去乌鲁木齐,乘火车离开新疆,后来据他们讲,车过河西走廊他们才摆脱父亲老王的追赶。
我大声说:“我爸十年前就死了,我爸活着也不会追你们到河西走廊。”
他们说:“古尔图荒原太大了,好像全世界的土地都在那里,都是你爸开出来的,我们总是把古尔图跟你爸混在一起。”
他们当中不乏具有艺术细胞的人,他们指着坡坡坎坎上的白石头说:“那就是你爸!”
“你们竟敢搬我的祖坟?”
“你别误会,这是我们离开古尔图时在路边随便拣的。”
我们凑过去看那块石头,石头裂好多缝儿,缝隙里沾满尘土,那些人说:“我们就是这些尘土,我们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古尔图度过的。”支边青年及后来的下乡知青,都难以忘怀与泥土融为一体的日子。那种感觉近于童贞,后来他们返回故里,荒原成为记忆。他们说:“所有的记忆都是尘土。”他们当中很少有平庸之辈,他们当中有画家,有诗人,有作家。
画家给我看他的组画《荒原景象》,第一幅画上画着两棵纤弱的树,彼此离得远远的,矗立在灰茫茫的原野上,背景是绚丽多彩的夕照。画家说:“一棵是我,一棵是我女朋友,那落日是我们的梦。”他又让我看第二幅画,画面上有一棵干瘦的牧草,灰尘弥漫了空间,一片灰黄。画家说:“女友沦丧,我不再是树,我变成一棵草,让泥土融化我,没有水分我融不进大地,我想让篝火烧毁,可地层的岩浆与我无缘。”“天上有雷电啊?”“电火只能击燃树,我早就不是树了。”画家拿出最后一幅画,画家指着画面上干裂的土地说:“那是我的嘴唇,它们一直龟裂到我的心底。”“你没有喝过天山的雪水?”“喝过,喝了十年,这种干渴是雪水浇出来的。古尔图的苇湖和牧草全都喝天山的雪水,可古尔图是荒原,古尔图的嘴唇是干裂的。”画家收起画册,画册上有一层灰尘,画家说:“我早就不是画家了,大家叫我画家就因为我不再干这营生。”
“你现在干什么?”
“去澳大利亚。”
“去发财?”
“不,是回家。”
“回家?”
“那年,我们离开上海去支援大西北,车子把我们拉到古尔图,我们到古尔图那天,正是加加林登上月球的日子,我们看到的古尔图就是月球。”
画家的声调比月球更荒凉,他的喉咙里全是石头和沙子。
“那天,我们忽然想家,我们把又圆又光的石头抛到空中,以为那就是月亮,月亮落在地上,我们的心就凉了,后来,我们见到那个开荒四亩半的老头儿,对不起,那时我们不知道他是你父亲。”
画家闭上嘴,我说:“你接着说,我父亲怎么样?”画家不愿意说我父亲,画家说:“我们知道这不是家,家不会在古尔图荒原。”
“你们好多人不结婚,就盼着回老家。后来你们都回去了。”
说这话时我的舌头很大。我母亲十六岁那年离开老家,来到古尔图荒原,多少年来她含辛茹苦,为的就是让她的孩子离开荒原。我和姐姐王慧考上大学,离开新疆。姐姐王慧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天动力学,成为宇航员进入太空。我大学毕业任职于北京一家报社,到大江南北去采访各行各业的明星,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眼前这位画家就是近年来的画坛怪杰。
画家说:“我们并没有真正地离开荒原,我们回到上海才明白,这里早就不是家了,真正的家十多年前就消失了,古尔图一直在我们身后,从我们的背后展开,一直铺展到上海,有些人去日本,去澳大利亚,古尔图的大地就一直铺到那里,古尔图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空间。”
画家说:“其实你想从我嘴里打听摆脱古尔图荒原的路径。”
我大吃一惊,这种想法好多年以后才能从我的脑仁里发芽,我对画家这种揠苗助长的做法非常生气。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你有点小难受,这是难免的,艺术家的思维总是超越时代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你写小说就应该习惯这些。”我很快就习惯了,并且承认我确实有这种想法,画家说:“这种想法很危险,根本就没有摆脱古尔图的路径。”我大声问他:“那你干吗回上海,干吗去澳大利亚?”画家说:“那只是拉开距离,空间大一点,不至于窒息。”画家给我一本书:《我的财富在澳洲》。“我朋友写的,艺术品只是藏身之处不是途径。你又吃惊了,你以为你姐姐王慧当宇航员飞上太空就算离开古尔图了?那是做梦,那只能扩大古尔图的面积。”
画家打开箱子,取出那块石头,画家说:“这是我的肖像,你刚才看到的树和草是我的过去,你瞧这块石头多么荒凉。”
“跟我父亲墓地的石头一模一样。”
“我们第一次看到你父亲开荒,还以为大地从他脚下诞生呢,原来是荒原在诞生。”
古尔图荒原郾迁徙(2)
1954年秋天,父亲老王带着美丽的妻子来到古尔图荒原,于是荒原变成了丰饶的沃野,那里长出大片的玉米大片的麦子大片的棉花和向日葵,生土变成熟土,他们跟庄稼一样长出一群娃娃。这就是故事的全部。
我要讲的是故事以外的事情。我对画家说:“你们看到的坎土墁是我父亲故意弄坏的,他想离开那地方,或者干技术性的工作。”
画家眼白很大,屋里所有的人眼白都很大。
我说:“他亲口对我说他中了埋伏。”
大家“哟”一声乱了套:“我们也中埋伏了。”
画家打开画册,给大家看智利画家何·万徒勒里的木刻画《迁徙》,画面是一片褐红色的大海,鸟群穿过浓云飞向新大陆。画家说:“我一直以为鸟群迁徙的是生命,没想到它们是在突围。”
海面和天空都是赤褐色,深重的色块把鸟群挤出空间。
十多年前,父亲老王在古尔图荒原碰到转场的哈萨克牧民,那宏大的场面把父亲震撼了,牧民们告诉老王,他们从额尔齐斯河那边转到天山里去。父亲老王从滚滚烟尘中得到某种启示,回家告诉老婆,老婆非常激动。“你说他们像鸟群往山里去?”老婆双手绞在一起,在屋里来回地走,并且推开了窗户。“当年咱们就是这样离开北塬到古尔图来的。”
那时,少女王慧已经出生,趴在母亲怀里吧唧吧唧吸奶水,这种响声包含了某种生命的东西,他们两口子唯一能迁徙的就是这小东西。他们很羡慕那些逐水草而居的哈萨克牧民。老婆说:“我们挪几步都不行。”丈夫老王翻箱倒柜找值钱的东西,找半天才知道自己家三代贫农,箱底压的全是军功章,这东西不好送人。老婆从自己的小包袱里找出一副玉镯,丈夫老王小心包好,连夜赶到总场。老王不少战友在总场大小是个头目,人家客气一番,收下东西,答应帮忙。于是有了希望,老王和老婆眼睛光亮光亮,看见马群穿越林带,他们停下手中活儿遥望总场,直到马群散入芦苇丛。老婆说:“去不了总场,离开七连也行。”好几个月过去了,老王屁股发烫,坐不住,搭顺车去总场。老战友说:“你在连里咋没人啊?我这边说话,下边也得有人说话嘛。”老战友压低嗓子如此这般地开导一番,老王嘴巴也张开了,眼睛也张开了,脑壳上的洞洞都张开了。老战友吓一跳,老王离开后,老战友对老婆说:“这家伙,脑壳里全是石头。”老婆说:“他那吃惊的样子像是开窍了。”老王再次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