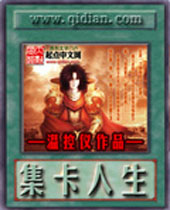��̷��-��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ȵ�������������������·�ڳ���ʢ��ʱ��������ʿ��ȥ
��Զ����������ҵ�ĵ�·����Ƭ�ġ�����ԭ������ڡ����Ǵӳ�������ƽ��
������ȥ���������ԭд������ԭ�ڳ����Ƕ��ϣ�����������ߣ����Ը�
���ȫ�ǡ�����ԭ��Ҳ���Կ����ӳ�����ȥ��������������ŵ�������
������������·���������˴������ٹ����Ļ���ͼ�������˽�ȡ�Ŀ�����
����������ʵ�ǣ�������ս���˻أ�ɥ��������Զ�Ƚ�������������Ҫ��
�öࡣ��ν��һ��������ǿݡ���д���������˼��ɥ�������ӣ���Զ�Ͼ�
����Ϣ����ˣ���Ƭд�����������׳ʿ������������ȡ������౯׳��
�������硰�����ŵ�������������ա������������ڡ�����Щ����д���˵�
·��������������Լ���ҵ��������Ǵ����ı���������Ҳ�����˶Խ�����
ҵ�ķ���Ȱ�����˲�Ҫ��ȥ֮�⡣
������Ƭ��д��������Ȼ��ͬ����ȴ���д����ԣ����ڡ����롱��һ��
��ͳһ���������Ƕ����и��ˣ����ڡ��dz�����Գ����顱һ�࣬�ʿɺ϶�
Ϊһ����Ϊһ����������Ƭ��������������ݳ����Ի�ȡ�������˵Ĺ�����
�����ñ��˵���ʫ
ë���ڸ�������ʫ������˵�������˶���������ʫ��������˼ά�ģ�
һ�����˹��ɣ�����ζͬ����������ָ�ġ�����˼ά���ǡ�������������
��ʫ�ٱ�����һ�ص����δ����ѱ�������ʶ�������Ž�ʫ��������һ��
�������ԹŹ�ʫ��δ������Ҳ�������и��������ˣ���֮��ʫ�ߣ����˽���
ڨҲ���ʲ���������ʫ֮һ����ӡ�������Ϊ���ˡ�����ڨ����ʫ��Ϊ����
�������Բ�������ʹ�á���Ϊ�����ˡ���ͬ��ֱ�������ĸ��������Դ����
�ģ������ױ������ߴ��䡣�ƴ��������裬��֮��ʹ�δ�ʫ�ۼ�����������
�����ڡ���ի��ʡ���˵�������˸�ʫ��������������ʱ�£�ֱ��ӽ�ģ���
�����ܡ���������������Ÿ��������˷���ʱ�µ���Ʒ���硶�����С�
�����衷�ȡ���ָ��������֮ʫ�˲��Ҷ������δ��⽨ר��������ƴ�Ҫ
�Ͽᣬ�������Ժ�ʫ����ʫ�������Ķ࣬�ر��ǹ�����ڦ��Ҳ���ǡ���С
���桱����½����˵������������Ϊ��������ڦ��Ϊ��ɡ���������ʷ��½
�贫������ˣ�ʹʫ����д��ʱ���ܲ������˼ɡ�
�δ�����������ʫ���ж��и���ʫ�б�������֯ʫ�������ġ����Ρ���
̨ʫ������ʷ����������˵�������·����̰��½������������������ʱ��
��������������֮��˫����ʫ�С�������Ȫ������������Ω������֪������
���ڻʵ�˵���������������죬����Ϊ��֪������֮����֮�������Dz�����
�Σ����˻���Ϊ���ǵ���ʵۣ������������������ģ���Ҫ�����֮��������
����֪�����ⲻ��Ҫ���ѱ��������Ǹ���ÿ��µ��������ҿ����ڻ�����
�ף�˵����ʫ��֮�ʣ���������ۣ�����ӽ�����������£���������������
һЩ����ȷ�����д�ˡ����յdz���ͤ��ʮ�������б�����ָժ�������ģ�
Ҳ���������ñ����ַ�д����ʫ�䡣��������ʫ������ׯ����÷��ʫ������
�����ƻ�Ȩ����ȴ�ɹ¸߲����š������˼�ע����Ϊ�����Ȩ��ʷ��Զ�ģ�
��ˣ�����ٳ����ٰ��������̳�����ʫ���С�������ͩ���Ӹ�������
������š���������Ϊ�ҷ�ʷ��Զ���ϼ����������ڡ�������ة���ȣ�
�������������š����һ����گ��ֹʿ�����ʫ���е�ʫ������������ʣ���
�ﻨ�̵ȣ�����ʵ����������ô���ѵ����Ȼ������ʫ�˵ľ��裬��������
��дʫʱ�����ܲ������Դ�����������ʹ��������������֮�۵ı��ˣ�����
Ȼ������ʫ���ٱ��˵�Ψһԭ��Ҳ��ԭ��֮һ��
ԩԩ�౨��ʱ��
����Ԫ����꣨1079���������κ��ݴ�ʷ�����κ�ĵط�����������Ҫ
���ʵ�д����л���Ըм���͢���Լ������Σ��������Լ����Ṽ�����еľ�
�ġ�ʵ���ϣ��ⶼ�����й��£�û���˻�����Դ��ġ����ϴ�������إ����
ר�Ÿ��������ʷ���к���������ʵۣ�ָժ����л�������仰������
ʶʱ���������Ƚ����ϲ����£���������С�������仰����˼���ұ�
��������ʶʱ�����ڳ������Ƚ����������·���Ȼ���������ϣ����Dz�
Ը����ظ�Щ����������ʺ����ط������������ϸ���������仰�Dz�����
������������������ʵ��Щ������������˵��������Ū��͢���������
�Ѿ��ϸ�̫�ߣ���������ϵ�չ�ȥ��д��һϵ��ʫ�ģ�˵����Ϊ��㪣���
����������ڨ���������Ϊ����δ���������֮��λ����ˡ��ε���
������е����ⶼ�����·�����Ϊ���ڻʵ�֧���·������������ͱ���ɲ�
���ڳ�͢���泼��������˵������һ��ˮ��֮�֣�����֮�䣬���س��ԣ���
���·���ϲ����ɫ��Ω�ֲ����������ֱ��Ω�����²��ҵĵ��ҷ����ˡ���
�¶��գ��Ǹ�ר�ź�������֮�����ڴ�������ʱ�ԡ�������������������ʷ
�恍Ҳ��������ҵ��Դ�ָ���������ˡ�����֮�˵�������ػ��ģ�
Թ��ʥ�ϣ�ڨ����d����á������˳�֮�ڡ�������������Ե��ָ���
�ߡ�����Ϊ����Թ����ʵۣ��������蹥���ڳ��Ĵ�ʵ��������ָ��
�̰���á��ʵۡ������恍������ʤ�ҷ߿���֮����������������������˵
�ա�������������лʥʱ�������ǣ��������Ӻ��ݴ�ʷ���������ǣ�����
��ʷ̨�����С���ʷ̨�׳ơ���̨�����˰�������ѧʷ�������ġ��ڰ�ʫ������
�˰������ڱ�������ʱ���˴������Σ����������ˡ���̨ʫ����һ�飬��
�š���д�ˡ�üɽʫ����֤����ʹ�����ǵ�֪�˰���Ѷ��ȫ���̡�����Ѷ�У�
����������ʫ�������ϸ٣����ᵽ���ԡ��·����������ɼ��˰�ʵ��
�����µ����˽�������һЩ��ӳ��ʵ�������ʫ�ģ��Դ���ɵ����ˣ�ʹ��
�Ƕ��µ���һ�оٴ붼������˿���IJ������恍������Ҫ��������֮����
�ء����ھɵ���һЩ��ֱ��ʿ��Ԯ�ȣ��ϻ�̫�����������ڻʵۡ�����ԩ
�ģ������к͡��Լ��µ��е���������������˽��Ϻã�������������
ʯ�ܣ����ڻʵ���ǰ˵�飬��������Ѻ��һ��������ڱ���ʮ����إ����
���٣����ܼ�У����ˮԱ���ɣ������������ʹ���������ã�����ǩ�鹫�£�
ʵ�����Ǹ���ٵ����֡������һ��һ�죬�����������Ķ��ӳ�������Щ��
�����������������֡�������Ҳ�ֱ��ܵ��˽��ٻ�Ǯ�Ĵ��֡������ӵ�
���˽ᡣ
��˵��ʮ��Ӷ���ʮ�������������Ԫ����꣨1085������Ӣ�����ţ�
���������λ����Ϊ���ڡ�����������̫С��̫��̫����ϣ����ڻʵ�֮ĸ��
һͬ���������ã�����ĸ����֮������½���ٻؾɵ����������˾���⡢
�����ȣ���˾����ִ���������·�һ�����ϳ�������˻������Ǿɵ�¢�ϳ�
���ľ��档��ʱ�ַ���һ������µ����˵����������С�����ͤʫ������
ǰ��˵����������ʫ�ĵ�����ࡰ�������DZ���֯���ɵģ��˰���Ȼ
�ɺ��������恍�������ʷ̨�Ĺ�Ա������ָ�أ������¾ɵ��������
������������Ϊ���̨������ʷ��ة��ȷ���������µ���Ԫ�vʱ�ھɵ�ִ����
��ȷ����ܲ�˶̰�߱��������ݣ�����Ȼ�Ǿɵ��Ļؾ���������Щ��������
�ף��ڰ��������ε�����ʤ����ͤ���̸�ʮ���䣬������Щ��ɧҲ����Ȼ��
�����������˶�Թ����ʮ��ʫһһ���Լ�ע���������ô��丽�ᡢ��
��Ӳ��������������ַ��뵱ʱ�µ��Դ������ķ���������ͬ�����Dz�����
��Ңɽ����͡����Dz�������������̨ʫ������һ��Ƚϡ�����͡��ԣ���
ƪ��ָʮ���е���ƪ���漥�����硰�δ����ľ�����˭��ŭ������Ӭ����
�Լ�����֮�ˣ���Ҷ�׳����ƿ��֣��������С��æ�������½�����֮�ˣ�
��˯��ݸ���ɶ�Ц��������͢��������֪ȷЦ���£����ý��������ɽ��
����ֱ����Ԫ�䡣�������´������ɽ�����Ƹ�����ѷλ����������ɣ�
����������Ԫ���꣬���̫��������������������£�ȷָ����Ա�̫��
�����������ﳾ����ν���ټ��Σ��ȷǼ������̨ʫ�����м�����ʫ��Ϸ
���ɡ��е���ɧ��硰�δӱ���Ц��˷����Ϊ���������š�������������
�����ԣ���֪��ǿ�ŵΨ������˵�ɼ����¹����DZ���٪�塢��칣���
����͢�¿���ٹ�������ϸ���£���ժ������Ωѧ�������𡣡�������ԭ��
��ʦ��ʫ���о䣺�����ײ���ҹ������Ⱥ��δ�ɱ��۴ơ���������������
ˡ�Ⱥף�ν����Ϊ�����Խ��ս���֮�ˣ�����С���Ӵ�������֮���ɱ���ۡ�
���ͳ����Ŷ���ӽĵ��������һ�����������������ػ�ѩ˪�ߡ�����ֻ��
�����ɣ������л������ݡ�������˵���Ǽ���ִ���������DZ���������
����������뢻�����С����Ҳ��������գ��ɼ��¡�������������Ȼ��
ͬ��������֮����������ж�֮�ˣ����õ��ַ������ơ����ڲ�ȷ��˵����
��Щ������֮����������֮������˼���̲�м�ñ磬Ҳ���ñ磬��Զ�����ݡ�
����������Ǿɵ��е���ʶ֮ʿΪ�����˱绤�����ܲ�ȷ֮����������ͬ��
����������Ϊ��˵�˻����ɵ�����ֱ�Ĵ��緶���ʵ�Ҳ�����������֮
�硣��˵������������������֮�䣬��������֮����������������˵��
�����վٶ����뽫��Ϊ�������������ɿ���Ҳ���������Զ��ʶ����Ϊ��
���������������������DZ�����Ū����ͷ�ľɵ����ˣ������������������
�����ܸ淶�����һ�������ڽ���ȷԶ�������ݡ����������������µ��ٴ�
��̨���ӱ�����ɵ�������ִ��ʱ�µ���һ�����ʣ�ר�Ե�ͬ���죬����
λΪ�¡����������ϴ��켺�ߡ�������������ȷ�����鵳�������ɵ�������
�����Կ��ڱ������ڳ��á�����������ġ�Ԫ�v�������������١�������Ԫ
�v�������֡�����Խ��Խ�ң�������Խ��Խ�棬ԩԩ�౨��������ʱ������
Ҳ�������ֻ��౨���������ˡ�
�й���һ������ҡ�������
���г����Ѿ��������ĵĽ��죬��Ҳ��һ����Ʒ����Լ�������˳����顣
��������ٳֳ��湤�������ǣ������֮Ի�����̡�����Ϊ�������ǿ���
��Ǯ���ˡ��������ֽ̻��IJ��ţ����ڳ�Ϊ������ʶ��̬�����ֲ��ò�
�����湤���ߣ�Ӧ�ðѺùء������飬��ע�����Ч����ڵ�һλ����
��������Ҫ������ң���Ҫ�����̡�
��Ȼ�����ڳƵ����dz���ҵIJ���û�У���Ҳ������ʶ��λ����ҹ��Ϊ
���������æ��Ȼ��һ�����������ƺ����࣬���Ǻ�������ң��������̣�
��ʱ���ƣ���ʱ�ı����֡������߸��ʱ�dz���ң�������Ϊ�����������ף�
��Ҫ�ƽϸ����٣���Զ���ʱ�����̣�ǿ����ۡ����۷��ǣ���۶�����
������զ�ࡣ��������Ϊ�������߳��������ģ����Ҳ�����������һЩ
���۹⡢�������������ij���ң�Ҳ�����������̡��Ϳ���̨ƽ��ӡˢ����
�ҷ�չ��Ϊȫ����һ�ҳ����������ӡ����е������ϰ�������ǣ�������
������Ԫ�õȵȣ�����˵���Dz������̣����ǿ�������ڡ���չ������˵��
�Dz��ǽܳ��ij���ң������ǵIJٳ��³��˶��ٺ��飬��Щ�鲻����������
�˵ijɳ�������Ϊ�й��Ļ��Ļ��������˶��Ĺ��ף��ر�����Ԫ��������
�ֵġ��IJ��Կ������������ݴ��顷��������¥�ؼ����������ı�إ��ʷ��
�ȶ�����˵�ǡ������̾���֮�����Dz������ұ��Ϳ��Դ����ģ������ڳ�
��ʷ�Ͼ��г�ߵĵ�λ��
���ǻ�������ǰ�����й�����ʷ�ϵ�һ���������ա��б�ӡ���鼮����
�����ģ��������κ����������ϰ�����������̣�����λ����ҡ�
��������֮��Ǯ���ˣ��ں�����������һ������������������Ҷ֮��
��ʫ̳�ϼ�Ϊ��Ծ����Ϊ�鷻�ϰ壬������Ϊ����ϳ�������������ǰ��
��Ҫ�伮�������Ǹ�ʫ�ˣ��dz����ĵ��ƶ�ʫ�贴��������Ϊ�ύ���Ž���
һȺ���ǽ�����ʫ�ˣ�������ӡ���ǵ���Ʒ������Ի�������������γ�����
�����һ��ʫ�����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