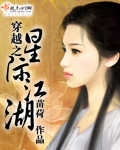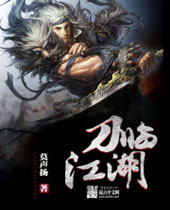江湖中国-第3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面子”的尊严含义逐渐淡出,面目的本义——即五官面貌重新回归,占据上风。譬如,清代曾朴著《孽海花》,全书共四章出现“面目”,都指五官面貌而非面子。后来,随着语言的分化,尊严含义的“面目”渐渐淡出公众语言,新的“尊严”概念——“面子”登上舞台,进入主流话语和价值体系。这一进一出的交替,标志面子文化制度进入新的成熟阶段,演变出独特内容。
清末以后,面子现象由古典时期进入现代时期,由目的型演变成目的—手段混合型,由原本纯粹的价值观蜕变出工具性,产生了手段型面子的操作规矩,以及手段型面子的话语载体——“给面子”、“还面子”、“赏脸”、“捧场”、“踢场子”……从此,面子操作就从目的领域延伸至手段领域,变成一种社会互动的技术体系,并与人情制度、关系网络融于一体,共同建构了关系社会。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正是中国社会的江湖化过程。现代型面子的生成,是近代江湖化进程的一个侧面。
清代以后,“面子”不仅替代“面目”的原有内涵和社会功能,而且还衍生出超越“面目”的新内涵。“面子”与“面目”,一字之差,含义却扩展许多。如果说,“面目”仅牵涉尊严的伦理取向,那么面子不仅部分继承它,而且还进化出一套工具性制度,发育出一套操作手法和专用术语——卖面子、做面子、死要面子等五十八种。这些专用术语不能替换成“卖面目”、“做面目”、“死要面目”和“给面目”,显示出其内涵已经更新,标志着新“面子”崛起,和相关文化机制的整体转换。
那么要问:面子一词究竟何时出现,如何发展,最后在清末全面取代“面目”的?
以正史为样本,从《二十四史》查寻到的最早出现“面子”文字的是五代(后晋)时期编撰的《后唐书》。《后唐书•;张濬传》载:“张濬出军讨太原,杨复恭奉卮酒属濬。濬辞曰:‘圣人赐酒,已醉矣。’复恭戏曰:‘相公握禁兵,拥大旆,独挡一面,不领复恭意作面子耶?’濬笑曰:‘贼平之后,方见面子’”。从上下文看,这面子与现代面子相通,既有荣耀之意,又有工具性授受行为。其中,张濬“圣人赐酒,已醉矣”一句——圣人赏赐美酒,未饮先醉,现在称“戴高帽子”,满口恭维地婉拒对方,反映时人已熟练运用双关语言逢场作戏,耍“太极功夫”。
但是,我们无法断定五代时面子体制就已经产生,因为自《后唐书》之后,接下来“面子”在经典史籍中很少出现,显示“面子”萌芽与“面子”制度尚有天河之遥。不仅是严肃的史籍,即便由宋人编撰、专收汉魏至宋初野史、小说、异闻、笔记的类书《太平广记》,亦无“面子”一说。小说是民间生活的窗口,是世情的晴雨表。一般而论,若民间有“面子”,则小说极可能有“面子”。若小说无“面子”,虽不能说民间无“面子”,充其量也只能说很少。至元明清,通俗小说诸如《水浒传》、《三言二拍》、《儒林外史》等章回小说中也都未出现“面子”,它们依按文言文传统,用“面目”、“脸面”或“颜面”表达类似含义。然后,至《红楼梦》的写作年代(1750前后),该书第五十二和六十五两回,王夫人与薛姨妈的对白两次出现“面子情儿”,始有“面子”二字。譬如,第五十二回薛姨妈道:“真个少有,别人不过是礼上面子情儿,实在他是真疼小叔子小姑子。”这个“面子”,其内涵是礼俗意义上的规矩、形象、人情的混合物,与现在的“面子”含义基本沾边,但还不完全吻合。
从《红楼梦》往后,从1750年到清朝覆灭的1900年,这一百五十年间发生了“面子”语汇使用的大爆发。譬如,在清末以《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代表的“谴责小说”中,面子语汇的使用达到了泛滥的地步。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例,该书七回讲到面子,譬如,第十九回:“有了银子,就有面子”,简直是现代功利主义面子观的宣言。而另一部小说《官场现形记》,其中面子话语的堆砌达到无以复加地步,全书竟然共166次说到面子,涉及大部分当代面子的操作手法和情景,譬如,讲、顾、要、给、留、卖、看和靠等等。
民国以来至当今,面子话语普及程度已尽读者所知,成为现代中国社会一部分,亦成为江湖化结构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面子语义的革命性转变出现在清朝末期,这种转变表面上看是以“面子”代“面目”的语词替换,实质上反映了面子价值观的工具性、手段性的转变,和转变背后的更大背景中国社会结构的江湖化变迁。
制度江湖化的本质,就是从传统的家族社会出发,进行脱宗族化、迁徙化和移民化。反映到价值观,尤其是尊严与自尊价值,中世纪以前的“脸面”蜕变为近代的“面子”,内在的尊严蜕化为表面的虚荣,虚荣进而蜕变为交换媒介,尊严外化为交易工具,被整合进江湖制度,以适应移民社会的利益交换和组织结构。这种工具性蜕变,实由人地紧张、人满为患、大举移民和游民泛滥的格局所催生。
人感冒时便会发烧,发烧是人体的一种病理性适应,是机体借升高体温,抑制病毒在体内繁殖,以牺牲局部利益维护生命总体利益。病理性适应破坏正常适应秩序,所以发烧肯定使人体感到不适——头晕、恶心和痛苦。
以面子制度为代表的江湖文化在晚清时代骤然崛起,相当于中国社会对近代移民格局的一次文化病理性适应,以病态的社会结构去适应无政府主义的风气和游民泛滥的格局。要注意的是,这种适应至今仍在进行,转型尚未成功,适应还在继续,不适、愤懑、隔膜、猜忌、压抑、恶心……还在延续。俗语“打肿脸充胖子”是面子的形象化解读。肿是病理,充胖子是用病理充生理。病理虽有害,却不乏其价值。以此为鉴,今人检讨江湖也要一分为二,看透弊端背后的益处。假如没有面子文化,没有江湖,近代中国也许早已消亡了。
后记
1958年,人类学家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C。Banfield)出版了《一个落后社会的伦理基础》。该书详细地描述了意大利南部的一个落后乡村Montegranesi中普遍存在的利己、家庭本位和排斥集体合作的观念和行为,称其为导致贫困的“贫穷文化”。村民们甘心做“家庭的囚犯”,只想最大限度地去获得一些即刻的、眼前的现实利益报酬,没有人愿意增进乡村或公众的利益。班菲尔德解释,社会结构因素引发了这个落后村庄的伦理基础──“非道德性家族主义”,他称之为这个村庄独有的贫困文化;反过来,作为整个村庄本质的“非道德性家族主义”,又进一步影响这个贫困村庄的发展,制造或加深了贫困,形成恶性循环。班菲尔德强调“非道德性家庭主义”是这个村庄所有人长期共同遵奉的价值伦理,“穷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贫困命运,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改变贫困的可能,只取决于外部的力量”。
我想说,中国江湖文化类似于爱德华·班菲尔德书中描述的意大利南部乡村“非道德性家族主义”文化及其制约的落后社会。本书中,我的结论与其惊人类似:社会结构因素(人口与制度矛盾)引发了近代中国社会普遍的“非道德性泛家族主义”江湖,同时江湖内化了国人的心灵,以其破坏性制造、加重了中国社会的贫困,形成中国近代贫困的恶性循环。在意大利,这种文化孕育了黑手党;在中国,这种文化孕育了江湖。从这种意义上说,对江湖的研究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它是社会转型大潮中淘出的沙砾。很可惜,这是一盘散沙。
此书脱稿后,作者摘少量章节张贴于互联网,有读者误认作者为江湖隐士,更将本书比作清末李宝嘉《官场现形记》;还有读者欲拜作者当“老大”,修研江湖术,令作者啼笑皆非,深感互联网上江湖情结泛滥成灾。如果单看互联网,毋宁说中国是一个江湖化国家。《官场现形记》与本书没有可比性,想看故事的人没准会对本书失望。然而往深远打量,彼此之间那样不同,一个是反思,一个是暴露;虽同系草根社会,诉求大大不同。作者坚持:一个江湖国家不能回避对江湖的反省。
著名学者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有高论:史学是历史记录和历史哲学的整合。有哲学而无史实属天书,有史实无哲学是“官场现形记”。所谓现形记,不免流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价值立场游移不定。
作者这里自称“草根”学问,诉求一种“公民读本”,从草根层面探究中国社会的内在结构,而不是从官学形态探讨中国的“真相”。所以,作者选择胡适、唐德刚的“启蒙体”,还有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费孝通(《乡土中国》)的“通俗国学”为榜样,务求深入浅出,务求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所谓深入浅出一概出于本土诉求,深也因草根,浅也因草根。至于是否有启蒙作用,作者不敢自诩,仅以此为自励和鞭策。
童年时,我便与本书有缘。
不是说我的环境很江湖,倒恰恰相反,它很不江湖。读小学遇到“文革”,学业勤勉,成绩也不俗,常常就引出一种故事情景。但凡沾沾自喜之时(譬如学业期末,一纸成绩单在手),常遇到如此这般:一圈人围着,左边人夸你好,右边人泼冷水,大放“读书无用论”厥词——“成绩好有鬼用,到社会一钱不值”……幼稚的我,如云里雾里,神情茫然。所以,自小我就接受一种二元知识观——书本知识vs社会知识,二者互不相干。具体说:做学生的,要想被人夸奖,去啃书本;要想混世,去学社会知识——抽烟、赌博、拜把子、结死党……简称“社会上的”。当中的奥妙,非一般孩童可以拆解,譬如书本为什么不敢说社会真相,社会为什么不愿渗进书本,这鸿沟怎样形成,大人们也说不清。问题是我提出的,既然大家都说不清,这就等于我自讨一道使命,争取将来有个话语权,尽力说清楚。
这一道自不量力的使命深埋于潜意识,只偶然想起。以后的岁月,忙于学业和谋生,这破“鸿沟”早已抛至九霄云外。“文革”中,先学提琴,巴望参军或者招工,进文工团混口饭,逃避上山下乡;后来赶上恢复高考,1978年进入复旦大学读书。鸿沟的问题,与我渐行渐远。不过,后来听说当代人文学者许多出自78级,不知这78级与勤思考是否一种缘分,这是后话。
不过,抛至九霄云外的潜意识,风筝线仍拽在肚里。
我这一辈所谓“60年代生人”,时值社会反复动乱,一生最大的“财富”就是动乱,是对体制反复变革、振荡、冲击的耐受,长期处于无所适从的矛盾心态。这看起来可能是坏事,说不定也是好事,因为世事变幻看多了,累积对体制内在结构的体悟,以及对体制变革趋势的敏感。就以我个人为例,半生经历了家族中的礼教残余,读书后经历集体主义时代洗礼,工作后经历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制度转型,一切公开的社会体制冲突都遇见过了。三十而立后,因生活所迫下海了,还要混迹、周旋于江湖……回头看,这简直就是四种社会体制。一个人仅仅在青春期短暂瞬间,就经历三种以上的体制变革,头脑简直发晕,真是十分不幸。然而,这究竟是一种苦难,还是一种机遇,很难说得清。管制我们的制度框架如此急速地变迁,今天向左,明天向右,规矩多变,世事无常,令60年代出生的人们无所适从——既无奈,又多疑;既接受一切,也怀疑一切。唯一得天独厚的就是能身处社会转型中琢磨制度转型。近水楼台先得月,历史上没有一代人能够经历如此之多的制度动荡。无论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还是清末民国,都没有形成过四种社会制度成分混淆一处,如此难于应付。
十年前一次邂逅,拾回了忘却的记忆。1995年,台湾著名学者杨国枢先生来大陆讲学,赠我台、港“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论文成果汇编十数卷。这套丛书对我启迪之大,在于它凑巧试图解答我心底的困惑——用“书本上的”研究“社会上的”,努力使二者贯通,弥合鸿沟。当然,这可能只是我心有灵犀之下的片面读解,是否“中国化运动”原意并不了然。但是它在效果上相当于贯通中国书本和社会,激起我莫大兴趣。书本和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