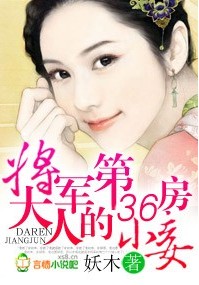3615-新发现的鲁迅-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苦与忏悔的情怀在小说《弟兄》和散文诗《风筝》中有着清晰的表白。
实在说,对于周作人,鲁迅并没有什么可忏悔的,周作人则太没有良心了。人的良心表现为能忏悔,而鲁迅在《风筝》中的忏悔是对朱安的,绝非对周作人。在《野草》第一篇《秋夜》中就有对周作人夫妇的谴责。《野草》中最难懂的一篇莫过于《失掉的好地狱》,笔者以为这篇文章中也含有鲁迅对于周作人的谴责。有人认为,《野草》中《衰败线的颤动》中被家庭逐出的老女人的复仇意志表现了鲁迅对兄弟失和的“揪心的苦难和难忍的愤怒,折磨鲁迅的,是一种‘被利用’的感觉;他为他的所爱者作了最大限度的自我牺牲,在失去了利用价值之后,就被所爱者无情地放逐,这是鲁迅绝难忍受的。一时间‘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交织于心……”(钱理群《周作人传》)。这也讲得通。有一种观点认为: “清官难断家务事”,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不是出于政治、思想、人生选择上的分歧,而纯属家庭内部的纠纷,很难说清其中的是非。而于对信子的谴责,是把一切罪责(大至国家兴亡,小至家庭离合)都归子女子的中国传统观念的表现,这正是为鲁迅、周作人所反对的。
中国古人的观念是: 修身齐家与政治绝不可分。《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大受世俗文化精英们的诟病,有人读不懂文言文,不知道“平天下”就是使天下太平、百姓平安喜乐的意思,而以为是“平定天下”、“扫平天下”、“铲平天下”。如果是这样,“修身、齐家”当然都不需要。兄弟反目自然就纯属家庭内部的纠纷,而无所谓是与非了。
再说女人的问题,不是鲁迅自己把此事的“罪责”“归于女子”的吗?鲁迅对于“家中的日本女人”一直耿耿于怀,不是事实吗?鲁迅的思想中有悖论,是很正常的。在鲁迅研究中,悖论处处都存在。笔者在此书中的一个根本观点就是: 非悖论的思想,就不算思想。在事实与预设理论发生矛盾或遇到悖论的时候,如果不懂中庸之道,就只好采取鸵鸟政策——你说便是你错。
第二部分由“陪着牺牲”到“我可以爱”(1)
鲁迅的身体向来较弱,“被家中的日本女人逐出”八道湾之后,即大病在床,多亏身边有朱安悉心照料,一个多月以后就康复了。这是朱安最能感动鲁迅回心转意的时候。萧文邦的《鲁迅新传》说:
这一时期是鲁迅和朱安结婚以来唯一接触较多的时期,也是朱安抱最大希望想以自己的温存去暖和和感化鲁迅已经冰得透凉的心的时期。鲁迅在准备搬出八道湾,去砖塔胡同前,曾与朱安有一段较长的对话,这可能是鲁迅与朱安结婚以来唯一的一次时间较长,内容较重要的单独的对话。鲁迅曾与朱安说: “我决定暂时搬到砖塔胡同去,你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娘家去?如果回绍兴,就按月给你寄去生活费用。”朱安略加考虑,颇有深情地回答: “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按: 绍兴称婆婆为娘娘)迟早一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呵。绍兴娘家我也不想去,你搬砖塔胡同,横竖总要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去……”鲁迅就于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鲁迅和朱安初到砖塔胡同,因受周作人夫妇的欺侮生气,于十月间肺结核复发,天天发烧,胃口不开,朱安是尽心尽力服侍的,病初发时,鲁迅菜饭不进,朱安就在厨房里,把大米泡了,亲自一下一下把米捣碎,天天煮成米汁,还把鱼熬成鱼汤,送给鲁迅喝。后来鲁迅的病稍有好转,就天天给鲁迅做米粥吃,这都见于鲁迅日记的记载,十月四日“晚始食米汁、鱼汤。”十一月八日记有: “夜饮汾酒,始废粥进饭,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
鲁迅的病能较快康复,与朱安的尽心服侍是分不开的。鲁迅能在砖塔胡同带病创作……天若有知,当也有朱安的默默无闻的一份辛劳在内。她怀着无望的爱,去服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使鲁迅一往无前的冲锋陷阵,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有她的一份贡献的。
朱安另有一种贡献,就是使鲁迅的文章总有一股战斗性和虚无感。鲁迅对许广平说过: “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灭亡。”(《两地书》)
鲁迅和朱安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从砖塔胡同搬到宫门口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定居,已经是他们“没有爱”的婚姻生活的第十八个年头了。到了西三条,鲁迅和朱安仍是分居两室。……
平时,鲁讯对于家务琐事.一般是很少过问的.都由朱安操持,朱安女士对于婆婆和丈夫在饮食方的喜好,观察得很细心,她还有一手煎炒绍兴风味菜肴的手艺,很受鲁老太太的称赞。鲁迅虽然没有当面赞誉过,但也从来没有批评过。她每天的时间,几乎都在安排菜饭上度过,她唯一的生活乐趣,是在忙了一天的家务之后,坐在娘娘身边咕噜噜地抽上几枪水烟。她虽然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学问很深,很受人尊敬的人,但他和鲁迅无论思想、志趣、性格上,可以说是全然迥异。哪里来的共同语言。如果说爱情的别名是理解,朱安又怎么能理解鲁迅呢?似乎有时朱安女士也竭力想缩短与鲁迅的距离,也做过种种的努力,但往往适得其反,原以为是想讨鲁迅的欢心,却反而增加了鲁迅的烦恼。
是理解之后才有爱情,还是先有爱情后理解?两种情况都存在,不必一定要先理解而后才谈得上爱情,或者是不需要理解的爱情反而更好?从鲁迅母亲的角度看,朱安的贤惠比较信子的奇怪的病(或换一种表达方式: 大先生的包办婚姻与二先生的自由恋爱),哪一种更好一点呢?爱情问题此处不能深论,但也不可以浅论,它往往是悖论。
据俞芳细心观察,她在西三条二十一号发现了这样一个秘密:
在砖塔胡同、西三条我所看到的,大先生和大师母(按: 即鲁迅和朱安)之间除必要事外,谈话很少。有一件事,我猜测这是大先生想的办法,把一只柳条箱的底和盖放在两处,箱底放在大先生的床下,里面放着大先生换下来的要洗涤的衣裤;箱盖放在大师母的房门右手边,即桌式柜的左边,盖子翻过来,口朝上,里面放着大先生替换的干净衣裤,箱底箱盖上各盖一块白布,外面是不易知道其中的奥妙的。这样,他们间说话的内容就更加少了。(《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俞芳的这段回忆,很形象地道出了鲁迅和朱安名存实亡的挂名夫妻的日常生活之一斑。鲁迅和朱安虽然一直过的是挂名夫妻的生活,但朱安似乎一直是抱有感化鲁迅的幻想,她也企图作出努力,来缩短和鲁迅的距离,得到鲁迅对她的爱,虽然这些努力是徒劳的,但她还怀着希望对俞芳说过: “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
这种幻想在朱安的脑海中一直时沉时浮了二十多年,直到她从羽太信子的口中,知道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已经同居的消息后,她的一切幻想都落一了空。这时她非常痛苦,精神十分疲惫沮丧地和俞芳说: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第二部分由“陪着牺牲”到“我可以爱”(2)
这是朱安对爱情的绝望的惨吟,这是朱安对爱情的绝望的悲泣。何等凄厉,何等悲凉,何等伤痛。但她又对鲁迅的人格,有充分的信心,她说: “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这个估计,是朱安二十年追随鲁迅的生活中体验得到的,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朱安日后的生活,一直由鲁迅从上海寄钱供养的,鲁迅逝世后,一直由许广平寄钱供养着。
局外人尚且可以认识到这一切,难道鲁迅就不知道朱安的心情吗?知道了,鲁迅焉能无动于衷,焉能不忏悔?鲁迅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他不像周作人那样坚决地放弃良心,六亲不认。鲁迅的良心,使他不忍心把握选择恋人的自由。鲁迅并非完全不自由,也不是完全自由,不自由固然痛苦,自由也痛苦,悖论使他很苦恼。鲁迅其实有很多的机会,请看萧文邦的《鲁迅新传》:
……一些浙籍同乡学生,就经常在假日和晚上,去拜访鲁迅。
……那种不修边幅的名士风度,很受男女学生的青睐和敬仰。他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一群群青年男女学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中如刘和珍、陆晶清、吕云章、许广平、程毅志、张静淑、王顺亲都和鲁迅有着亲密的师生关系,特别是同乡学生俞芬(时二十六岁)、袁志先(时二十六岁)、王顺亲(时二十七岁)、许羡苏(时二十四岁),都到砖塔胡同和西三条探望过鲁迅。
这些朝气蓬勃的新型女子,为死寂的毫无生气的鲁迅家庭,增添了青春的活力。她们经常出入于鲁迅的家庭,成为鲁迅母亲的知心人。鲁迅的母亲十分好客,很容易接受新事物。其中的俞芬、许羡苏后来成了鲁迅母亲的陪伴人,她们尊鲁迅的母亲为太师母。太师母刚到北京,语言不通,不会讲普通话,她们陪伴太师母上街当翻译;太师母上街路不熟,她们作向导;太师母行动不方便,她们当太师母的采购员。
……当时和鲁迅接触最多、相处得最熟、感情最好的女学生,不是许广平,而是另一个在鲁迅日记中出现上百次的“淑卿”、“许小姐”许羡苏。许羡苏(一九○一~一九八六),字淑卿,浙江绍兴人。她是鲁迅的学生许钦文的四妹,她比许广平小三岁,但比许广平早结识鲁迅三年。
严格的说来,鲁迅没有直接教过她书,她到鲁迅家寄宿,是周建人的关系,她是周建人在绍兴明道女校教书时的学生。一九二○年她从绍兴来北京准备投考北京大学,在投考之前,原准备住在北大附近的公寓里,但因公寓不收未入学的女生,没有住处,就找到周建人,寄住在八道湾鲁迅家里。她与周作人一家、周建人一家都住在后院,与周建人紧邻,住在最靠东的那一间,白天却和鲁迅的母亲、朱安一起吃饭。……
……她什么事都愿意找大先生谈,有什么困难也找大先生帮助。她刚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时,梳的是蓬松的新潮型短发。校长毛邦伟几次找她谈话,要她留长发,梳成盘龙髻或S髻,不许留短发,否则就要她退学,许羡苏把这事和鲁迅谈了。毛邦伟是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鲁迅便几次到毛邦伟那里疏通,没想到毛竟不买帐,而许羡苏也不听邪,照样留她的新潮短发,使校长无可奈何。后来鲁迅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曾回忆这件事说……
一九二一年九月周建人南下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鲁迅成了许羡苏的“监护人”。许羡苏有事就找鲁迅帮助解决。一九二一年许羡苏转学到男高师生物系的时候,鲁迅亲自带领着她办好转学手续,并为之作保人。后来许羡苏在男高师求学课程跟不上,想转到女师大来,鲁迅又为作保,并亲自出面办理手续,把她转到女高师数理系来。鲁迅对她也不例外,经常指派许羡苏为自己办一些琐事。……
许羡苏对鲁迅的生活也格外关心照顾。一九二三年七月,鲁迅与周作人失和,急需搬出八道湾。是由许羡苏出面联系,向同乡同学俞芬借了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的房子,给鲁迅暂住,并在鲁迅和朱安迁入俞宅后,专程来探望鲁迅。
一九二四年许羡苏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前身即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没有工作,初由鲁迅介绍到私立华北大学附属中学任教。帮助她在生活上独立自存。同年五月二十五日鲁迅由砖塔胡同六十一号迁入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四合院定居。北屋三间,母亲住东屋,朱安住西屋,中间是客厅;在客厅北面鲁迅自建了一间书房,就是所谓的老虎尾巴。当时许羡苏住在西单一个公寓里,但在公寓里住不安静,就于一九二五年搬到西三条二十一号鲁迅寓所的南屋住,女师大风潮平息后,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