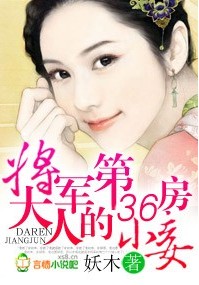3615-新发现的鲁迅-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鸮便鸱鸮般叫。我们不必学那些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声音。
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帐勾消的时候。旧帐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热风?随感录四十》)
文中的“……”是本来有的,鲁迅有一些潜台词不便于说出,也无非是“欲有所可爱”的意思。这位青年人的思想不算深刻,只是抒发了自己的悲哀,鲁迅的思想就太深刻了,要完结中国四千年文化的旧帐。既然男女双方都没有错误,有错误的当然是中国的文化(礼教)和中国的社会制度(家族制度)。鲁迅后来又说: “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南腔北调集?关于妇女解放》) 虽然说的是妇女的解放问题,但是在潜意识中也包括了自身的包办婚姻。那么,打倒了“周公孔圣人”,也就解放了怨偶。基于此种认识,所以鲁迅认为要成功地反抗包办婚姻就必须算四千年中国文化的旧帐——把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一锅端掉。在《长明灯》这篇小说里,鲁迅塑造了一位有几分狂人精神的先觉者、“疯子”、“不孝子孙”,他一定要熄灭他家乡吉光屯的命根子——从梁武帝时代就点亮了的那盏长明灯。由于遭到了大家的反对和阻扰,他就要求更彻底地解决办法: “我放火!”把古庙与长明灯一锅端掉。这个“疯子”与“狂人”一样也是鲁迅的化身。他“年级这么大了,单知道发疯,不肯成家立业”,显然是暗示鲁迅不肯承认自己的包办婚姻。鲁迅所说的“解放社会”也就是毁坏旧社会: “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以一锅端掉的毁坏方式算四千年中国文化的旧帐——自然也就“解放了自己”。不毁坏包办婚姻,一切都没有意义。
“陪着做一世牺牲”并非心甘情愿,反抗就不可避免,然而阻力甚大,反抗就过火了。因个人身心遭受不幸而痛恨“古老的国度”和东方文化,要求彻底毁灭中国文化(鲁迅最激烈的名言是: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是当时许多中国文化精英们的共同特点,发掘这种态度的心理基础——潜意识,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人永恒的苦难,具有重大意义。全盘西化的思想在当时中国新知识分子中间是很普遍的,这在当时算是很深刻的思想罢,如今这种思想依然很流行,然而理论上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时间问题。俗话说: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解放社会与澄清黄河一样,不知须要多少代人的正确的努力才能完成。何况还有“歧路”。当年严复访问欧洲,在伦敦与孙中山有一次会面,谈到中国社会的前途,严复主张从教育入手进行改良。孙中山说: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施行家也。”对时间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似乎是思想家与革命家的一个主要区别。李长之认为鲁迅不是思想家,是否也考虑到这一点?社会转型要马上见效,改良太慢了,不如一锅端掉,这是革命家的特征。如果“解放社会”是指建设新社会,那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据说是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再解放自己的包办婚姻当然就更来不及啦。
从包办婚姻中醒过来极其容易,大概从包办婚姻存在的那一天起就有人醒过来了。有病毒必有抗体,一阴一阳谓之道,岂有等四千年之后方才有人觉悟之理?问题是要解放社会从而解放自己,就感到征途太遥远,不走捷径就等于无路可走。据外国书萨特的观点看来,人注定是自由的。实际上鲁迅还是自由的,他找到了先解放自己的捷径,从而发生了理论上和道德上的困难。鲁迅当然不可能不认识到这一点,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也说过: “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所以鲁迅才有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哀,因为他又走进了另一个梦——现在的梦。所以在《野草》中有许多次的“梦见……”。人从此梦醒来之后即进入彼梦,彼此彼此,人生似乎总也逃不出庄子式的梦。庄子太“陈腐”了,那么,就用外国书时髦的方式表达: 人的本质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人人都处于两种同样客观,又相互矛盾的可能性的存在之中,所以人是虚无的存在。“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这个判断等于说,黄河清了,我的包办婚姻就解决了,内在的否定正如它的肯定一样客观真实,肯定与否定是一体两面,呜呼,无法可想。鲁迅本来也明白这一点,看他的《阿Q正传》就知道: 阿Q在梦中命小D搬赵家的家具时想的是: “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因为只有“搬得快”才能即生成就,解放了自己,然而这是梦。
第一部分婚姻与自由(7)
除了时间上“要搬得快”的困难之外,还有另一个更深刻的困难: 以社会为中心,重社会,轻个人的观念并非新思想,而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如果说鲁迅没有看出一矛盾,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虽然鲁迅从来也不进行深刻地理论思辨,但是基本的思维的条理性和逻辑的一致性总不会缺乏。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本质到底怎样,人如何获得幸福的问题。走“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之路有没有可操作性?为了避免离题,仅从个人身体的存在与世界的关系中的基本形式——性的表达方式的角度谈一谈。请看英国作家戴?维?劳伦斯的观点,劳伦斯要求人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他认为: 当人真正去爱一个人的时候,这种爱可以滋润人的灵魂。人可以通过人最基本的行为即性行为,使人得到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满足。人可以不通过社会而得到幸福,只要两情相悦就行。人的成功也不需要社会,性爱的满足可以表示他的成功,性爱是使双方获得伟大力量的武器。劳伦斯的这些观点,挑战了工业革命时代英国社会的流行观念: 国家利益重于个人利益,社会幸福决定个人幸福,个人要成功必须通过社会,等等。所以他的书《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等小说,就不为英国社会的舆论所容,而长期受到封杀。劳伦斯写的外国书简直就是英国的《金瓶梅》,既然外国书也有相互对立和矛盾的观念,我们读外国书也就有可能产生读中国书的效果。在《灯下漫笔》一文中,鲁迅对某些“赞美中国人”的外国书表示愤慨,因为这种外国书赞扬中国的文明。读这种外国书岂不是比读中国书还糟糕?又如外国书主张中庸之道者也是有的,等等。“多读外国书”,不论是流行书(大众通俗读物)还是纯文化的哲学只要是读懂了,都有可能翻过来再喜欢读中国书。鲁迅自己其实就是如此。而一些“食鲁不化”的人,就是不肯明白这一点,这正好应了鲁迅所说的“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这句话。
鲁迅“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的思想显然不同于劳伦斯的观点——重个人,轻社会。鲁迅的观念更接近于中国书的传统观念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或工业革命时期社会中的流行书的观念——重社会,轻个人。虽然两个人的观念不同,但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却又颇有些相似。劳伦斯与自己的师母,德文老师的太太私奔;鲁迅则与他的学生许广平往上海同居。他们都摆脱世俗观念的束缚,突破了先“解放了社会”的“梦”,“只要目前的梦”——“解放了自己。”
由此可见,“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显然是一个由未经证明的假设作出的判断。它既不能为现实观察所证实,也为以上的逻辑推论以及鲁迅自己关于梦的理论和革命实践所证伪。鲁迅在《野草?希望》中说: “我大概老了。”鲁迅通过自己的身体衰老知道实现这一假设的困难。鲁迅在《野草?一觉》中说: “每听得机件搏击空气的声音,我常觉到一种轻微的紧张,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鲁迅由“死”的可能性而一下子觉悟到“生”的迫切性,于是就把“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的逻辑关系颠倒了一下,先解放了自己,再去解放社会。这也无可厚非,只要你的心是真诚的就好,孰先孰后,并不重要。
有人认为,鲁迅只是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却始终没有绘出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这是鲁迅思想的缺憾。其实不然,鲁迅清醒地知道,“这么早,这么容易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人们,可仍然有些不确实,在我看来,就不免有些空虚,还是不太可靠。”(冯雪峰《回忆鲁迅》)现在设计出的“黄金世界”的蓝图,也无非是腾口说空话而已,所以鲁迅不去做这种无用功。不作理论思辨,而是以诗赋的风格使用语言,以否定的方式发表“随感”式的思想,这是鲁迅文章的特色,鲁迅不以诗人的思维设计未来社会的蓝图,是颇明智的,鲁迅毕竟是革命文学家,不善于玄想。
此时的鲁迅是非常痛苦的,作为“人之子”,他已经“醒了”,然而仅仅是醒了而已,醒了之后怎样?他还没有想好该如何走出去,正如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认识到的,这就使人痛不欲生了。鲁迅面临着梦醒之后的选择,十分悲愤,这种选择是煎熬人的,这种痛苦充分地表现在鲁迅定居上海之前发表的文章之中。鲁迅不满意于做“人之子”,做“儿媳妇之夫”,而要做一个真正的人。伊藤虎丸所谓“个的自觉”。何谓真正的人?知道“爱情是什么东西”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忍受包办婚姻,延续“挣扎”的痛苦,几乎也等于在“吃人”,谁吃谁都分不清了。这是鲁迅《狂人日记》不好懂的地方,后面再说。
爱情并不等同于性欲,也不是人一结婚便可得到的。鲁迅在《寡妇主义》一文中就曾说过: “爱情虽说是天赋的东西,但倘没有相当的刺戟和运用,就不发达。”所谓“相当”就是满意、合理;所谓“刺戟”就是有“所可爱”的对象,包办婚姻就不太可能提供这种刺激;所谓“运用”,就是能操作的爱,能享受“敦伦”之乐的夫妻生活,而非性幻觉。鲁迅没有得到正常的夫妻生活,有爱的欲望和能力,却没有所可爱的对象,“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生命的泥委弃在地上”,里比多白白地浪费了,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家庭生活中的一个“悲哀”。鲁迅特别在“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之后又点明“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然后就用了“……”号。当然,除了“……”号以外,还可以用其他方式表达他的悲哀。《呐喊》、《彷徨》、《野草》的绝大部分篇章里都在表达这种悲哀。
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是痛苦而沉闷的;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是脱俗而高尚的,但又不能免于“内心的矛盾”。由于鲁迅的性格的缘故,这种复杂的感情产生出来的《呐喊》、《彷徨》、《野草》就很耐人寻味。鲁迅不像郁达夫或郭沫若等人那样喜欢表白性压抑,而是喜欢掩饰性压抑,所以需要一番猜测。
后来兄弟失和,鲁迅被迫搬出八道湾时,曾经建议朱安回老家绍兴去住,他将按月寄钱供应她的生活,朱安不同意,因为一旦回老家就等于被休,娘家人也要受人轻视,朱安恐怕会与祥林嫂同一命运,所以回老家无疑是死路一条。鲁迅写《祝福》说明他很能理解这一点,他们仍然住在一起。再后来,鲁迅和许广平恋爱,常来常往,以后在上海同居,朱安不仅不妒忌许广平,而且对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颇示好感”。朱安勤俭治家,一心一意地服侍鲁迅的母亲。鲁迅逝世以后,朱安继续照料鲁迅母亲的生活,直到老人87岁逝世,朱安代鲁迅为母送葬,完全尽到了一个长媳的责任。朱安的这种高尚的道德,是很感动人的。朱安说她自己是“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她实实在在地是“陪着做一世牺牲”。鲁迅对朱安,也忠实地实践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