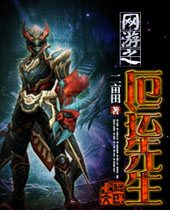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她是知道的。
第三部分那可怕的死亡
她沿着山顶方向往上走去,刚才那条橙黄色的狗就是从那个方向上来的。她笨拙地走着,她的腿瘦瘦的,线条可说优美好看,像小鸟的脚爪一样;老人眼含笑意,颔首望着。他看她渐渐远去,一直到看不清,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见她那衣裙像一个小小的蓝点。随后,他又陷入孤独之中,这种被遗弃的孤独之感正因为她来过(当然她的到来这件事本身是这般审慎而深有用心),更加显得深广无边,令人张皇失措。
她那件连衫裙刚才在照满阳光的平台上显得非常蓝。昂代斯玛先生闭上眼睛,它那色调依然清晰可见,可是在此之前,从这里走过的那条狗,它那橙黄色的毛色却已经淡忘,难以分辨了。
他猛然后悔让她走了。他叫喊,要她回来。
“你父亲究竟是在干什么呀?”他问。
到此为止,她对于年迈力衰的人尽管敬畏,但总觉得厌恶,现在她变得很有些肆无忌惮。于是从树林里传出一声气势汹汹的刺耳的叫声:
“他在跳舞。”
昂代斯玛先生的等待又重新开始。
等待,说起来显得矛盾,这等待现在倒是心平气和的,不像刚才那么叫人难熬。
他望着那光芒耀眼的深谷。大海从这个高度看去几乎是一片蓝色,他发现,海和天空是同样的蓝色。他站起来,两腿舒展一下,更好地看一看大海。
他站起来,往深谷那边走上三步,深谷里的光线已经开始呈现黄色的色调,正像他预料的那样,村里广场树阴里一排绿色长椅附近,瓦莱丽的黑色汽车就停放在那里。
接着他又转回身,走到椅子跟前,又坐下去,再一次估量着自己这庞大躯体,穿着深色服装,沉陷到椅子里去。坐好以后,他就准备等待米歇尔·阿尔克,不但是等他,还要等那个小女孩,等她回来,是预计要等她的。这时候,就在这一段空白时间内,昂代斯玛先生将要看到死亡的恐怖。
他神智清醒循规蹈矩重新坐到椅上,准备等米歇尔·阿尔克,他将要迟到,他准备承受下来,他对他礼貌不周,他也情愿以完全宽容的态度处之,因为在这一刻他想到瓦莱丽毕竟是近在咫尺——她的那部黑色汽车不就在那边吗?不就停在村里白闪闪的矩形广场上吗?——可是,就在这一刻,昂代斯玛先生看到了那可怕的死亡。
这是不是因为看见那个小女孩走在路上,步履不稳娇弱地走在满地松针之上?是不是因为想象她一个人在树林下踽踽独行?她心惊胆怯地朝着水塘急行?是不是因为想到她父亲叫她来通知老人,这个见了就叫她厌恶的老人,这虽说是苦役,可是她还是得顺从照办,哪怕顺从最后也还是让傲慢给摧毁无遗?
昂代斯玛先生觉得自己被一种欲念所吞没,去爱另一个孩子,他感受到这样的欲念,他的感情只能顺应这种欲念,此外他是无能为力的。
他有时也许会讲起在他漫无止境的风烛残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次意外事件,他总是坚持说:自从这个小女孩向着荒凉的山顶走了以后,而且她走路的身姿那么袅娜娇弱,是往水塘方向走去,他知道,瓦莱丽决然不会一个人单独去水塘那里的,从这个时刻起,就是在那一天,他觉得,那强烈的欲念就在他心里盘踞滋长。就是在那一天,而且是最后一次,他想改变他的感情,倾心于那个小女孩的欲念在他心里滋生出来了;可是那个小女孩,却以某种粗犷甚至凛然不可犯的力量竟自往水塘那边走去,他说,从前他曾经以同样的力量对一个女人也发生过同样强烈的欲念——真是致命的情欲呵。
第三部分一个不相识的男人
不过,现在,他的欲望是这么强烈,恍惚间像是闻到了瓦莱丽孩子样的头发发出的芳香,他面对着自己的无能,他生命最后阶段的这种无能,痛苦得两眼紧紧闭起。但是——在树林深处是不是掩藏着许多花卉,未曾见过的鲜花,一阵轻风吹来,把花香吹到他的面前?是不是那另一个女孩从他面前走过,他没有察觉,她留下的芳香依然飘动不散?——正因为这样,对他自己孩子那芳香四溢、金光闪闪的美发的记忆又涌现在心头,正是因为这样呵,那金发不要多久很快很快就要在这座房子里把一个不相识的男人的睡梦熏染得芳馥无比——这地狱似的可怕的记忆,就这样预先盘踞在他心上萦回不已。
一种渗透性的沉重感徐徐潜入昂代斯玛先生的身体,这种重量流布在他四肢五体,从整个身体又一点一点扩散到他的精神领域。他手搭在坐椅扶手上,变得像铅那样沉重,他的头也恍恍惚惚渺渺茫茫,头脑甚至感到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消沉沮丧,也不知头脑是不是还保持着清醒健全。
昂代斯玛先生想要挣扎一下,他想说这样长久枯坐不动,等待米歇尔·阿尔克,天气又这么热,不应讳言,对他的健康来说这简直是灾难。但是毫无办法。沉重感在他身上越来越加重,越来越深入,更加使人消沉无力,更加叫人无法理解。昂代斯玛先生想要阻止这种情况再发展,阻断它不要再往身体里面渗透,可是这种沉重感在他身上还是不停地在扩展。
这种重量终于占领了他整个生命,并且潜伏下来,这时,这种游走性的东西在取得全胜之后,就安然睡去了。
这沉重之感盘踞在他身上安然睡去,在这期间,昂代斯玛先生却试图去爱他根本不可能爱的另一个女孩。
当它躲在他身上沉睡的时候,昂代斯玛先生又试着唤起对瓦莱丽的回忆。瓦莱丽这时就在山下村里白色矩形广场上,瓦莱丽把他给忘了。
“我要死啦,”昂代斯玛先生大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不过,这一次,他没有感到吃惊。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就像刚才听到一阵风吹来一样。不过,这声音这时即使出自另一个不相识的人,也不会让他感到惊诧,因为爱水塘边上那个小女孩,他是无能为力的。
这样,他只好不去爱那个小女孩了,若是他能他是要爱的,正因为他不能,所以他只有一死,一种并不置他于死命的虚构的死亡。总会有一个人去爱她,爱得如醉如狂,那个人不是他,本来可能是他,但是他毕竟将不是那个人。
他并没有死,虽然他竟自相信已经死去。他静静地等待这个意识带来的如此强烈的震惊逐渐消逝。他这样的情绪,他想改变一下,但是不可能,他想采取另外一种爱的意向,也不可能;这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他倾其所有的力量集中于审视四周生长的树木,强使自己搜寻那些树木的奇姿美态。美丽的树也帮不了他的忙。他心里想着另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站在水塘岸边,并不去看四周的树,只顾注意池边青草难以察觉的萌生滋长,可是草木的生长又于他何干,也帮不了他的忙,他宁可爱他的女儿瓦莱丽,对瓦莱丽的爱永远是灿烂发光、不可言传的。这是既成的事实。
“这家伙,真是坏透了,”他又开口说道。
第三部分最完善卓越的理性
徒劳无用呵。你看,他在想方设法,还是回到等待中来,久久的期待,他被撇在等待之中,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久久的等待,长久地等下去,他完全可以说是空等一场,这就是失望!瓦莱丽有多么好的金发,她走遍世界,世界也要为之黯然失色,在他看来,世界上有这样美的金发,该有多好,但是他又为什么要想到这个呢?昂代斯玛先生这样想。同时,昂代斯玛先生,他也知道这些都不该去想。如果可以去想,那为什么他又满怀痛苦,心碎欲裂,而不是柔情满怀、心喜情悦?昂代斯玛先生继续想着,这时,他发现他是在说谎,他知道只有在极端痛苦之中才会有意作如是之想。
昂代斯玛先生认为这样的痛苦未免幼稚,还带有青春气息,幼稚得可憎。痛苦持续了多久?他也说不出。反正持续时间相当久。最后,他也只好甘心承认是它爪下的牺牲物了。在他一生当中,理性从来不曾遭际到任何险境,恰恰相反,一向是受到称赞的,说它是可能存在的理性之中最完善卓越的理性;现在,这样的理性也不得不从一贯运行的轨迹上改弦更张,还要妥善地去适应。
昂代斯玛先生同意不再去发掘什么其他的奇遇,只专注于爱瓦莱丽。
“米歇尔·阿尔克今晚不会来了,为什么还要等他?”
他又大声地说。他有意把话大声说出来。他觉得他发出的是发问的声调。一点也不感到有什么可怕,他自己又作出回答。因为发现了瓦莱丽金发之美含有普遍意义,与他能感到的恐惧相比,世界上难道还会有更可怕的事物?
“事实上,究竟是谁搞成这样的?”他自己回答说,“处在我的位置上,谁能不生气?”
他往左边朝山路上看了一看,等一下那个已经被昂代斯玛先生抛弃不顾的小女孩就要从这条路上走回来。昂代斯玛先生就这样,直直坐在他的柳条椅上。可是那个小女孩并没有从水塘返回。黄灿灿的柔和的阳光照耀下的下午,这时充分展现出来了。
昂代斯玛先生在这样的身姿下睡着了。
后来,昂代斯玛先生认为这一天下午他一度成为某种前所未曾发现的事件的受害者——据他说,这新发现的事件既惊心动魄,又空无着落——他一生不曾有过闲暇去注意这样的事,由于他年事已高,本来也不一定使他这样心乱神慌,但是竟害得他这样疲于应付;他认为这件事肯定不是无关紧要的琐事。为图方便,或者因为思绪恍惚找不出一个确切的字眼,他把这一发现就叫作对他女儿的爱的灵智的发现。
话题是由米歇尔·阿尔克引起的,他独自一人在这里讲了一大篇话,他还要继续讲下去,可是米歇尔·阿尔克究竟是何许人,原来他也不甚了了。他本来是温和平静的,接下来,措词激烈、满腔愤懑的话语就滔滔不绝地在平台上响起来了。他自己也听得清清楚楚。
第三部分一种已经见过的纯洁无瑕
昂代斯玛先生处在这种绝非他力所能当的恐惧情绪之下,如同在死之盛宴上吞嚼自己的心肝脏腑一样。他隐隐约约感到这种狂吃大嚼的乐趣,同时,无疑也是由于恐惧,昂代斯玛先生想到米歇尔·阿尔克对他这样漠不关心,这时一团怒火涌了上来。
这以后他朦朦胧胧沉入半睡眠状态,那充满柔和的黄色阳光的山谷就在他面前。
在山下一片平原上,在某些点上,在灌溉过的耕地的上空,已经腾起一片细薄的水汽,这山谷下黄色柔和的阳光要把这一片水汽驱散是愈来愈不容易了。
盛夏六月中这一天,真是完美无比,是难得一遇的,不用说,也是寂寞单调的。
昂代斯玛先生打一个盹儿继续了多少时间?他也根本说不上来。他说在他整个迷瞑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些说来可笑但又令人称心的快事,关于同米歇尔·阿尔克谈给瓦莱丽修建未来那个一年四季面对大海的露台的预算的事。
其实打个盹儿,不过片刻时间,充其量不过让那个小女孩走到水塘去玩又从水塘走回来那么一点时间。事实上她正从山顶往下走呢。
于是昂代斯玛先生又回忆起在他生命最后时刻与这另一个小女孩曾经有过接触这件事。
走在地上发出的脚步声,先是在树林的远处,渐渐由远而近。这脚步走在铺满枯叶的山路上发出的声音是那么轻盈,昂代斯玛先生就是睡去也不会受到惊扰。他还是听到了脚步声。他知道有人走过来,他估计那是在南山的半坡上;他对自己说,那个小女孩从水塘已经转回来了,他认为离平台还远,还可以再睡一会儿,所以他没有准备去迎她,管自己睡着,睡得这么实,转眼就什么也听不见了,甚至她走到离他只有几米远他还一无所知。
小女孩果然是回来了。昂代斯玛先生沉沉睡去,睡得可真好,他的脑袋,那还用说,依旧朝着她从水塘回来必经的那条山路的方向,就那么低着头睡着。
她是不是一声不出、默默看他看了好一会儿?他不知道。她兜了这一圈前后是多长时间,他也不知道。睡了这一觉,他也不知道。
“喂,先生,”小孩轻声叫他。
她的脚轻轻拍击着平台上的沙地。
昂代斯玛先生两眼一睁开,就看到别人在看他——一种已经见过的纯洁无瑕、放肆无礼的眼神。她在他身边靠得很近,这和她第一次来时是不同的。在阳光下,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