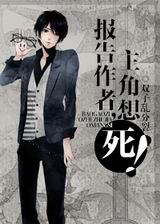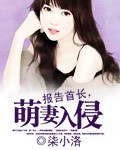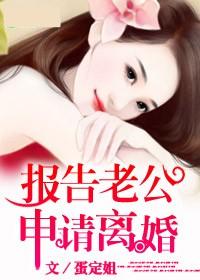高考报告-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者吴敬梓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先生等等都曾在此处挥汗应试过,他们中有的考中了秀才,有的考中了进士,有的考中了状元。
在江南贡院这座〃科举考城〃中,最为壮观、占地面积最大、令人看后最为毛骨悚然的要算〃号舍〃了。所谓〃号舍〃,既是考生考试的地方,又是考试期间考生们吃住的场所。江南贡院这个大考场有〃号舍〃多达两万零六百四十四间之多!我走进一排排像养鸟的笼子似的〃号舍〃细细观摩,觉得十分恐怖,那号舍外墙高约八尺,门高六尺,宽刚好一人之身多些。每排号舍长短不等,多则百间,少则几十间,前排与后排之间相隔不足一米,因此整个考场就像一排排猪圈鸟笼式的建筑,旧称〃号巷〃。号巷门口设有水缸和号灯,供考生夜间行路和白天饮水使用。号舍三面是密不通气的墙,只有朝南一面是出入处和考试见光处。号内有一块掀起的木制的桌案和一张坐凳,考生晚上睡觉时就把桌案翻下作床铺,有的就干脆躺在上面。所有考生自跨进这里,一直到考完才能离开号舍,吃喝拉撒全在其中。据传有一位才华横溢、文采超群的考生,因为没有占据好一些的号座,只得坐于巷尾的〃粪号〃,结果几天下来,被粪桶熏得昏头转向,无法考试,还差点送了性命。有史料记载,由于号舍管理杂乱,常有考生被蛇咬死。有的考生则受不了号舍之苦,用烛签自刺身亡或悬梁自尽。至于考场的一条条规矩,更是名目繁多,且严厉之极,是我们现代人闻所未闻的:
负凳提篮浑似丐,过堂唱号真似囚。
袜穿帽破全身旧,襟解怀开遍体搜。
未遇难题先忐忑,频呼掌管敢迟留!
文光未向阶前吐,臭气先从号底收。
这是清嘉庆年间文士缪仙记述乡试感受的一首长诗中的片段,读后令人仿佛能亲身感受旧考场上那种〃三场辛苦磨成鬼,功名两字误煞人〃的辛酸以及获得〃一路连科〃的不易。江南乡试,各科应试学子多达两万余人,但能够录取的只有一百多名,其比例仅为1000 : 1,相比我们现在的高考成功率难上几十倍。多数久困场屋、备尝艰辛的学子,最后只能名落孙山,折桂无望。但科举考试毕竟又是读书人通向荣祖耀宗、改变命运之路,同时也是证明个人才学实力的机会,所以像《儒林外史》中描写的一直考到七八十岁的人不足为奇。郑板桥从二十三岁考上秀才,到四十岁才中举人,前后历经十七年之久,比我们现在考博士要艰辛得多。而许多名流学士还连秀才进士都没有考取,当然有人本来就对八股文不感兴趣,但旧科举考试的艰难一面多少也能从中体现出来。
当历史车轮滚滚碾入20世纪时,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日,光绪皇帝收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一份奏折,上书:〃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奏折后来到了慈禧手中,这位已入暮年的老太婆自知无力抵抗时局变化,便顺水推舟,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即1905年9月2日,诏书全国:〃……着即自丙午科(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亦即停止。〃此诏书宣告了中国长达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的结束。1903年江南贡院乡试后得头元的刘春霖,因此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爷。
科举废除之日,北京清华大学、京师大学堂和上海马相伯创建的〃江南第一学府〃复旦大学等现代学校已经开始建起。尤其是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蔡元培出任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后,中国的教育更进入了第一个全盛阶段。〃一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学问的人团聚起在一处,一面研究高等技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大学教育准则,几乎成了后来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大学的办学灵魂。〃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的这些思想与观念缔造了百年中国知识分子以学问为天职的那种勤学精神和对政治与物质常常不屑一顾的清高。中国的大学,在这些具有全新思想的先导者们的奠基下,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崛起,并为20世纪中国诞生大批政治家、社会学家,特别是自然科学家准备了温床。但在前半个世纪,大学的大门一直朝有钱人敞开,穷人不可能或者说极少有人可以跨进去。
第一章 大学——中国人的梦邓小平决策
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宣告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的诞生。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平民百姓才开始以公平竞争的方式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当然也有不少人因为工作和劳动的突出表现而被直接送进了大学,他们毕业后在各条战线上成了骨干和管理者,这使得大学真正意义上成了人民的高等学府。然而由于国家底子薄,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程度很低,一般能读上小学、初中的就很不错了。在建国初的十几年里,大学仍是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通过十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随着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和受教育的普及,一批解放前后出生的普通百姓的孩子开始有机会向大学门进军。可就在这时,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政治与文化的〃浩劫〃,使中国人上大学的梦彻底地被打碎了,大学被停办,这是中国教育有史以来受到的最为痛苦的一次摧残,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使连笔者在内的无数适龄学子失去了基本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并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里处在人生前途的黑幕之中……这种痛苦,并由此带来的沉沦只有亲历者才会有切肤之痛。
后来我们这一代人曾经有过重上大学的可能,偏偏又出了一个〃白卷先生〃。
十年浩劫和〃白卷先生〃给本来已经落后的中国又添了重重的一层冰霜,中国人久碎的梦何时复圆?
苍天在问,百姓在问,更有众多青年学子在问。
1977年8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自告奋勇挑起了主管教育的工作,在那个炎热的夏天,他心中装着一件早已想透又没来得及说出的大事,便在人民大会堂,亲自召来四十多位教育界的著名人士及官员,其中引人注目的有周培源、苏步青、张文佑、童第周、于光远、王大珩等毕生从事科学与教育的专家。虽说那时〃两个凡是〃仍高悬在人们头顶,但因为此会是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所以有人说这个会倒有点像〃神仙会〃,大家畅所欲言,难得这么痛快。
8月6日下午,有一位被邓小平邀请来的教授大概受到这个会议的气氛影响,激动地站起来,面对邓小平慷慨陈词:请中央领导尽快采取坚决措施,迅速改变现行的大学招生办法,切实保证新生的质量。因为大学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的第一关,其作用就像工厂的原料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可是这些年来,我们招收的大学生有的只有小学文化,我们这些大学教授只能为他们补中学甚至小学的文化课,大学成了什么?什么都不是,还谈什么教育成果?这种情况不改实在是不行了!
〃查教授,你说,你继续说下去。〃坐在沙发上的邓小平深深地抽了一口烟,探出半个身子,示意那个被他称为〃查教授〃的老先生往下说,〃你们都注意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哩!〃
查教授提提神,继续他刚才的慷慨演讲。这时人们发现邓小平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与会人士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一件大家早已想说想做却又不敢打破束缚的大事情就要发生了。
果然,等查教授发言完毕,邓小平询问了一下身边管教育的刘西尧部长有关具体细节后,当机立断:好,就这么办。招生会议重新开,高考从今年就立即恢复!
高考立即恢复!立即恢复高考!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是最高兴的一个,全国人民也跟他一样兴奋不已。
这消息应该说是1976年10月结束〃十年浩动〃后,在中国老百姓中第一个引起重大反响的事。尽管那时国家的整个机体仍处在僵硬状态,但恢复高考则如冬眠的肌体的脉管,开始有血液在涌动,正是这根血脉的涌动,神州大地像初春般有了第一枝青绿……
第一章 大学——中国人的梦亲历恢复高考大战(1)
1977年,新中国教育史上出现两大奇观:四十四天连续不停的教育工作会议;第一次在冬季进行大学招生。
似乎恢复高考招生的一切枷锁都已解除,但这时突然有人提出:中国虽然是个考试大国,积压了整整十年的考生一起拥进考场,谁也没有组织过呀?首先需要一大笔经费,其次印考卷需要大量纸张啊,这两样事现在想来根本不可能成为问题,甚至可能是考试主持部门赚大钱的好机会呢!当时不行,全国上下一片穷。问题因此上交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中央决定:关于参加考试的经费问题就不要增加群众负担了,每个考生收五毛钱即可,其余由国家负担;印考卷没纸,就先调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印考卷!
从此,就有了世界上有史以来声势最浩大的一次考试,参加考试的总人数达一千一百六十余万之多。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几个月时间内,神州大地竟有如此庞大的考试大军一起拥进考场,这本身就值得史学家们大书一笔。
中国人的大学梦在此次的大考中获得了最彻底、最淋漓尽致的展现。它有太多的精彩,也太令人回味。
就学龄而言,应该说我正是属于这部分人中的一员,但我却没有这个福分亲历这场波澜壮阔的大考我当时已经走进另一种大学(穿绿军装的人民解放军大学校),使我遗憾地丧失了这次机会。但在今天,我身边却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与同事,他们以自己的亲历替我们那一代人圆了历史性的一场大学梦。
这场梦做得好苦,而圆它时又突如其来,让人不知所措。
〃当时我一个同学特别兴奋地骑车来告诉我,说要恢复高考了。我虽然早就盼望这一天,但还是一下子就惊呆了,眼泪一涌而出。我跟同学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这下有希望了!当时那种情况,有点像在黑夜里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你什么东西都看不见,迷路了,你根本不知道往哪儿走。恢复高考这个消息,就相当于前头突然冒出火光。当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想着我赶快蹦到那儿去。〃中国儿童剧院编剧、北京师范大学78届学生陈传敏所表达的心情正是当时数千万年轻人共同的感受。
那种感觉的真实情形,其实用语言无法表达,只能是惊愕,只能是梦幻,只能是眼泪……
肖正华,67届高中毕业生,77届考生,现为安徽某师专附中高级教师。他对我说的那年恢复高考及参加高考的过程是一场〃天方夜谭〃:
……1977年第四季度的一个早晨,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喜讯,就立即把它告诉了正在喂猪的妻子,她却并没有多大的反应,更没有我那种欣喜若狂的激动。一个农村妇女关注的主要是实际生活:丈夫、孩子、柴米油盐……
而我则有些措手不及,因为当时被公社抓差去写个现场会材料和编一个短剧。完成后,我掐指一算,离高考只有十一天了,能用于复习的也只有十一个晚上了考什么呢?理科吧!翻晒物理,冲洗化学,只觉得〃雾都茫茫〃,欲记还忘。改道易辙,考文科!耙地理,挖历史,抢数学;语文和政治,就靠自己的〃老板油〃凭自己经常为公社写点〃四不像〃的看家本领。总之,一切听天由命吧。
开考了,我坐在县二中第五考场第27座。每场我都大刀阔斧,一口气从头杀到尾,然后再回师围歼〃顽敌〃。虽然时有〃精逃白骨累三遭〃的痛苦、〃大雪满弓刀〃的遗憾,但丝毫也没有改变我〃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信心和意志。为了下一场的轻松顺利,每一场我都第一个交卷,决不恋战。一位满唇茸须的小老弟考生替我担忧道:〃喂,27号老大,还能泡幼儿班,做游戏吗?〃十一年才盼来这个机会呀,人生能有几个十一年呢?换成李白,不说〃千年等一回〃才怪哩!
为了赶这趟考,事前我还专门向老岳父汇报了思想呢。〃很好,能考上?〃〃能!〃〃那你就去考呗。〃考取后,我才笑着向他解释,当时为了孩子,大的六岁,小的三岁,队里又刚分责任